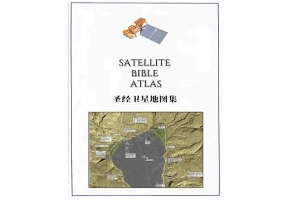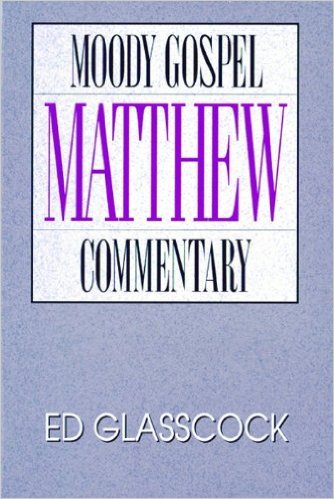在古代教会,篇幅最短小、内容最简单的马可福音远没有其他三卷福音书那样受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它只是更全面的马太福音之缩写版,因此它难以企及后者的崇高声望。然而,近现代学术研究终结了马可福音相对受冷落的局面,反而将其摆在学术关注和重点研究的聚光灯下。人们不再认为它是另一部完整作品的删节版,反而确定它是一部为某个特定目的而撰写的完整、独立的作品,也是研究福音叙事的极佳入门书卷。
与其他福音书一样,马可福音也未清楚地指明其作者。然而早期教会的传统一致认为,作者应为使徒彼得的侍从马可。
关于马可福音及其来源最早的直接证据,是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主教帕皮亚(Papias,公元70-150年左右)在大约公元140年写下的。[1]优西比乌(Eusebius)曾引用他的见证如下:
长老(即约翰长老)曾经这样说:马可成为彼得的解释者(interpreter)后,准确记下了他所能记起的全部内容,然而并非按照主所言所行的时间顺序。因为马可既未听到主亲自的教诲,也不曾有机会跟随他。如我所言,他后来跟随的是彼得。彼得曾经根据需要(即听众的状况)有取舍地做教导,而非连贯地陈述主的训诲。因此,马可照着自己的记忆做记录,可谓是无可指摘。他毕竟没有删减自己听到的教导,更未篡改其中的任何内容。[2]
对于马可福音及其作者,这份来自亚细亚省的古老见证包含几个重要声明。首先,马可没有跟随过耶稣本人。第二,马可是彼得的同伴及讲道助手。第三,马可的记录准确无误,然而他从彼得听到的事情“并非按照……时间顺序”。第四,马可是彼得讲道时的“解释者”。
“解释者”的确切意思我们并不清楚。它或许是翻译者的意思,有些学者赞同这种见解。[3]在这种情况下,马可的职责一定是把彼得的亚兰语讲道翻译给希腊语听众。但问题是,彼得也像马可一样懂双语。所以这个词更可能的意思是,“马可把彼得的话笔录在这卷福音书里,对整体教会来说,他便成了彼得的解释者”[4]。正如彼得珍藏并宣扬了耶稣的话语,“马可也同样珍藏并宣扬他所敬重的拉比彼得之宝贵言语”[5]。
约翰长老的直接见证,似乎只限于优西比乌在上文所引的第一句话,其他引言则是帕皮亚的个人评论。不过帕皮亚指出,自己代表并传递的是约翰传统。这个见证的内容可追溯到使徒时代。
长老这个见证,显然是要回应诋毁者的攻击,并捍卫马可福音。许多人质疑这卷福音书,比如它的“疏漏”,没有“按照顺序”记载,以及某些内容的可靠性。长老这个辩护表明,这些批评声浪涌起时,其他福音书正被人用来与马可福音作比较。
长老和帕皮亚对这些批评的回应是,马可福音的特点与局限是因其出处而产生。它如实地记录了老年彼得的公开见证,但彼得不总是按照时间顺序分享信息,而是根据听众的需要做了调整。这便解释了这卷福音书为何会有目前的“疏漏”及顺序。马可忠实地再现了彼得的见证。于是,帕皮亚传统坚称马可福音的真实来源是彼得本人。
优西比乌在公元326年的作品中,曾引用关于马可福音来源的这一解释。该事实表明,这个解释得到了教会的认可。优西比乌显然不知道其他解释,也不认为对此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然而,优西比乌并非单单因为帕皮亚的解释年代久远便接受它,这从他轻蔑地拒绝帕皮亚的千禧年观便可见一斑。优西比乌接受帕皮亚的这个解释,是因它真实可靠。
帕皮亚的主张也得到其他早期见证人的支持。公元150年左右,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the Martyr)在《与特来弗对话录》(Dialogue with Trypho)第106章,引用了源自《彼得回忆录》(Memoirs of Peter)的马可福音3:17。学者们认为,马可福音有一篇写于公元160-180年的拉丁文序言残卷,被称为《反马西昂序言》(Anti-Marcionite Prologue,“马西昂”又译“马吉安”)。根据这篇序言,“马可……是彼得的解释者。彼得死后,马可在意大利地区写下了这卷福音书”。这份文件不但与帕皮亚的见证一致,还进一步明确马可福音是彼得死后于意大利写成。
高卢里昂(今属法国)的大主教爱任纽(Irenaeus,公元140-203年左右),约公元185年在其名著《反异端》(Against Heresies,3.1.1)的某个段落中指明了四卷福音书的作者:“在这些人(即彼得与保罗)死(希腊语为exodus)后,彼得的门徒与解释者马可,也将彼得的讲道内容用书面形式传给我们。”
爱任纽论到,马可是在彼得与保罗“离开”(exodus;出埃及记即由此得名)后写成这卷福音书。人们对此理解不一。曼森(Manson)[6]主张马可福音在彼得死前写成,他认为爱任纽的exodus一词意思应为彼得、保罗“离开”罗马。然而上下文更支持exodus解作“死亡”之意。韦纳姆(Wenham)在其近作《再思对观福音的写作年代》(Redating Matthew, Mark & Luke)中认为,exodus一词“解作‘死亡’非常符合上下文语境”。他认为,爱任纽以上声明的要点是,“使徒的见证在他们生前身后都具有连贯性:马可将彼得口授的内容用书面形式传了下来”。然而韦纳姆强调:“爱任纽并没有说马可在彼得与保罗死后写下这卷福音书,而是说他将彼得的讲道内容用书面形式传给我们。”[7]因此,韦纳姆主张马可是在彼得生前写下这卷福音书,但该书是在彼得死后把他的讲道继续“传递”或“传了下来”。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克莱门”又译“革利免”;公元195年左右)提供了一份稍微不同的报告,被记在优西比乌著作的两处。根据优西比乌的引述,克莱门曾提到:罗马有许多听过彼得讲道的人,要求“长时间跟随彼得并能记住彼得讲道内容的马可将其记录下来。马可完成后,便将福音书交给那些人。当彼得知晓此事,他既未阻挠,也没有鼓励”(《教会史》,6.14)。然而在另一处,据说克莱门又提到:彼得在圣灵启示中得知马可写作福音书一事,“他对信徒们的热心感到喜悦,并批准各教会使用这卷福音书”(《教会史》,2.15)。马可在他人催促下写作此书的可能性极大,但他在彼得生前写成此书却不大可能。因为这与爱任纽、《反马西昂序言》,以及帕皮亚的早期见证均有抵触——如果帕皮亚原话“照着自己的记忆”的主语是马可、而非彼得,这其实是最自然的理解。
优西比乌(《教会史》,6.25)也引用了奥利金(Origen,又译“俄利根”;公元230年左右)的见证,指出马可是在“彼得引导下”写成这卷福音书。彼得亲身参与了福音书写作,这种说法似乎是早期传统为强化福音书使徒权威性而有的。
因此,第二卷福音书由“彼得的解释者”马可写成这个传统可追溯到2世纪早期,且源于早期基督教的三大中心——亚细亚、罗马(与高卢)以及亚历山大。如果马可没有撰写这卷福音书,教会实在没理由将作者指定为马可这样的年少之人。这一点增强了教会传统的可信度。此外,该福音书的古代标题Kata Markon(“根据马可”),也支持这个一致的传统。因为该标题显然是要指明其作者,而非信息来源。否则,这个标题就应当是Kata Petron(“根据彼得”)。
人们普遍赞同,帕皮亚见证的那位马可就是新约中的约翰·马可。泰勒(Taylor)评论道:“这个观点在今天几乎没有任何异议。”[8]凡在这一点上提出的反对意见,几乎都没什么市场。[9]
没有证据表明,罗马教会还有另一个马可能像帕皮亚和新约宣称的这样跟彼得关系密切。人人皆知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与彼得关系甚密,最适合撰写这卷福音书。我们便很难理解,罗马教会为何要认可另一位也叫马可的不明信徒之作品呢?新约中的马可形象,完全吻合帕皮亚的传统。[10]
帕皮亚声明马可不是耶稣当初的跟随者,这与马可的名字未曾出现在福音书的事实吻合,尽管使徒行传指明约翰·马可曾住在耶路撒冷。他之所以未直接参与耶稣的侍奉,可能是因他当时过于年幼或缺少对基督的足够委身。在马可福音14:51-52,客西马尼园里的“少年人”正是马可自己。尽管被某些人一口咬定为“完全不大可能的猜想”[11],这却是一个很自然的假设。因为这是对马可插入这件无关痛痒之事的最自然解释,否则这跟当时的情境实在是毫不相干。我们最好将其理解为作者“在他的福音书里加入了一点自传文学”[12],以便指出他跟这些令人不安的夜间事件有何关联。
使徒行传先把这卷福音书的传统作者介绍为“那称呼马可的约翰”(徒12:12)。这两个名字其实是互换使用的,所以称他为“约翰·马可”并不太准确,新约就从未这样用过。约翰是一个常见的希伯来名字,马可(Mark or Marcus)则是拉丁文名字。对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而言,在希伯来名字后面加一个拉丁文(或希腊文)名字极为常见。
在使徒行传中,他三次被冠以这两个名字(12:12、25,15:37),两次被称为约翰(13:5、13),一次被称为马可(15:39)。在新约书信,他总是被简单地称为“马可”。新约书信里的马可显然就是使徒行传里的约翰·马可,因为相关的经文(西4:10;提后4:11;门24节;彼前5:13)总是提到他跟同一群人(保罗、巴拿巴、彼得)在一起,这跟使徒行传里的情形完全一样。这两个名字可能是按照具体处境加以使用。在犹太圈子里,他会以约翰而为人所知;但在外邦人圈子里,他使用的应是拉丁文名字。他的犹太名字在新约书信中完全消失,表明马可的活动范围已变为外邦人圈子。
马可的母亲是一位耶路撒冷的寡妇,她居住的宽敞房屋成了早期教会信徒们聚会的场所。罗大对彼得声音的反应,证实彼得是这个家庭的常客(徒12:12-17)。因此,马可很早便熟悉彼得本人及其讲道。
当巴拿巴和扫罗完成赈灾使命、从耶路撒冷返回安提阿时,他们便带着马可同去(徒12:25)。显然,马可从此就待在安提阿,直到第一次宣教旅行启动。那时,他是以“宣教助理”(英王钦定本作their minister,美国标准译本作attendant;13:5)的身份随巴拿巴和扫罗踏上征程。
由于某些未陈明的原因,马可在别加离开宣教队伍并返回了耶路撒冷(13:13)。保罗认为,马可的这个过错难以原谅。于是,当巴拿巴提议马可继续参与第二次宣教旅行时,保罗对此断然拒绝。因马可而起的巨大分歧,最终导致保罗和巴拿巴分道扬镳。巴拿巴带着表弟马可(西4:10)坐船前往塞浦路斯,保罗则找到一位新同工西拉(徒15:36-40)。
马可从此在圣经里销声匿迹,直到保罗第一次被囚于罗马。保罗在给歌罗西人(4:10)和腓利门(24节)的信中,都转达了马可的问安。在腓利门书,保罗将马可列为“与我同工的”之一。这表明保罗与马可已彻底和好,马可再次积极地与保罗同工。
保罗获释离开罗马时,马可显然仍留在那里。等到彼得抵达罗马,马可又加入了彼得的侍奉。在彼得前书5:13,彼得代表“巴比伦”(显然是指罗马城的一个暗语)的教会向小亚细亚众教会问安,并且加上“我儿子马可”的问安。这封信应该是彼得在罗马殉道不久前写成。[13]
在提摩太后书4:11,即将在罗马殉道的保罗要求提摩太赶紧前来,并加上这样一句富有启发的嘱咐:“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处。”整卷圣经对马可的最后一瞥,让我们看到一个宝贵仆人的形象。他从起初失败的废墟上爬起,最终证明自己是主的忠仆之一。
主张“彼得的解释者”马可为第二卷福音书作者这一传统,与这卷书的内部特征基本一致。马可福音的基本纲要,符合彼得在使徒行传10:34-43口述的福音故事大纲。所以,把这卷福音书当做使徒彼得讲道要理的延展,或许有一些依据。哈里斯维尔(Harrisville)就宣称:“形容马可福音的最好方法,就是称其为一篇讲章,即1世纪听众从基督教传教士和演说家那里惯常听到的那类讲章。”[14]但是,我们实在不需要假设马可开始撰写福音书时,故意把自己局限于再现彼得的讲道。我们必须记住,马可早年在耶路撒冷便已熟悉使徒彼得的讲道。彼得的讲道诚然是马可的主要信息来源,但在成为彼得的助理之前,马可早已对耶稣了解颇多。
当马可开始撰写福音书时,无疑在试图照某种时间或逻辑顺序编排素材。虽然马可福音的内容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帕皮亚却认为马可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主(的)所言所行”,后者的主张似乎也有几分道理。有时候,马可的内容编排好像是主题式。比如2:1-3:6,马可在此组合了一系列抵挡耶稣的事件。也可能因为帕皮亚熟知约翰福音的构思精妙,故而感到马可的叙事不太有规律。
根据传统把彼得作为这卷福音书的信息来源,对经文解释谈不上绝对必要。然而,这个传统若属实,的确能让马可福音的某些特征呈现出更多趣味。[15] 比如,马可福音16:7提到“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和彼得”这个只出现在本卷福音书的短语,便带出几许耐人寻味的感情色彩。又如,传统观点若属实,马可笔下像现场目击一般栩栩如生的许多情节,便丝毫不难解释。在很多地方,马可使用they(他们)来开始一段耶稣的故事(参见1:21、29,5:1、38,6:53-54,8:22,9:14、30、33,10:32、46,11:1、12、15、20、27,14:18、22、26、32)。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些“他们”乃转述自门徒彼得在口述这些亲历事件时使用的we(我们)一词。
马可福音的早期证据几乎一致赞同,这卷福音书是在罗马写成。唯一的例外是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又译“屈梭多模”),他认为马可福音的写作地点是埃及。[16] 然而,若说他的见证比更早的诸多证据更加可靠,实在有些不可思议。泰勒认为,克里索斯托持这个观点是因为他“误解了优西比乌一处含糊不清的陈述”(《教会史》,2.16)。[17]
马可福音的内容与传统观点是一致的。马可选用了许多拉丁词汇,而非对等的希腊词,显然是因为马可的读者更熟悉前者(参见6:27,7:4,12:14,15:15、16、39)。支持写作地点为罗马的事实,还包括马可在福音书中总是详细解释犹太习俗和术语(参7:3-4,12:42,14:12),并对所有的亚兰词汇和句子加以说明(参3:17,5:41,7:11、34,14:36,15:22、34)。尽管以上观察只能证明马可的写作对象是外邦读者,这却与本书在罗马写成的见证不谋而合。
支持罗马为写作地点的更坚实证据,是马可提到古利奈人西门为“亚历山大和鲁孚的父亲”(15:21)。之所以特别提到这两个人,最自然的理解是他们二人被马可的读者所熟知。罗马书16:13指出,鲁孚正是罗马教会的成员之一。
总之,马可的写作地点应当是罗马,这卷福音书没有任何与该传统观点不合之处。我们对布鲁克斯(Brooks)的结论深表赞同:“这卷福音书最有可能的写作地点及最初读者群,都是在罗马。”[18]
有关马可福音写作时间的传统证据,彼此间有些分歧。如果照更自然的方法理解其见证,爱任纽应该认为写作时间是在彼得和保罗死后。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反马西昂序言》。帕皮亚的见证没有明确涉及这个主题,但他大体同意爱任纽的立场,因为爱任纽似乎是从帕皮亚处直接提取的见证。
另一方面,亚历山大的克莱门与奥利金却认为马可福音写于彼得离世前。这种观点令福音书写作的时间范围变得宽广许多。格思里(Guthrie)认为,“马可在彼得生前动笔撰写,又于彼得死后成书——这种可能值得我们更多考虑”[19]。在这个前设下,上述分歧便可冰消冻释。马丁代尔(Martindale)认为马可福音成书于彼得生前,正式发表却在公元64年彼得离世以后。[20]但是,这种观点较不可能。
我们若接受爱任纽的观点,认为马可福音写于彼得死后,最早的写作日期就会是公元64年,因为这是大家公认的彼得在尼禄逼迫下殉道的时间。然而,人们通常主张的写作日期是公元65-68年。泰勒认为:“公元65-67年是最有理据的。”克兰菲尔德(Cranfield)对此表示赞同。[21]
认为马可福音写于彼得生前的学者们,提出的写作时间各不相同,分别在公元45-60年这个跨度内。这种观点以为,爱任纽所说彼得的“离开”不是指他的离世,而是彼得离开他和马可曾共同服侍的地方。这样一来,爱任纽与克莱门的见证就彼此相合了。然而,这却与《反马西昂序言》相抵触。
人们公认,彼得到公元63年才抵达罗马。所以,比这更早的写作时间似乎都在暗示马可福音是在罗马以外的地方写成。然而,这不符合上文所述有关写作地点的公认传统。
韦纳姆坚定支持马可福音在较早时期写于罗马,他认为彼得与马可实际上早在公元42-44年便在罗马一起同工了。他根据使徒行传12章,为这趟前往罗马的旅程提供了适当背景:彼得从希律王手下奇迹般地逃生,深夜拜访马可家,然后“往别处去了”(17节)。韦纳姆认为马可与彼得一同往别处去了,“即或不然,他也很可能被迅速传唤至彼得那里”[22]。彼得的工作促成了一间活跃于罗马的教会。然而,在安提阿外邦人中极为成功的福音事工却“在耶路撒冷与安提阿之间产生出巨大张力,这很可能成了彼得离开罗马的原因。亚基帕已经死了,教会却面临自诞生起最为严重的危机。这位大使徒会觉得放下一己侍奉,前去处理危局,乃责无旁贷之事。无论如何,当扫罗和巴拿巴于公元46年带来赈济饥荒的款项时,我们看见彼得的确在耶路撒冷”[23]。韦纳姆的研究结论是,马可福音“很可能写于使徒彼得生前,在公元42-44年彼得停留罗马之后,马可与保罗、巴拿巴踏上宣教旅程之前”[24]。
如果彼得躲避希律亚基帕的藏身处果真是罗马,马可福音写于较早时期便非常可以接受。韦纳姆最终认为,马可福音写于公元45年。[25]
另一方面,某些学者主张写作时间在公元70年以后。[26]他们声称,这样才能让这卷福音书包含的福音传统在教会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起来。[27]有人以为,这卷福音书的作者不过是把早期教会不断发展的耶稣传统收集起来罢了。上述学者的意见,只对这样的人有价值。为了支持公元70年之后的写作时间,这些人极力主张13:14“那行毁坏可憎的”是一种有意模糊化的表达,因马可是在耶路撒冷被毁(译注:该事件发生在公元70年)之后写的。然而,作者如果在基督的预言实现之后写作,他应该写得不这么模糊才对。根据基督在第13章的末世讲论来论证马可福音的写作时间,这是无效的,除非我们否认基督预见未来的能力。
总之,我们缺少足够资料来界定马可福音的确切写作时间。尽管更早期的写作时间不无可能,这卷福音书发表于公元64-67年间却是最有可能的。
与约翰福音不同的是,马可福音没有指明其写作目的。要想理解其目的,就必须评估这卷福音书的内容。
马可福音的开篇暗示我们,马可有意将耶稣基督的故事呈现为“好消息”,即基督教的独特信息。他立即介绍耶稣正式、公开的侍奉,刻画出耶和华忙碌工人的形象。但是,马可一开始就认定耶稣是“神的儿子”(1:1),这强调了一个基本真理:我们必须依据耶稣的独特位格看待其服侍。他不但是上帝的弥赛亚,也是他的儿子。这卷福音书描绘的忙碌工人是耶和华的大能仆人,作为神子,他也展露出胜过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的能力。透过讲述耶稣的奇妙事迹与精湛教导,马可让这份记录本身去为耶稣那独特、显著的位格去作见证。耶稣那大有能力且充满仁爱的侍奉,宣告了“神的国(在他里面)近了”(1:15)这一事实。马可的目的不只是讲述一位伟大宗教老师的故事,也是宣告耶稣基督的到来乃是希伯来众先知曾宣称、犹太教也长久期盼的那个拯救事件。马可的基本目的是要传福音,使人归信基督教信仰。
马可的记述也把耶稣基督描绘为耶和华受苦的仆人。他清楚写明,耶稣大有能力的侍奉,很快就被人们不信与公然敌视的阴影笼罩。误解他、攻击他、拒绝他的,正是他来服侍拯救的那些人,因为耶稣没有满足他们对弥赛亚先入为主的期待。其实,受苦也是弥赛亚不可避免的命运。耶稣受苦并受死的图画,在这卷福音书中赫然耸立。与每卷福音书一样,十字架与复活都是基督的中心。理解马可描述的关键,是他故意将神子耶稣的人格尊严与他甘愿承受的痛苦被拒二者间所做的比较。这幅图画融合了举世无比的力量与令人惊奇的顺服,透过明显惨败获得的荣耀胜利。布鲁克斯评论道:“像马可福音这样平衡的基督论,不利于那种认为马可是在辩驳异端的理论。马可特别关注、强调耶稣的受苦和死亡,以此成为罪人的赎价。”[28]
马可福音并非一本耶稣的传记,而是在勾画救赎的“好消息”如何透过耶和华受苦的仆人成为现实。马可呈现的这画面与耶稣宣告的目的完全一致,即“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众所周知,马可福音是四福音中最短的一卷,篇幅还不及路加福音的三分之二。部分原因在于马可略去了耶稣诞生的叙事及其家谱。耶和华仆人的故事,不需要花费笔墨描写他的出生和世系。对仆人而言,首要的关注点不是血统,而是其表现。但是,这卷福音书篇幅较短的主要原因是马可几乎排除了耶稣所有的长篇讲论,只有两个例外(4:1-34、13:3-37)。即使是仅存的这两篇讲论,也比马太福音中的平行段落明显要短。
这卷福音书是一部典型的“行动之书”(a book of action),里面记载的事迹一件接着一件,令人目不暇接。所以,它不无道理地赢得了一个称号,“行动的福音书”(the go Gospel)。[29]马可使用希腊文副词euthus(意思是“立即,马上”)的次数,比其他三卷福音书里的总次数还要多。此外,他也频繁使用“然后、于是”(and)一词衔接不同的事件。
马可福音的首要重点落在耶稣的行动上,形象地刻画出基督那持续不断、坚忍繁重的工作。他总是忙碌不已。四福音中,唯有马可记载耶稣曾经忙得没有时间吃饭(3:20,6:31)。人们总是带着各种需要不断来到耶稣面前。有人发现:“如果一气读完这卷福音书,你会感觉自己被人群团团围住,被各种需要搞得精疲力竭,甚至遭到鬼魔猛烈攻击。”[30]
在这卷书的记载中,耶稣所行的神迹占据了显要位置。相对于总体篇幅,马可福音比其他三卷福音书花费了更多的笔墨来描写基督的神迹。
马可对耶稣的系统教导记录得较少。他多次提到耶稣在教导,却没有记下具体内容(1:21、39,2:2、13,6:2、6、34,10:1,12:35)。在马可福音中,许多耶稣讲论的片段都是从耶稣与犹太领袖辩论时冒出的(参2:8-11、17、19-22、25-28,3:23-30,7:6-23,10:2-13,12:1-11、38-40)。这些片段成了以上叙事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在马可笔下,耶稣的教导事工也成为耶和华仆人工作的一部分。
马可福音有一个特征,里面的许多记述富含细节,栩栩如生。尽管某些事件记载得十分简略,与其他福音书平行的事件却往往极其详尽。马可笔下的事情常留给人一种印象,即这些情节是由当时的亲历者提供,且带有亲历者口述的特殊烙印。马可对历史现在时(the historical present tense)的大量运用,营造出一种让故事在读者眼前徐徐展开的效果。马可对事件的呈现活泼有力、通俗易懂,有时甚至让结构显得松散,表达也略显粗糙。有好几次,马可在只需一次表述的地方使用了两次(参1:35,2:4,4:5,9:2,11:1,13:1、19、35,14:61)。
马可以非凡的坦诚记载了这些故事。他没有给众门徒戴上光环,反倒如实记下他们在许多事件中显而易见的迟钝(4:13,6:52,8:17、21,9:10、32)。他甚至不避讳指出,门徒有时也胆敢批评指责耶稣(4:38,5:31)。家人们对耶稣的态度不佳,也被马可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3:21、31-35)。
马可福音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耶稣人性一面的各种反应和丰富感情。书中提到他的怜悯(1:41,6:34,8:2)、叹息(7:34,8:12)、愤慨(3:5,10:14)和忧伤悲痛(14:33-34),也注意到耶稣全方位的凝视(3:5、34,5:32,10:23)、手的触摸(1:31、41,7:33,9:27)以及对小孩子的兴味盎然(9:36,10:14-16)。唯有这卷福音书记载耶稣在重重不祥之感下,在最后一次前往耶路撒冷时毅然决然地走在众门徒前头(10:32)。马可不但把耶稣描绘为上帝之子,也将其刻画为一个喜欢与人为伍、甘苦同享的性情中人。许多群众被他吸引,欢欢喜喜地听他讲道(12:37)。马可也留意到人们对耶稣的各样反应。他们对耶稣或惊讶(1:27),或指责(2:7),或惧怕(4:41),或稀奇(7:37),当然也有苦毒仇恨(14:1)。
这卷福音书的基本神学概念,正是基督信仰与生俱来的那些特征。作者开门见山,指明耶稣基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1:1),借此让读者对“高阶基督论”(high Christology;译注:从耶稣基督的神性与超越性入手,进而探讨其人性的研究方法)引起注意。关于基督独特属性的这个声明,在天父的见证(1:11,9:7)、鬼魔(3:11,5:7)耶稣自己(13:32,14:61-62)及监督行刑的百夫长(15:39)的话中得到印证。基督的超自然要素透过他满有权柄的教导和所施行的神迹奇事得以彰显,而这些神迹几乎都是在满足人的特定需要。马可的记述表明,耶稣并不喜欢用“弥赛亚”这个称号来指自己,因为该称号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已带有一种对耶稣救赎使命不利的涵义。耶稣为自己选择的称呼是“人子”(在马可福音共出现14次),并将其与以赛亚先知指出的“受苦仆人”概念结合在一起。基于这种身份,他有权柄赦罪(2:10),行使安息日之主的权力(2:28),宣布神国已随着他的出现而临近(1:15)、他最终会在大能和荣耀中再临(8:38,13:26,14:62)。然而,这一切都要求他先照着先知预言的那样来受苦(8:31,9:31,10:33、45)。
马可福音的内容极其适合外邦人。该书既没有马太福音那样浓重的犹太基督徒色彩,也没有假设读者能全面了解旧约。尽管书中多次提及耶稣引用旧约,马可本人却只引用了一次(1:2-3)。马可记载的差遣十二门徒事件,没有提到众门徒被禁止向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传道(6:7-11;参太10:5-6)。在基督的末世讲论部分,马可记载了福音要传给万民的训示(13:10);在洁净圣殿部分,他指出耶稣要把圣殿保护为“万国祷告的殿”(11:17,美国标准译本)。作者马可深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全人类而预备。总之,这卷福音书非常适合罗马人阅读,起初也显然是为他们而写的。
[1] 有些学者则主张更早一些的年代。D. F. Wright, “Papias,” in J. B. Douglas,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p. 746,认为帕皮亚的生卒年代为“公元60-130年左右”。James A. Brooks, Mark, Th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p. 18,指出帕皮亚的写作年代应为“公元120-130年左右”。
[2] 优西比乌,《教会史》3. 39。
[3] W. W. Sloan, A Survey of the New Testament, p. 15; Alfred Wikenhauser,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pp. 160-61.
[4] R. C. H. Lenski,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 Mark’s and St. Luke’s Gospels, p. 9.
[5] R. A. Cole,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p. 36.
[6] T. W. Manson, Studies in the Gospels and Epistles, pp. 38-39.
[7] John Wenham, Redating Matthew, Mark & Luke, p. 139.强调字体乃维纳姆所加。
[8] Vincent Taylor,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p. 15.
[9] 这些反对意见包括:① Marcus这个名字过于常见,因而无法借此确定以上两个“马可”是同一人。(我们当然不是靠名字来鉴定作者身份。)② 在哲罗姆(Jerome,又译“耶柔米”)之前,没有证据直接表明这种身份关联。(因为更早的作者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觉得需要强调这点。)③ 作者不可能来自耶路撒冷,因为他明显不熟悉巴勒斯坦的地理。(这个主张无法成立,也几乎无人接受。福音书里没有任何内容,跟一个曾在耶路撒冷度过青年时代之人的正常知识面有明显抵触。)
[10] 更多详情,参见D. Edmond Hiebert, In Paul’s Shadow: Friends & Foes of the Great Apostle, pp. 67-68。
[11] Werner George Kümmel,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p. 69.
[12] Manson, p. 35.
[13] 关于彼得前书的写作时间、地点,参见Charles Brigg,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s of St. Peter and St. Jud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pp. 67-80; D. Edmond Hieber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vol. 3,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on-Pauline Epistles, pp. 122-27; J.N.D. Kelly, 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s of Peter and Jude, Haper’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pp. 26-34。
[14] Roy A. Harrisville, The Miracle of Mark, p. 14.强调字体乃哈里斯维尔所加。
[15] A. T. Robertson, Studies in Mark’s Gospel, rev. ed., pp. 38-43.
[16] Chrysostom, Homily on Matt. 1.
[17] Taylor, p. 32.
[18] Brooks, p. 28.
[19] Donald Guthri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3rd ed., p. 73.
[20] C. C. Martindale,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Mark, p. xiii.
[21] Taylor, p. 32; C.E.B. Cranfield,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Mark, Cambridge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p. 8.
[22] Wenham, p. 169.
[23] 同上,p. 169。
[24] 同上,p. 182。
[25] 同上,p. 238, 243。
[26] B. Harvie Branscomb, The Gospel of Mark, Moffatt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p. xxxi; Ernest Findley Scott, The Literature of the New Testament, pp. 56-57.
[27] D. E. Nineham, The Gospel of St. Mark, p. 42.
[28] Brooks, p. 30.
[29] Manford George Gutzke, Go Gospel: Daily Devotions and Bible Studies in the Gospel of Mark.
[30] Gerard S. Sloyan, “The Gospel of St. Mark,” in New Testament Reading Guide, p.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