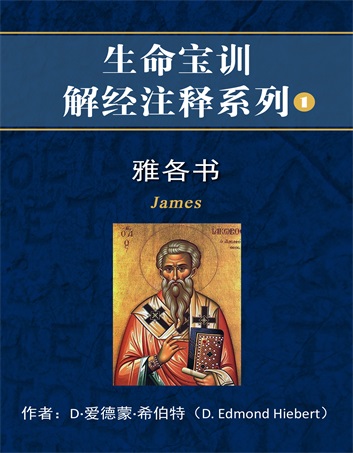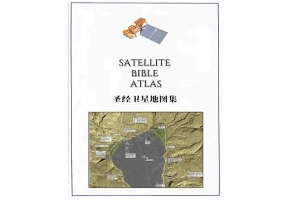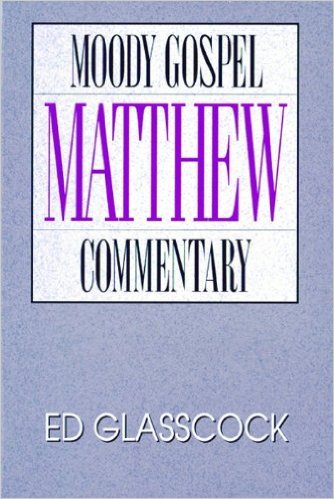导论
雅各书要求,基督徒的信心必须是有功用的信心。活的信心乃是有行为的信心。作者的主要目的是挑战读者,让他们验证自己是否有确实的信心。作者预设他们已经拥有信心,因此这封信并未详细论述有关信心的教义。但是他们必须意识到,福音对基督徒在日常行为中活出更新的生命提出了很强的要求。
这封信严格地坚持基督徒在实践和信仰上一致,毫不留情地蔑视一切空洞的认信,对读者与世界为伍的行为给予激烈的责备。它强调了福音的伦理义务,让这封信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其最初写作的意义。将这封实践性的书信纳入新约正典,在道德感和社会关切上成为基督教会的一座丰碑。
作者身份
这封信起头的问安宣称作者是雅各(James),也许可以更恰当的是雅各布(Jacob)。但是作者只说明了他在属灵上的身份,没有揭示自己究竟是谁。传统上人们认为他是早期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主的兄弟雅各”(加1:19)。现代那些拒绝传统观点、持高等批判观的学者提出了各种替代的解释,并且通常认为这封信的成书年代晚于主的兄弟在世的时期。莫里斯·琼斯(Maurice Jones)说:“保守立场和先进的批判立场在雅各书上产生的鸿沟,比他们在新约任何其他书卷上的分歧都要大。”[1]
外证
已知最早引用并提及雅各书名字的作者是奥利金(Origen,又译“俄利根”,约公元185-254年)。[2]他常常把这封信当作“圣经”来引用,并随意从中得出各种教训。他意识到这封信并未被人普遍地接受(Commentary on John〔《约翰福音注释》〕19.6),但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怀疑其正典性质。有时他会称此信的作者为使徒雅各。当他在《马太福音注释》(Commentary on Matthew, 13.55)中讨论耶稣的四个兄弟时,奥利金花了不少笔墨来描写雅各的公义和名声,说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1:19中提到的雅各,也是犹大在犹大书前言中提到的兄弟雅各(犹1节)。尽管没有明说,但是整个讨论给人的印象是,奥利金将雅各书与主的兄弟联系在一起。
假托罗马的克莱门(Clement of Rome,“克莱门”又译“革利免”)所作的《论童贞的两封书信》(Two Letters Concerning Virginity, 1.11),将雅各书称为“圣经”。但是,这两封信似乎是3世纪上半叶在巴勒斯坦或叙利亚的作品。
优西比乌(Eusebius)在其著名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公元325年)中,将雅各书列为“引起争议的经卷”(antilegomena),即某些教会尚未完全承认的经卷(3.25)。优西比乌明确地区分了引起争议的经卷和那些应当无条件拒绝的伪作。他承认自己列出的作品尚存争议,“但是广为人知,得到许多人的承认”(3.25)。在另一处谈到主的兄弟雅各,“就是人们说写了第一封普通书信(general epistles)的人”时,他指出有些人怀疑这一点,并且“古时候很少有人提及这件事”。但是他的结论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大多数教会都公开使用这些(大公书信〔the catholic epistles〕)”(2.23)。
优西比乌暗示,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约公元155-220年)认为雅各书和其他普通书信都是原作(《教会史》,6.14)。威肯豪泽(Wikenhauser)指出,“在亚历山大的克莱门那些众多的作品中一处也没有引用雅各书”,因此他认为“除了优西比乌给出的证据,究竟克莱门是否接受此信为正典,是一件可疑的事情”。[3]萨蒙(Salmon)根据克莱门作品的拉丁译本,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4]
公元367年,阿塔那修(Athanasius,又译“亚他那修”)在其第39封“复活节文告”(festal letter)中记载了官方认可的正典。他引证说:“按照我们现在遵照的顺序,他将七封大公书信列为一组,放在使徒行传和圣保罗书信之间。”[5]
德尔图良(Tertullian,又译“特土良”,约公元160-215年)、爱任纽(Irenaeus,约公元140-203年)、西普里安(Cyprian,又译“居普良”,约公元200-258年)或希坡律陀(Hippolytus,卒于公元256年)现存的作品中,没有任何对雅各书的引用。代表罗马教会所承认之圣经正典的《穆拉多利经目》(Muratorian Canon,约公元180年)也没有提到这封信。大约公元359年写于非洲的《切尔滕纳姆书目》(Cheltenham List)也没有提到雅各书。[6]在古拉丁文译本各个主要抄本中,也缺少这封信。
雅各书很晚才被叙利亚教会接受,但是彼得前书和约翰一书同样也拖延了许久。这封信被收录在5世纪早期的别西大译本(Peshitta Version)中。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勒(Theodore of Mopsuestia,约公元350-428年)拒绝了这封信,但是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Salamis)主教伊比芬尼(Epiphanius,又译“伊皮法纽”,约公元315-403年)却在自己的新约正典中列出了该作品。
耶路撒冷的西里尔(Cyril of Jerusalem,约310-386年)在他给出的目录中收集了我们所有的正典作品,只遗漏了启示录。他迫切地警告说,不要采纳任何别的作品。
西方教会最早明确地引用雅各书的作品出现在4世纪中叶。普瓦提埃的希拉利(Hilary of Poitiers,约公元315-404年)和安波罗修(Ambrosiaster,约公元339-397年)的作品甚至直接引用了此信的经文。在哲罗姆(Jerome,又译“耶柔米”,公元345-419年)和奥古斯丁(Augustine,公元354-430年)的影响下,这封信渐渐得到了西方教会的普遍承认。在罗马会议(synod of Rome,公元382年)和迦太基会议(synod of Carthage,公元397年)上,它被收入了正典。尽管哲罗姆在武加大译本(Vulgate)中收录了这封信,但是表达了某种怀疑。他在《光明之人的生活》(Lives of Illustrous men)(第2章)里提到,这封信是由另一个人冒了主的兄弟雅各之名发表的。纳西昂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公元330-89年)、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又译“屈梭多模”,约公元344-407年)以及别的一些人也接受了这封信,但是正如哈蒙(Harmon)所见:“即使那些接受此信的教父们也很少使用它。”[7]然而,莫(Moo)恰当地评论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强调雅各书并未被拒绝,而是受到忽视。”[8]
间接的证据表明,早在2世纪人们就知道雅各书的存在。克莱门的《致哥林多人书》(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约公元90-100年),特别是黑马(Hermas,约公元90-140年)的《牧人书》(The Shepherd),明显受到此信的影响。[9]莫法特(Moffatt)和劳斯(Laws)都认为,根据黑马对雅各书的依赖关系,可以清楚地确定雅各书最晚的成书时间。[10]威肯豪泽指出,根据克莱门和黑马的证据,“许多学者推断,雅各书早期在罗马就广为人知,受人尊重,只是后来被遗忘了而已”。[11]
米顿(Mitton)指出,既然这封信被收入普通书信之中,就间接地证明了传统观点对其作者的确信。他说,这封信甚至排在耶稣最早的门徒彼得和约翰的书信前面,“只能解释为它的作者是主的兄弟,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极有影响力的领袖之雅各”。[12]
外证显示,雅各书慢慢地流行起来,后来终于赢得了正典地位。莫法特的结论是,这一证据“更清楚地支持雅各书是后来伪造的这个假设,它不是早期教会的作品”。[13]尽管戴维斯(Davids)也承认这种解释的可能性,但是他指出:“人们对这封信的兴趣不大,它缺少流通性——这种理论也能解释上述证据。”[14]保守的学者们相信,现有证据不能决定性地证明此信是后来的伪作。他们强调应当更慎重地考虑2世纪的证据,假定此信早就存在,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格思里(Guthrie)辩称:“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2世纪的证据。”[15]对于早期环绕此信的谜团,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
随着基督教在外邦人中发展出自己关注的独特问题,一封专门写给犹太基督徒教会的信件,显然无法引起整个教会的普遍关注。此信简洁和极为注重实际的性质,在那些主要关注教义的人看来,只具有微小的重要性。米顿指出:
从事宣教的使徒之作品,因其特别强调信心等福音性教义,要比一位在教会里并不主要负担传福音或宣教的使徒所写的信,更容易被人称许。[16]
这封实践性的书信很容易被那些关心如何捍卫基督教义真实性的人忽略。
另外,一封写给某个特定教会的信,特别又是教会的创始人所写的,最可能被该教会珍视和传播。而一封普通书信,因为没有任何特定的基督徒群体自觉地负起直接的责任,倒是不容易传播开来。
这封信的作者没有宣称自己有使徒权柄,也是它被人忽略的原因之一。它的作者自称为“雅各”——一个古时候很常用的名字,因此那些不熟悉其历史的人,自然会怀疑其真正的作者是谁,质疑其正典地位。而那些对作者和权柄存疑的人,当然不会积极地推广此信。相应地,这封信的流通范围“异乎寻常地狭隘,仅限于残存的基督教会中一个微小的局部之内”。[17]造成这种情况的真实原因是,犹太基督教随着耶路撒冷的毁灭而遭到重创。[18]这一事件标志着,作为众教会的母会,在主的兄弟雅各领导下的耶路撒冷教会所发挥的犹太基督教力量结束了。因此赫德(Heard)说:“雅各一开始的威望,在教会最初的日子里显得如此崇高,但很快就随着耶路撒冷教会失去领导地位而衰落了。而雅各也变成一个模糊的影子,仅仅在保罗书信少数提到他的地方为人所知。”[19]
当雅各书变得比较知名以后,人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它对于教会整体的属灵价值。奥利金和其他教会领袖们重新发现了它,让它焕发了新生。当这封信最终被普遍认识之后,关于其署名作者的身份和权柄之疑问自然导致人们怯于承认其正典地位。它所受到的忽视又自然成为进一步怀疑的沃土,特别是当教会提高警惕,认识到鉴别伪作的需要时,更是如此。
内证
人们对这封信本身收集到的关于作者的证据,有着极为不同的评价。
传统观点的论证
开篇的署名——“雅各、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十分模糊,可以用来指称新约里那几位叫做雅各的当中的任何一位。作者觉得不必澄清自己的身份,这一事实或者源于他在教会里的地位,或者源于他的亲属关系(参犹1节),暗示他非常有名,以至于读者立刻就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在早期基督教群体中如此有名并且叫做雅各的领袖,只有主的兄弟雅各一人。教会传统排除了两位名叫雅各的使徒,将此信归在主的兄弟名下,这一事实“暗示他的身份一定得到某些事实的支持,不是随便为了敬虔的愿望而将此信附会到一位重要人物身上,以便增加其威望”。[20]
如果此信不是雅各所作,那么显然“一位虚构的作者为了努力推荐他自己提出的劝告,几乎不会选择一个这样谦虚的称呼来作为信的开头”。[21]一封伪托雅各的信件应当这样开头:“耶路撒冷大主教雅各,书喻四方众教会。”[22]若是稍晚,他就应当强调雅各与耶稣的关系,说他是主的兄弟。但是戴维斯说,这种关系要“在他死后强调,也唯有在他死后才能强调。”。[23]哈里森(Harrison)指出,主的兄弟雅各(加1:19)在新约中被提及的时候,都只提到“他自己的名字(加2:9、13;犹1节;徒12:17,15:13,21:18)”。[24]这封信充满权柄的口吻,与主的兄弟在早期犹太教会中众所周知的地位相称。
这封信反映出作者的犹太背景,与传统观点吻合。作者非常熟悉旧约和犹太人的思考、表达形式。此信写给“散住各国的十二个支派”,也具有犹太特征。他提到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2:21),也是新约里唯一一位用“全能之主”(5:4,kuriou sbbaōth)这个旧约的称号来称呼神的作者。(新约里还有罗马书9:29用到这个称呼,但是那是对旧约的直接引用。)他非常自由地从旧约中提取各种例子(2:21、25,5:11、17-18),并提到“只有一位神”是信仰的中心事实(2:19)。他熟知犹太人起誓的套路(5:12)。这些地方透露出的作者形象,与新约其余部分所刻画的主的兄弟的形象相符。
这封信与雅各在耶路撒冷大公会议上的讲话(徒15:13-21)以及之后的书信十分相似;那封代表会议决定的信件很可能出于雅各的手笔(15:23-29)。[25]修饰语“亲爱的”(agapētoi,雅1:16、19,2:5;徒15:25),以及劝告的话“请听,我亲爱的弟兄们”(雅2:5;徒15:13)都出现在这封信和使徒行传中。此信使用了不定式形式的问安(chairein),而耶路撒冷会议书信也用了这个不定式(雅1:1;徒15:23)。雅各书和使徒行传都用“回转”(epistrephō)来表示归信(雅5:19-20;徒15:19),都用了“看顾”(episkeptomai)一词(雅1:27;徒15:14)。使徒行传15:24采用的希伯来语短语“你们的心”,也出现在雅各书1:21里(参5:20)。还有人注意到,这封信的措辞与雅各在使徒行传21:20-23里的用语有不少相似之处。[26]
这封信与耶稣的教导,特别是与登山宝训之间存在众多的相似之处。请读者比较下面各处:
|
雅各书 |
马太福音 |
|
1:2 |
5:10-12 |
|
1:4 |
5:48 |
|
1:5; 5:15 |
7:7-12 |
|
1:9 |
5:3 |
|
1:20 |
5:22 |
|
2:13 |
5:7,6:14-15 |
|
2:14-16 |
7:21-23 |
|
3:17-18 |
5:9 |
|
4:4 |
6:24 |
|
4:10 |
5:3-4 |
|
4:11 |
7:1-2 |
|
5:2 |
6:19 |
|
5:10 |
5:12 |
|
5:12 |
5:33-37[27] |
梅厄(Mayor)还列举了此信与马太福音其余部分,以及与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相似之处。[28]但是雅各从未说过他曾引用耶稣的话。事实上,他完全没有让人觉得自己是在引用他人的话语。相反,他与耶稣教导的相似之处,似乎代表了教会在最初的日子里所记忆的耶稣教训。后来,这些教训才被珍藏在福音书的记载之中。格思里进一步指出:“这些平行经文并不是按照任何机械的方式产生的,而是显示了对主的教训背后的观点之真正理解。”[29]戴维斯总结说:“总体上看,这些隐约的引用说明作者长期浸淫在耶稣的教训中,而且这件作品是作者接触书面记录的福音书传统之前就写成的。”[30]这一立场与传统所承认的作者完全相符;但是,若说这封信写成于我们现存的福音书开始流通以后,则很难令人信服。
这封信反映出的读者的情况,也与传统所承认的作者相符。读者的社会经济状况暗示,此信的完成时间应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前。造成耶路撒冷被毁的对抗冲突,极大地改变了犹太人的生活条件。此信所表现出的简单的教会组织结构,以及对基督第二次降临的生动盼望,都更倾向于较早的成书年代。若将此信的成书时间放在主的兄弟雅各在世的年代,并不会构成任何年代上的矛盾。[31]
反对传统观点的论证
有人激烈地反对传统观点所认定的作者。
流畅的希腊文
按照我们所知1世纪巴勒斯坦的语言环境[32],雅各很可能从童年时代就懂得希腊文。伊斯顿(Easton)承认,“鉴于拿撒勒位于繁忙的贸易线路上,我们应当假定大多数拿撒勒人多少知道一点希腊文”,但是他坚持认为,我们不能“超乎寻常地想象”雅各能够写出这封信所具有的流畅的希腊文。[33]然而,他忽略了一点:犹太人是地中海各民族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七十士译本(LXX)标志着犹太人对希腊文化的接受;这个译本很快就成为约旦河以西所有大流散(Dispersion)的犹太人会堂中的标准手册。”[34]塞芬斯特(Sevenster)用下面这番话总结自己对此事的详尽调查:
根据过去数十年所积累的所有数据,我们不能否认1世纪的巴勒斯坦犹太基督徒有可能用流畅的希腊文写成这样一封信。[35]
而且,莫尔顿(Moulton)断言:
没有人敢轻率地假设,那些声称从最早的一批信徒之中流传出来的作品不能采用希腊文写成。他们写作起来就和从小使用希腊文的人所写的一样,而不像痛苦地采用不恰当的成语来表达意思的外国人。[36]
这封信用流畅的希腊文写成,但若说它是“精彩的希腊文”,则是对它的文学品质过誉了。罗伯逊(Robertson)断定:“在正式的修辞技巧上,希伯来书的作者以及路加和保罗都远在他(雅各)之上。”[37]扎恩(Zahn)指出,这封信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其雄辩发自内心,直击良心,绝非学过修辞的学究所为。”[38]
尽管用精确的通用希腊语(Koine Greek)写成,此信的语言却带有明显的希伯来文色彩。“希腊的思维表现形式,”奥斯特利(Oesterley)说,“似乎打上了希伯来语的模印。换句话说,作者似乎非常熟悉希伯来的思维方式,习惯于用希伯来语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因为他用希腊文写作,因此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要折返到希伯来语的模式之中。”[39]伊斯顿完全意识到这种犹太色彩,所以他认为此信的文学形式暗示作者是一位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受过希腊化的修辞训练,但拥有坚实的希伯来宗教背景。”[40]这一文学现象造成了某种引人注目的情势。自由派学者通常认为,这一现象排除了传统所认定的作者。支持传统观点的人进一步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雅各确实相当熟悉希腊文,能够写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封信。若雅各从儿时就熟知希腊文,那么他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地位应当需要他进一步精通这门语言。从一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就有一些希腊化犹太人,一群在家里完全使用希腊文的人。每天和这些希腊化犹太人接触,以及在公开演说和辩论中不断地练习,给了雅各众多的机会让自己精通这门语言。雅各也完全可能在耶路撒冷找到正式地学习这种语言的机会。[41]或者,雅各具有特殊的语言天赋。米顿说:“雅各一定是一位智力相当出众之人,有能力快速地上升到他所在的高位。对于他这样不同寻常的才智之士而言,实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并不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42]
另一种解释是,雅各使用了一位饱学的文士,简略地告诉他“自己想要说的话,并让这位文士自由地形成文字”。[43]贝莱斯·默里(Beasley-Murray)支持这种观点,他断言说:“在新约成书的希腊化时期,甚至写信的时候也很少有作者以自己的语言和风格完成最终稿;作者对文士写作技巧的依赖性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44]塞芬斯特质疑这一断言,认为“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并总结说,在新约里“没有哪怕一处无可辩驳的清晰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45]他指出,信中的关键字、双关语、头韵(alliterations)以及将内容组织成简短段落的方式,“让人几乎无法想象一位秘书如何可能在雅各的指示下编写一封这样的书信”。[46]另外,亚当森(Adamson)也说:“若说他期望自己的秘书依靠几句短短的笔记就写成这样的文字,那是承认了一种最不可能成立的假设,即秘书比作者本人更聪明。”[47]
上述任何一种理由都可以减轻此信的语言风格所造成的问题。但是,考虑到目前已知的、主的兄弟雅各生活年代的语言背景,以及成为耶路撒冷教会领袖显然需要的杰出能力,前一种观点是最自然的解释。后一种观点无助于高举“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之观点。
贫乏的基督教内涵
奥斯特利认为,此书从未提及耶稣一生中发生的任何重要事件,让人“几乎无法相信,作者熟悉基督,亲眼见过他的作为,听见过他的教训,却在写信给其他基督徒时,对这些事情保持绝对的沉默”。[48]罗普斯(Ropes)认为,主的兄弟完全不提耶稣基督之死是人类得救的途径,这一点让人难以理解。[49]奥斯特利还发现,此书也完全没有提及基督的复活。若考虑到复活在早期教会讲道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一件难以解释的事情。[50]雅各亲自见到过复活的基督(林前15:7),并且此事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主的兄弟非常不可能是此信的作者。必须承认,这些论证十分有力,但是赫德的回应很得体:
正是因为缺乏对耶稣的生平、死亡和复活的神学解释,从而否定了此书为后世一位不具名的基督徒所写的任何理论;我们最好将雅各的沉默和犹大的沉默一道视为耶稣的兄弟们宣告信心的方式。[51]
不可能是因为作者无知,才让此书缺少了这些基本的基督教教义。在写信给其他基督徒时,作者可以假定读者们熟知这些教义。他出于伦理学目的所写的信里,不必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和主有着亲密的个人关系,所以在讨论这些宏大主题的时候,他自然会有所保留。塔斯克(Tasker)正确地指出,彼得后书因为强调作者和耶稣的个人关系,也常常被认为是伪作,但是所有这一类的论证都属于心态失衡所致。[52]
作者的宣告
还有人根据作者没有宣告自己的使徒权柄、也没有声明自己是主的兄弟这一点,来反对传统观点所认定的作者。奥斯特利认为,如果真的是主的兄弟雅各写了这封信,我们应当发现他提及自己有权柄的地位,从而让这封信可以更加有效地服侍流散各地的读者。[53]
雅各一定与保罗一样,认为从肉体的层面所认识的耶稣,没有重要的属灵意义(林后5:16)。当耶稣复活后向雅各显现(林前15:7),让雅各清楚地认识自己兄弟的真正本性之后,他与耶稣的血缘关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现在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属灵关系。尽管其他人也许会承认他与耶稣的血缘关系,但是雅各觉得自称“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更为合适。耶路撒冷教会著名的领袖是“主的兄弟”(加1:19),这一事实在雅各死后才被基督徒圈子强调。教会认识到,肉体上的关系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拥有更高明的属灵洞见。
希腊化特征
这封信的希腊化文学特征,被有些人用来当作反对传统作者的证据。伊斯顿断言:“雅各书全书以训勉(paraenesis)方式写成,常常采用哲辩形式(diatribe),这一事实表明作者在文学上寻求与希腊读者而非希伯来世界发生联系。”[54]但是这样一些特征并不能得出如此结论。哈里森恰当地指出:“保罗这位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采用了同样的希腊文学手法,包括哲辩法和所有其他的修辞手段来写作。”[55]
读者的情况
有人认为,读者们的悲惨境况指向雅各死后的某个时期。他们断定,信中所谴责的罪需要漫长的发展过程;因此,此信不可能是直接写给早期教会里的基督徒群体的。
这种说法值得斟酌。在哥林多教会成立不久,保罗就对他们提出了众多的指责。使徒行传开始的几章(5:1-11,6:1)显示,早期犹太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并没有免于雅各书所责备的某些罪。诺林(Knowling)指出:“作者所描述的罪和软弱,正是我们的主责备他的同胞——特别是法利赛人这个群体——的那些过失和弱点。”[56]戴维斯相信,这封信所处理的道德问题“甚至可能是新近归信的犹太人身上的过失,他们需要认识到新的信仰所蕴含的意义”。[57]
迪贝利乌斯(Dibelius)对此种论证不屑一顾,认为它毫无联系。他辩称,既然此信是劝勉文学作品,就不可能从内容中提取出任何读者的真实状况。[58]
文学依赖性
试图依据文学依赖性来推导出真正的作者,是一种危险的尝试。[59]莫法特断言:“明眼人一眼可见,这封信不仅依赖于彼得前书,而且部分依赖于保罗书信(特别是罗马书)。”[60]
实际上,我们无法肯定雅各书在文学上依赖于彼得前书或者罗马书。罗普斯说:“即使我们承认文学依赖的存在,也完全不可能确定究竟是谁依赖于谁。”[61]他认为,这些书信的相似性是源于两位不同作者独立得出了相同的想法。论到这一类文学依赖性的说法,格思里巧妙地回答说:“人们最多能够肯定地说,此信的作者拥有基督徒的常识性思维。”[62]
关于作者的其他观点
那些决定不接受传统作者的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其他的观点。
一种假说是,某些不知名的教师以主的兄弟雅各的名义发表了此信。这种伪托的观点遇到很大的困难。莫法特正确地指出:“此信缺乏对使徒个人身份与权柄的强调,十分不利于这一理论。”[63]信中没有任何异端观点,因此难以想象有人具有合情合理的动机来伪造这样一封信。这种论调的支持者们也许会贬损这件作品,将其打上伪作的烙印,但是这样做并没有解决其中牵涉的道德问题。[64]
另外一种假说是,这封信的作者是一位名叫雅各的不知名教师,后来被人误认为是主的兄弟雅各。[65]这种观点对解决传统观点的困难而言算是往前进了一步,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困难。“一位名叫雅各的不知名的作者,一定会意识到他的读者会把他和那位著名的雅各搞混。如果他不是故意想制造混乱,就应当更具体地说明自己的身份。”[66]按照这种观点,我们也很难解释此信充满权柄的口吻和通喻所有教会的性质。若此信因为作者虚假的身份而得以进入正典,它也会面临道德上的指控。而且,这种观点仍然建立在一种未加证实的假说之上。
1896年,F. 施皮塔(F. Spitta)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假说,认为此信本是一位巴勒斯坦犹太人写给大流散中的犹太人的一篇道德训诫集。后来有人增加了一点基督徒的笔触,比如在1:1和2:1加上了耶稣基督的名字,赋予此信基督教的味道。这种假设很不可能成立。“一位基督徒篡改者应当不会满足于仅仅插入这样一点内容,却可能把2:1修改得更清楚一些。”[67]库梅尔(Kümmel)指出,这种假设忽略了“一系列只有考虑其基督教来源才能被理解的特征”,并指出1:18、21、25,5:8、12所包含的教训不可能具有“非基督教的犹太来源”。[68]麦克尼尔(McNeile)断定:“作者的基督教背景在此信的言辞后面发出温和的光芒,是任何编撰方式都无法产生的。”[69]这种理论过分强调信中的犹太元素,忽略了明确的基督教元素,但是帮助我们意识到,不必假定此信来自希腊化世界。
1930年,阿诺德·迈耶(Arnold Meyer)在其《雅各书之谜》(Das Rätsel des Jakobusbriefes)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幻想出来的理论,认为雅各书背后隐藏着一份根据雅各留给12个儿子的最后遗言写成的犹太寓言作品。这件作品描绘了每个支派的传统美德与恶行,而雅各书是按照基督教的需要对此进行的改写。他认为应当寓意化地解释各个族长的名字,而这种道德寓言的处理方式是理解此信如何组织材料的关键。这种理论是伊斯顿的注释基础,但他减少了犹太文献的分量,增大了基督徒编辑的成分。[70]迈耶的理论非常精巧;他提出的线索远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但是,他的整个方法实在太精妙了,不足以取信。塔斯克公平地评价说:·
这样的解释方法也被当作是解决雅各书或者其他任何新约文献来源的一项严肃贡献,这实在是现代圣经批判学令人惊奇的特征之一。[71]
除此以外,还有理论假定此信采取了原本出自雅各的材料(可能是一些讲道的内容),然后由一位编辑对这些原始材料进行翻译、调整和扩展,从而构成现在这件作品的样子。因此,巴克利(Barclay)提出,这封信“的内容出自雅各的讲道,被某人拿去翻译为希腊文,略作增补修饰,发送给了更大范围的教会,好让所有人都读到并从中受益”。[72]如果这种假设的过程事先知会了雅各并征得他的同意,那么就与雅各请了一位饱学的文士执笔的观点没有太大的差别;它不过在真正的作者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封信之间加上了一个假想的联系。
戴维斯为这封信想象出一种更确定的两阶段来源。他提议说:“无论编辑的工作完成于作者生前还是死后,此信的作者可能几乎不认识后来的编辑;后者可能只是将前者的材料编定汇集起来而已。若是如此,我们可以肯定它出自公义者雅各,尽管雅各本人可能对此信的流通一无所知。”[73]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位编辑—汇编者要背着雅各炮制这样一件作品来冒充雅各的书信,或者当他心目中的读者大多数都知道雅各已经离世,他还要做这样一件事呢?而且,这种观点引发我们对神是否默示了这封信的疑问。在有关这封信为何迟迟不被教会认定,很长时间都没有归为雅各原作的问题上,它没有能提供比传统观点更好的解释。
作者其人
信中的形象
作者自称为“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1:1),仅仅提及了他的属灵地位。对于他来说,指出自己是神的仆人并不带有丝毫卑躬屈膝的意思,而是暗示自己像一位仆人一样效忠于神,同时又表达出与神的个人亲密感。这是他自我身份的核心现实。与犹大(犹1节)不同,他显然不觉得有必要说明自己的家庭关系。他似乎极为有名,因此不需要进一步向读者说明自己的身份。
除了在3:1间接地指出自己的教师身份,作者没有再直接提及自己。然而,很少有人可以像此信的作者一样,用同样的篇幅揭示出更多的个人信息。他在信中显明了自己强烈的个性,坚定有力地持守自己的立场。他那明快、简洁而充满权柄的口吻,十分引人注目。他采用的简短而尖锐的句子,就像一支支锋利的羽箭,毫不差池地命中各自的目标。“除了耶稣的演讲,他使用的那种不容分说的语言在早期基督教文献中无人能及。”[74]
他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熟知大自然的运行,并反复从自然现象中引申出教训。他也是人性的精密观察者。“他了解世界的潮流,清晰无误和机智幽默地描写了人的特性;他看出了人类浅薄的善良,懒惰的利己主义,低俗的气质,以及不加约束的空洞思想所带来的危害。”[75]
他有很强的道德信念,对于公义的深刻感受让他无论在何处遇到错误,都会严厉地指出来。他责备的话语尖刻锋利,然而他却是一位天性良善的人。他公开地同情穷人(2:5),看到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5:4)或者在基督徒的集会中受了蔑视羞辱(2:2-4)时,他的怒气就发作起来。他认为,活的信心必须以良善的生命(2:17)和社会关怀(1:27)来体现。
他深深地坚持基督徒的信念。他坚信一神论是信仰的基本原则(2:19)。“他认为神是‘永恒不变的那一位’,各样美善的赏赐都从他而来(1:17),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都由他护佑(4:15)。”[76]他坚信祷告的能力和重要性(1:5,5:14-18)以及内住在我们心里的道(1:18、21)。他完全意识到罪根植于人性之中(1:13-15),并看到不加控制的舌头会暴露出人内心的恶(3:6-8)。他尽管闭口不言,却深爱着基督,将他称为“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2:1)。他等待着基督的再来(5:7)。
作为一位敬虔的基督徒,作者的思想却扎根在犹太的背景中。信中基督教的观念被犹太的形式所包装。在旧约中,爱世界被谴责为背离神,行淫乱(4:4)。他从来没有使用“福音”一词,却似乎用“至尊律法”或者“使人自由的律法”来加以替代(2:8、12)。他谴责口出恶言的行为,将其归入轻看律法之类(4:11)。他自然地回到旧约中寻找例证,但是这封信却没有任何地方提及我们需要遵守犹太的礼仪或献祭。
在圣经中的身份
希腊文名字Iakōbos,在我们的英文版中译为James。这个名字在整个新约圣经中出现了42次,一共有7位不同的人物叫这个名字。
福音书中最常提及的一位雅各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太4:21,10:2,17:1;可1:19、29,3:17,5:37,9:2,10:35、41,13:3,14:33;路5:10,6:14,8:51,9:28、54)。在使徒行传里,他的名字被提到过2次(1:13,12:2)。他和他的兄弟约翰属于耶稣最早的一批门徒。他也是十二使徒中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徒12:2)。
十二使徒中另一个雅各是亚勒腓的儿子(太10:3;可3:18;路6:15;徒1:13)。他似乎也被人称为“年轻的雅各”(James the younger,可15:40,新国际译本)[77],是马利亚的儿子(太27:56;可16:1;路24:10)。他有一个兄弟名叫约西(可15:40)。他的名字与福音书中发生的任何故事都没有关系。
十二使徒中另有一人叫做“犹大、雅各的儿子”(路6:16以及徒1:13,新国际译本)。若按照严格的字面意思翻译,他应被称为“雅各的犹大”(Judas of James)。根据同一份名单中与之平行的“亚勒腓的儿子雅各”(James of Alphaeus),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这里应当译为“雅各的儿子”,而不是按照英王钦定本译作“雅各的兄弟”。这位雅各只是简单地作为十二使徒中某一人的父亲出现。第四福音书进一步说明这位门徒“不是加略人犹大”(约14:22,罗瑟拉姆译本)。
另一位雅各,连同他的三位兄弟,在福音书中2次被叫做耶稣的“弟兄”(太13:55;可6:3)。这群弟兄作为一组,也出现在约翰福音7:3-8以及使徒行传1:14里。在加拉太书1:19中,保罗提到“主的兄弟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里一位重要人物,信主三年以后他专程回去与雅各见了一面。他更提到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三大柱石之首(加2:9),是一位甚至对安提阿教会也有很强影响力的领袖(加2:12)。在使徒行传里另有3次提到雅各,但是都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只是提到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领袖(徒12:17,15:13,21:18)。然而根据哥林多前书15:7和使徒行传1:14,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主的兄弟。他似乎也是犹大书第1节提到的雅各。
在这四人当中,我们可以立刻将使徒犹大的父亲雅各排除在雅各书的作者之外。除了他是使徒雅各的父亲,我们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
认为作者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的观点,支持者寥寥。[78]寥寥几条支持这种观点的抄本证据,都是后人增加上去的。[79]支持这种观点的内证也很少,而且难以取信。这位雅各在公元44年被希律亚基帕斩首而亡(徒12:2)。没有证据表明当时他已经在犹太基督徒中得到了特殊的领袖地位,可以让他有资格写这样一封信。在使徒行传前12章里,他不是一个主要的人物,几乎总是在提及他的父亲和著名的兄弟约翰时,才出现他的名字。因此,他是此信作者的可能性不大。[80]
要从亚勒腓的儿子雅各与主的兄弟雅各中选择谁是作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两个名字是否指的是同一个人。哲罗姆在4世纪提出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这已经成为罗马天主教传统的释经立场。因此,斯坦米勒(Steinmueller)拒绝承认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主的兄弟雅各是两个不同的人,认定早期教会传统已经确认他们本是一人。[81]但是身为天主教徒的威肯豪泽指出“新教徒和现代天主教会内部人数渐渐增加的少数派认为,主的兄弟和亚勒腓的儿子不是一个人”,并认为这种观点更为可取。[82]
若要认定他们是同一个人,就需要假定约翰福音19:25里的革罗罢与雅各的父亲亚勒腓是同一个人(太10:3;可3:18;路6:15;徒1:13)。与语言学上看,这两个名字确实可能具有相同的亚兰文的词源[83],但是朝夕相处的门徒们不太可能用两个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同一个人。翻译古叙利亚文本的人,毫无疑问精通亚兰文的名字和它们的译法,但是他们用了不同的词形来翻译亚勒腓和革罗罢这两个名字。[84]
这种观点还需要假定约翰福音19:25只提到三个女人的名字,于是“他母亲的姊妹”就是“革罗罢的妻子马利亚”。这种看法尽管时有所见,但是不太可能。[85]因为若是如此,那么在一个家庭中就有两位活到成年的姊妹都叫马利亚。参考马太福音27:56和马可福音15:40,约翰提到四位妇人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他把她们分成两对,因此耶稣的母亲马利亚之姊妹,其实应当是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名叫撒罗米。别西大叙利亚文译本(Peshitto Syriac Version)在这里插入了一个连接词,表明译者的理解是约翰提到了四个妇人。
福音书中提到耶稣兄弟的地方,无法与其中一位或几位兄弟属于十二使徒的观点统一。耶稣的兄弟总是代表着与使徒们不同的另一群人(太12:46;可3:31;路8:19;约7:3;徒1:14)。
他们曾试图和母亲一道来检查耶稣密集的事工(太12:46;可3:21、31),因此他们(或者他们中间的几个)不可能属于他的门徒。拿撒勒一带的人提到耶稣的兄弟时,也有别于他的门徒们(太13:55;可6:3)。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约六个月的住棚节前夕,“甚至他自己的兄弟也不信他”(约7:5,新国际译本)。
支持耶稣的兄弟雅各和使徒雅各是同一人的学者们认为,在加拉太书1:18-19里,保罗提到主的兄弟雅各是使徒之一。但是,我们完全无法如此肯定地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保罗的话。保罗所谓“只有(ei mē)雅各”(新国际译本),最好被理解为转折含义,即“除此之外,没有……”;他所增加的“如果不是雅各”(希腊文直译),应当被简单地当作他除了见过彼得和雅各,没有再见任何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86]即使我们同意保罗在这里将雅各称为使徒,他也可能是在更宽泛的含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将教会里各个重要人物都包含在内(参徒14:4、14;罗16:7)。[87]主的兄弟雅各不是十二使徒之一,因此与亚勒腓的儿子雅各不是同一个人,这个结论与作者在这封信的开头问安的时候没有宣告自己拥有使徒权柄的事实相符。
在那些承认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主的兄弟雅各不同的人中间,只有相对少数人认为,雅各书是亚勒腓的儿子写的。加尔文(Calvin)认为这种观点并非全无可能,并认为在加拉太书2:9里被保罗称为“柱石”的雅各是亚勒腓的儿子。然而,他并没有明确肯定地说,究竟是两人中的哪一位写了这封信。[88]似乎“把这封信归于一位本不在十二使徒之内的作者名下,却又赋予作者与保罗相同的使徒权威,让加尔文深感不安”。[89]
巴克斯特(Baxter)这位现代人支持作者是亚勒腓的儿子雅各,他坚持认为,若要认定使徒行传12:17,15:13-21以及21:18-25里的雅各是主的兄弟,就是让路加犯下严重罪行:不加解释就取消了一位使徒的资格,并用另一位不是使徒的领袖来充数。[90]在使徒行传第1章列出所有十二使徒之后,在该书剩余部分一共只提到过三位最初的使徒之名。在福音书里,亚勒腓的儿子与任何故事都没有关系;他的名字仅仅出现在十二使徒的名录之中。一个在福音书叙事中几乎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印象的人,似乎不具有我们的雅各书所反映出的强势和有力的性格。而主的兄弟雅各尽管不是原来的使徒之一,却能在短时间内进入早期教会的领导层,这不仅是因为他与主的亲密关系和耶稣复活之后对他显现的缘故,也是因为他的能力和敬虔的人品。复活的基督亲自向雅各显现(林前15:7),赋予他成为使徒的基本资格(徒1:22)。
我们的结论是,在新约里提到的四个名叫“雅各”的人里面,只有主的兄弟雅各符合作者的形象。我们的发现与传统所认定的雅各书作者一致。
与耶稣的关系
认定作者是“主的兄弟”,引起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作者和耶稣到底是什么关系?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也已经持续了很多个世纪,但是基督徒之间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对此,人们一共提出了三种主要的看法。[91]
伊比芬尼派理论(The Epiphanian theory)认为,这几个兄弟都是约瑟前一次婚姻留下的孩子,因此都比耶稣年长。[92]萨拉米斯主教伊比芬尼(Epiphanius,约公元315-403年)在大约公元375年所写的一封教牧书信中强烈支持这种观点。这种流行于2世纪的观点多次出现在各种伪托的福音书中。[93]这个理论本身并不是完全不可能成立。它受到早期教会的大力支持,因为它可以维护马利亚的童贞性。
支持这个理论的理由之一是,有人认为它能够解释为何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时刻,会将自己的母亲托付给约翰(约19:27)。在那个悲剧时刻,门徒会比马利亚的继子们更同情她的遭遇。如果这几个兄弟比耶稣年长,似乎他们对待耶稣的方式更符合犹太的习俗。在他们试图干涉耶稣的事工(可3:21、31-34),以及公开批评他的时候(约7:2-9),他们的表现不像是弟弟。C. 哈里斯(C. Harris)进一步论证说,如果马利亚在生下耶稣之后还有别的孩子,“教会传统(在事实上)却几乎完全一致地认为她永久地保持童贞,这样的情况应当绝不会出现”。[94]凯洛克(Keylock)回应说,这种论证“十分软弱,因为尽管它已经得到如此充分的发展,仍然无法消除过去反复存在的矛盾”。[95]
这种理论有一个弱点,就是如果这些兄弟比耶稣年长,那么耶稣就不能继承大卫的王位,因为长兄的继承顺位应当在他之前。如果这些兄弟们比耶稣年纪大,那么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们会一直陪在他的母亲身边;当耶稣开始自己事工的时候,他们应该早已结婚组成了自己的家庭,但是圣经留给我们的印象却是他们当时仍旧住在一起。而后来,他们在服侍基督的时候已经结婚,则是一件广为人知的事情(林前9:5)。
赫尔维狄乌斯派理论(The Helvidian theory),是第4世纪晚期一位默默无闻的支持者首先命名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这几位兄弟是约瑟与马利亚的孩子,因此都比耶稣年幼。[96]赫尔维狄乌斯(Helvidius)写于罗马的论文,对罗马教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支持这种观点,人们提出,一位完全不受历史和教义方面影响的读者读到新约的时候,自然会认为这些兄弟是约瑟和马利亚的孩子。除了约翰福音7:3,他们总是和马利亚一起出现,似乎一直是她的家庭成员。马太福音1:24-25说,约瑟“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自然的含义是他们等到耶稣诞生以后才有了夫妻生活。路加说(路2:7)耶稣是马利亚“头胎的儿子”(prōtokos),结合福音书的记录可以理解为,路加暗示后来马利亚还生下了几个孩子。如果路加的本意是教导说马利亚没有别的孩子,那么他可以用monogenēs(用在路7:12和8:42中,表示“独生的”孩子)一词。当路加开始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拿撒勒人把耶稣叫作“木匠”,自然地表示约瑟死后,耶稣作为长子继承了父亲的职业,成为了一家之主。
德尔图良(约公元160-220年)是第一位公开断言这些“兄弟”是耶稣同母异父兄弟的知名作者。他所说的话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与某种业已建立的“永久童贞”的传统相抵触的意思。根据奥利金的说法,只有“一些人”持有相反的观点,因此罗普斯的结论是,2世纪时基督教会里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德尔图良的观点。[97]
赫尔维狄乌斯派理论的反对者指出,主流的古代作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都认为马利亚没有别的孩子。当这个问题得到充分讨论的时候,马利亚永久童贞的理论已经逐渐进入到教会的神学之中。修道主义的情绪让人们不敢去想象,那让永恒之道成为肉身的童贞女马利亚的子宫,居然还孕育了别的婴孩。凯洛克指出,那些有权有势的罗马基督徒妇人认定守贞要比结婚更好,于是被哲罗姆所吸引,对赫尔维狄乌斯的教导进行反驳。[98]
有人断言,(根据犹太习俗)这几个兄弟想要对耶稣事工的方式进行干涉,与他们是弟弟的观点不相符。雅各布斯(Jacobs)对此简洁地回应道:“那些追求邪路的人,不能成为一致性的榜样。”[99]耶稣死前将母亲托付给约翰一事(约19:25-27),被人认为是支持马利亚没有别的儿子之证据。在那黑暗的时刻,她没有一个儿子可以理解耶稣,或者像主所爱的门徒约翰那样同情马利亚。约翰是马利亚的妹妹撒罗米的儿子,他在属灵的关系上比马利亚自己不信的儿子们更为亲近。
哲罗姆派理论(The Hieronymian theory),本是哲罗姆为了反驳赫尔维狄乌斯的立场而提出的。这种理论认为,耶稣的“兄弟们”其实是他的表兄弟,是革罗罢和马利亚——耶稣母亲的姊妹——的孩子。[100]
这种观点依赖于一个很成问题的假设:革罗罢和亚勒腓是同一个人,而革罗罢的妻子马利亚是童贞女马利亚的姊妹。如果他们真是马利亚和革罗罢的儿子,那么他们总是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一道出现,而从来没有与自己的母亲一起出现,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他们是耶稣的表兄弟,我们应当看到福音书作者使用anepsios一词,因为这才是表示“表兄弟”的正确词汇。这种观点还假设有些“兄弟”是耶稣的门徒,但是约翰福音7:3-8却构成了它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哲罗姆无法提出任何早期教会的人支持他新奇的观点。
这个棘手的问题可能永远没有一个让人人都满意的答案。我们完全赞同姆伯特(Mombert)的结论:
耶稣还有弟兄姐妹的观点和任何别的理论一样古老。我们与尼安德(Neander)、温德尔(Winder)、迈耶(Meyer)、施蒂尔(Stier)、奥尔福德(Alford)以及法勒(Farrar)一道,相信这种观点最符合福音书记录。如果排除教条主义的偏见和情绪,这也是最简单、最自然和最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案;否则,我们将毫无希望地陷入到这个混乱不堪的问题之中。[101]
历史和特征
雅各似乎是耶稣的弟弟中年纪最大的,因为在两处耶稣兄弟的名录中,他都排在首位(太13:55;可6:3)。耶稣在地上服侍期间,他的兄弟们没有明白他的真实身份,无法将他与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联系起来(约7:2-8)。但是,当复活的基督向雅各显现之后(林前15:7),一切疑惑都烟消云散。他与其他弟兄一道,成为基督的坚定跟随者(徒1:14)。复活基督的显现,赋予雅各在众多信徒中独特的地位(徒1:22),无疑对他后来成为早期教会的领袖有所帮助。圣经其他提及雅各的地方,比如使徒行传(12:17,15:12-29,21:18-25)和加拉太书(1:18-19,2:6-9)等处,让我们认识到不同的时期里他在耶路撒冷教会广受认可的重要地位。犹大书的问安部分(犹1节)提及自己著名的兄弟,显明了雅各的领袖地位;犹大知道,这样的关系可以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身份。
我们隐约知晓雅各在耶路撒冷行割礼的教会中做领袖,因此知道他具有犹太背景。在耶路撒冷大公会议中,正是雅各的发言平息了犹太弟兄的争议(徒15:13-21)。根据彼得所描述的神带领外邦人信主的作为,雅各明确反对教会里的犹太主义者所提的要求,就是外邦人必须行割礼才能成为信徒。他还建议在大公会议的决议中加上限制性条款,以避免激怒犹太信徒,并挪去向各地犹太人传福音的阻碍。他也提醒自己的听众注意,先知论到以色列未来的话语,正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15-18节)。
雅各的属灵敏感性和开放的心态,使得他可以与彼得、约翰一道承认保罗的使徒身份,以及保罗向外邦人宣教的使命(加2:6-9)。雅各全心全意地赞同如此划分事工的领域,并将自己的事工集中在受割礼的信徒身上。显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耶路撒冷度过,对这孕育了其他教会的母教会之事工给予指导。我们不清楚雅各是否也像他的众位兄弟一样,参与到耶路撒冷之外的布道事工中(林前9:5)。但是,从雅各书的问安部分(雅1:1)以及使徒行传21:21他对保罗所说的话可以看出,雅各也在寻求影响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的犹太信徒之灵命。
当保罗带着救济犹大地区圣徒的奉献回到耶路撒冷时,他向雅各以及众长老报告了自己的外邦人宣教事工之进展(徒21:17-26)。作为回应,他们提醒保罗,有无数犹太信徒“都为律法热心”(20节)。根据所得到的反对派报告,他们恳求保罗顾及犹太人的感受,接受一个折中的计划,表明他并不反对人们遵守犹太的礼仪。雅各向保罗重申了自己对耶路撒冷大公会议关于外邦人的决议之支持(25节),但是现在的建议是基于自己对犹太信徒的温柔同情。从加拉太书2:11-21看来,雅各自己似乎一直遵守着犹太人的饮食规矩。当某些自称“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到了安提阿,拒绝与外邦人信徒一起吃饭时,他们的立场对安提阿的犹太信徒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不能确定他们究竟是不是雅各派去的,但是彼得似乎认定他们所宣扬的饮食规矩得到了雅各的支持。显然,大部分由雅各执笔写成的耶路撒冷大公会议官方通告,明确否认在主要由外邦人构成的安提阿教会里引起纷争的人是他所派遣的(徒15:24)。
作为犹太教会领袖的雅各继续坚持摩西的律法,并不是因为律法是得救的手段,而是因为长期的生活习惯。耶路撒冷大公会议已经解决了外邦人信徒与律法的关系问题,但是并没有一点提及犹太人信徒的地方。因为忠于自己的犹太传统,所以他们继续按照犹太方式生活。
雅各绝不是一位思想狭隘的犹太主义者。在耶路撒冷大公会议上,他与保罗站在一起对抗那些犹太主义者。在阐述会议决议的书信中,他明确表示,犹太主义者无权代表耶路撒冷教会的立场。
雅各表明自己是一位“具有巨大影响力、可敬的人格,而且十分敬虔”的人。[102]他的生命和品格深受教会的尊重,在各种纷争中,众人都认为他是值得依靠的坚固柱石。米顿发现“他具有谨慎保守的气质,不愿轻易冒险损害既有的价值观。但是,一旦他看出从根本上改变教会的政策是智慧之举,他就坚定决断地采取行动。即使如此,他仍然认为自己有责任赢得争议各方的支持,为了和平以及和睦的缘故,呼吁双方做出让步”。[103]
约瑟夫(Josephus)在《犹太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一书中,简短但是显然真实地记载了雅各的死亡。他写道,当公元62年,总督非斯都死后,继任的总督阿尔比诺(Albinus)尚未到来之时,新任大祭司、年轻的亚拿二世(Ananus II)“聚集了大公会和审判官们,把那称为基督的耶稣之兄弟,就是名叫雅各之人并其他数人带到会中受审。他指控他们破坏律法,并判处他们被石头打死”。[104]犹太大众曾经公开谴责了他谋害人命的恶行。[105]
2世纪的基督教作家黑格斯普斯(Hegesippus)有一篇雅各传记,特别强调了他的犹太特征和他在犹太教中的名声。他记载说,敬虔的生活为雅各赢得了“公义者雅各”的称号,还说因他在圣殿中长时间祷告,以至于双膝硬得像骆驼的膝盖一样。当雅各公开地拒绝作出放弃耶稣是弥赛亚的声明后,恼羞成怒的祭司们强迫他爬上圣殿的屋顶,将他从那里推下;但他没有死去,于是他们用木棍把他打死了。[106]这份传记显然保留着传说的成分,夸张了雅各的苦修做法,并夸大了他在不信的犹太人中间的影响力。
读者
身份
雅各书的问安部分,将读者称为“散住各国的十二个支派”(tais dōdeka phulais tais en tō diaspora,字面意思是“致十二支派、那些散住之人”)。这句话有三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观点是,这封信是写给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的犹太人的。“十二支派”是对犹太人的完整称呼,表达了与神立约的百姓理想状态下的合一(太19:28;徒26:7);而“散住”一词则是描述那些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之外的犹太人的专门术语(约7:35)。因此这种观点认为,雅各书采用对犹太民族的完整称呼,是想要把犹太人中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包括在内。麦克奈特(Macknight)断定:“这封信至少部分是为不信的犹太人写的”。他引用4:1-10和5:1-6为证,坚持认为“这些事情不可能是对信主的犹太人说的”。[107]另外,“弟兄们”这个犹太方式的称谓,也可以指所有的犹太人。
但是,这种混合读者的观点不可能成立。雅各起首就对读者说明,自己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对不信的犹太人而言,这种说法会立刻造成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隔阂。相反,“整封信应当都是写给作者和读者同属其中的信仰群体的”。[108]雅各认为自己的读者已经在神的话语中得了重生(1:18),并且成为“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信徒”(2:1)。“他的尊名,就是你们所属的名字”(2:7),几乎可以肯定是指基督之名。他们盼望“主来”(5:7),也可以肯定是基督教独一无二的术语。如果作者有意要把非基督徒犹太人囊括在内,那么这封信缺少引领人把信心建立在基督之上的宣教元素,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另一种观点认为,起首的称呼应作象征性解释,指的是“用古代以色列的通称为符号,象征从中孕育出的整个基督王国”。[109]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必须根据彼得前书1:1来解释雅各书。在彼得前书里,读者被称为“分散寄居者”(美国标准译本直译)。但是,雅各书与彼得前书并无精确的对应关系。彼得没有提到“十二支派”,也没有像雅各那样在“分散”一词前加上冠词(希腊文);彼得着力刻画的是,读者生活在信中所提到的罗马各省,作为少数民族所具有的特征。这种观点所建议的读者身份,似乎难以与雅各书的犹太特征相符。
我们认为,最可能成立的观点是:这封信是写给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之外的犹太基督徒。收信人是基督徒,雅各说他们在“会堂”中聚会(sunagōgēn,2:2),同时又称其为“教会”(5:14)。正如莫所说:“雅各在4:4里使用了阴性的‘淫妇’(moichalides)一词,对于不了解旧约传统将耶和华与百姓之约比作婚姻关系的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110]
一神论而非多神论,被认为是信心无可置疑的基础条件(2:19)。梅钦(Machen)更进一步地指出:
这封信直接谴责的错误是典型的法利赛人的做法,诸如没有行为的信心,没有行动的话语,判断他人,野心勃勃,好为人师,献媚财富和地位,蔑视穷人,披着宗教外衣的贪婪等;而对哥林多前书这样的书信中非常突出的错误,例如拜偶像和不洁的生活,却引人注目地付之阙如。[111]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与这封信的整体形象完全吻合。
读者的地点
除了知道他们散住在各地,这封信没有提到读者所在的具体位置。全信以希腊文写成,没有任何从亚兰文翻译而来的迹象,因此读者似乎是散住在希腊世界或者西方的犹太基督徒。格洛格(Gloag)认为,读者“很可能主要由靠近犹大地区各国的会众构成,也就是说他们大概分布在腓尼基、叙利亚、基利家和地方总督治下的亚细亚行省”。[112]这封信的读者很可能是那些“因司提反的死引发的逼迫,从耶路撒冷被驱赶四散的犹太基督徒”。[113]
使徒行传9:2、11:19以及13:1的证据表明,基督教最早扩散到了巴勒斯坦北部地区。但是,他们是否推进到亚细亚行省那么远的地方,却缺少明确的证据。因此戴纳(Dana)的结论是:“这封信是写给叙利亚的犹太基督徒会众的。”[114]彼得告别耶路撒冷之后(徒12:23),雅各自然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也自然对散住各地的犹太信徒的属灵福祉有着深切的个人关怀。
与雅各的关系
作为犹太人,读者们已经习惯将耶路撒冷视为在宗教上具有领导地位。这种背景使得他们会寻求耶路撒冷犹太基督徒领袖雅各的指导,并从他那里获得教义上的指教和实践上的指引。照顾这些犹太基督徒会众属灵需要的责任,以某种特别的方式落在了雅各的头上。这些会众中的许多成员,在受到逼迫分散出去之前,可能曾经是耶路撒冷教会里的一员。
雅各可能接触过这些会众中的某些人,他们是不同教会的成员,因为生意上的原因来到耶路撒冷,或者前来参加犹太全民性节日。他关心他们的属灵福祉,于是很快就发现他们的情况令人不安。这些情况促使雅各使用书信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也是他在耶路撒冷大公会议之后采用的方式。
写作地点与写作时间
写作地点
那些拒绝这封信为主的兄弟雅各所作之人,将写作地点放在了外邦世界的某处。人们提出了众多不同的写作地点。布兰登(Brandon)认为在亚历山大[115],亨肖(Henshaw)和劳斯倾向于罗马[116],而古德斯皮德(Goodspeed,又译“顾斯庇”)相信最可能的地点是安提阿[117]。这些假说的基础是认为此信带有希腊化的思想和表述方式,而不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主义论调。
若我们接受传统认定之作者,自然会得出此信写于雅各长期所居住之地耶路撒冷这一结论。这种观点与此信所借用的来自自然界的隐喻相吻合。信中提到的“早雨晚雨”(5:7),“是一个特别的天气现象,为巴勒斯坦的居民所熟悉,但并不是更往西去的地区之气候特征”。[118]信中还提到热风(1:11),甜苦两样的水(3:11),无花果树和橄榄树所结的果子(3:12),以及描绘了临近海洋的景象(1:6,3:4),全都让人联想起巴勒斯坦的情景。另外,正如莫所指出的:“1世纪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社会环境,显然为雅各书提供了合宜的写作背景。”[119]
写作时间
那些拒绝传统观点的人,在此信的写作时间上分歧巨大。他们给出的时间跨度从1世纪最后25年直到2世纪中叶。
那些认定主的兄弟是此信作者的人,大体上分为两派,各自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时间。有人认为此信写于雅各晚年,接近他在公元62年殉道的时间;另一些人则认为要更早一些,甚至把它放在耶路撒冷大公会议之前。拒绝传统观点的莫法特认为,上述两个雅各在世的日期中,后一个日期“所带来的心理学和历史事实上的困难,甚至比较早的日期还要多”。[120]
支持较早日期的证据是“一根画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非常细的线”。[121]除了基督教最初的那些特征,例如基督的主权和对他来的日子近了的盼望(1:1,2:1,5:8),这封信缺少基督教的特征。甚至“福音”这个表示基督教之拯救信息的词也很少。
信中所述初期教会的组织形式,也偏向于支持较早的日期。信中提到的“教会的长老”(5:14),与读者属于犹太基督徒会众,他们按照犹太会堂的模式组织聚会的观点相符。不要多人做师傅的警告(3:1),似乎指向某种早期自由风格的组织形式。
信中完全没有提及外邦人以及他们与基督教的关系,表明写作时间在外邦人信徒成为教会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之前。没有提及割礼,可以理解为当时这个问题还没有成为教会争议的焦点。在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之后,割礼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并引发了耶路撒冷大公会议(徒14:27-15:5)。这封信没有讨论犹太人和外邦人信徒之间的社会关系,但在耶路撒冷大公会议之后,这个问题会变得非常尖锐(加2:11-14)。信中没有任何地方直接提及“信心与行为”的争议,最好的解释同样是成书时间早于此问题的爆发。
因此,正如莫所断言的:“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形,即雅各书是写给犹太基督徒的,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就住在安提阿或不远的地方,却完全没有提及大公会议所涉及的问题和决议。”[122]
支持将写作时间定在雅各晚年的人坚持认为,若对照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相应段落,可以隐约看到雅各书2:14-26的教导给出了信心和行为之争的线索。他们认为雅各书是在驳斥保罗的教导,或者曲解了保罗的教训。如果雅各是为了回应保罗关于因信称义的教训而写了此信,那么作为一封回信,他应当更明确地说明自己与保罗的关系。多兹(Dods)坚持认为,雅各书第2章的有关讨论“无法证明作者熟悉保罗的立场。这一章的证据正好相反,因为若作者了解保罗书信,却只给出如此简单的回应,除此之外不置一词,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123]
雅各与保罗的教训并行不悖;他们相互支持,共同应对两种偏离真理的趋势。保罗拒斥的是要有善行才能在神面前称义的观点(罗4:4-5;弗2:8-9);雅各坚持的是,称义之人需要行善,以此作为真正得救信心之明证。得救的信心需要通过生活中的善行显明出来,在这一点上保罗与雅各并无分歧(加5:6;弗2:10)。
更可能的是,保罗的对手将雅各的话抽离原来的上下文,当作反对保罗因信称义教训的武器。雅各书的成书年代,似乎早于“行为”、“善行”、“守律法的行为”等概念有更明晰的区分之前。
支持这封信写于雅各去世前不久的人认定,“基督教要扩散到全体流散的犹太人之中”,需要这么长的时间。[124]但是,只有当我们将1:1里的读者理解为散布在如此广大范围的读者时,这种论证才有力量。如果我们合理地限制读者的范围,那么就不能排除这封信的写作年代更早的可能性。
我们的结论是:占据优势的证据表明,这封信写于更早的时代,即某个早于耶路撒冷大公教会的时间。因此,我们也许可以将这封信的写作年代定于公元46年,至少不会晚于49年。这种观点认为,雅各书是新约最早的一篇文献。
写作主题与写作目的
众所周知,要列出雅各书的大纲极为困难。目前存在差别极大的各类大纲,将这封信划分为不同数目的章节,从两个主要部分直到25个分段都有所见,证明了划分大纲的难度。[125]这封信似乎没有预先计划一个清楚的结构,从逻辑上组织其主要内容。“简单地浏览这封信,”亨德里克森(Hendriksen)说,“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任何大纲都不合适。”[126]学者们常常强调它这种零散的特性,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篇“训勉集”(paraenesis;来自于希腊文单词parainesis,意思是“劝勉,建议”),就是一组道德教训的合集。松格(Songer)说:“将一系列训勉松散地组合在一起,而没有特意要推动某个主题或将作品按照某种思路串联起来,正是训勉集的特点。”[127]因此,古德斯皮德将此书描述为“只是一捧珍珠,一颗一颗地洒落在听者的心上”。[128]亨特(Hunter)断言:“它的形式是如此的松散,任何分析家都会感到绝望。”[129]
但另有一些人没有被绝望击倒,竭力从信中辨识出某种组织秩序,认为雅各按照这个顺序讨论各种独立的主题。斯克罗吉(Scroggie)在信中发现了超过一打的讲道主题,“几乎都是单独进行处理的”。[130]谢泼德(Shepherd)找出了全书“8个讲道与教导性演说所构成的系列”[131],而巴克(Barker)、莱恩(Lane)和迈克尔斯(Michaels)则认为此信由“四个简要的讲道或信息合并而成”。[132]有些人,比如马丁(Martin)[133],发现此信的主体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
还有人认为,这封信的统一性在于它强调了一个单独的道德方面的主题,而不是一个教义方面的主题。基(Kee),杨(Young)和弗勒利希(Froehlich)如此描述这种整体性倾向:“整封信都集中在一个简单的真理上: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无法显明他/她的基督徒身份,那么仅仅‘是’一位基督徒是不够的。”[134]麦克尼尔发现,这封信统一的线索是“一个明显而重要的真理,即如果一个人的信心、他对神的态度没有显出效果,没有在生活中以实际的行为表达出来,那么他的信心是不真实的,他对神的态度也毫无价值”。[135]伦斯基(Lenski)合理地断定:“整封信都在处理基督徒的信心,并显明这种信心应当如何真实无伪、生动活泼、充满果效。”[136]
雅各希望详尽地讨论信心,但是他并不打算对信心的性质进行神学上的阐释。相反,他关心的是信徒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鲜活信心。他认为人因着使人得救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便完全能够拯救人(1:1,2:1),但是他的目的是有效地激励读者,让他们意识到使人得救的信心是生动活泼的信心,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2:20,英王钦定本及和合本)。
读者面临的根本性困难在于误解了因信得救的性质以及这个概念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因信称义应当为我们基督徒品格的发展提供基本的支持。在接受基督之前曾受律法主义辖制的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的行为仿佛在说,仅有真理的知识就足够了;这封信也许是对这种倾向的某种极端反应。“他们认为,信心不是与神在灵魂层面的生动接触,从而带来人生命本质上的改变,并自然地结出善行的果子(2:17、18),而是简单地从形式上承认某种教条而已(2:19)。”[137]雅各认为,他的读者迫切需要试验自己,看看自己的信心究竟是活泼的,还是无生命的认信。据此,这封信围绕这一个基本主题:“试验是否有活泼的信心”。雅各对没有信心的行为不感兴趣,但是他非常重视这一主题,想要说明活泼的信心必须由行为证明其生命力。
在简短的问安之后(1:1),雅各立刻切入了正题:“你们信心的试验”(1:3)。“试验的问题,”戴维斯观察说,“构成了串联整封信的线索。然而就像串起项链的细线一样,因为常常被项链外表的各个特殊装饰所掩盖,所以很多时候自己反倒忽隐忽现”。[138]在1:2-18里,雅各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试验与试探的主题。他劝勉受到压迫和试验的读者们坚定地忍耐,好让自己所受到的试验产生他们期望的结果。因为人类堕落的本性,这样的试验可能变成试探。但是,如此而来的试探并不是出自于神,反而与神在人类事务中采取的仁慈行为相对立。
雅各给出了一连串的六种基本试验,告诉读者他们的信心将会在其中受试。在1:19-27中,他指出信心必须在对神话语的反应中受到试验。在2:1-13里,他进一步讨论说,我们如何对待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也是一种试验,可以揭示信心的本质。信心也必须在所产生的行为中得到试验(2:14-26)。另外,信心是否带来节制,也是它所必须经历的试验(3:1-18)。读者偏爱世俗的倾向,让雅各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处理面对世界时信心如何反应,以及世俗的想法在信徒生活中所体现的各种不同问题(4:1-5:12)。对信心的最后试验是,它是否在任何环境中都依靠祷告(5:13-18)。
雅各书没有采用通常的书信体结尾,而是在恳求众人挽回偏离真理的人时突然结束(5:19-20)。而这正是通过生活中的善行表明他们活泼信心的一种有效方式。
特征
省略
省略是这封信的突出特征。基督被称为信心的对象,在信中被叫作“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2:1),但是没有进一步讨论其位格或事工。信中也没有提及基督道成肉身、受苦、死亡与复活。对于赎罪或未来的生命等教义,雅各书也没有任何涉及。
这封信没有提到割礼、安息日、圣殿礼仪、犹太庆典,也没有警告读者提防异教徒的偶像崇拜及其参与者之罪恶。信中没有任何线索表明教会中存在外邦人基督徒,或者读者的生活受到外邦人各种做法的影响。
此信也没有提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任何个人联系。雅各甚至没有在信中加上任何感谢或表扬读者的话语。除了间接地提到自己是一位教师(3:1),信中没有作者的任何个人信息;相反,保罗书信则到处可见保罗对个人经历的描述。作者也没有提到任何当代的历史事件或个人。
教义上的重要性
作者并不缺乏教义上的确信,但是他这封尖刻的、实践性的书信并没有充分地讨论各种教义。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言行一致地体现基督徒的信仰。他坚持“你们要做实行者,而不要只做聆听者”(1:22,美国标准译本),清楚地表明他熟悉并接受了“道”(word)中的教义内容。这封信包含着大量“压缩状态的神学”。诸如“他选择用真理之道生了我们”(1:18);“那所栽种在你们里面的道”(1:21);“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1:25);“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度”(2:5);以及“他所赐而住在我们里面的灵”(4:5)等短语,都有丰富的教义内涵。然后,这些短语更强调道德层面的意义而非其教义。
这封信多处提及神的属性和作为。雅各肯定神只有一位(2:19,4:12),但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及神的三位一体性。神是宇宙的创造者(1:17,5:4),他也创造了人类(3:9)。他是永不改变的美善(1:17),也是众善之创始者(1:17),智慧之源头(1:5)和先知启示之根据(5:10)。他不试探人、让人陷入罪恶之中(1:13-14),而是赐给他们恩典(4:6-8),垂听他们真诚的祷告(1:5-7,5:15-16)并赦免他们的罪(5:15),但是他也会毫无怜悯地审判那些不怜悯人的(2:13)。
虽然作者言辞谨慎,却在信中揭示出对基督深刻的信心。基督是作者宗教生活的中心和基础,这一点明显体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完全认信的称呼、提及基督的荣耀(2:1)、承认自己是基督的仆人(1:1)等各个地方。他期待基督快快地再来(5:7-9),并在此基础上呼吁基督徒在目前的处境下保持忠心和忍耐。莫指出,雅各赋予再来的基督“末世审判的功能,明白地暗示耶稣是神”。“通过在同一封信中断言‘只有一位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且当他再来时将会审判世界”,雅各阐明了上述立场。[139]戴维斯认为,雅各书反映出“早期教会通常的摇摆性,没有清晰地划定界限;在一处归于神的功能,也许在另一处又说明是基督在执行”[140],从而隐含地表明耶稣是神。
在1:12-15中对试探和罪的心理分析,是这封信的一项独特贡献。而5:14-16这一段,对于教会生活来说具有永恒的价值。
对道德的强调
众所周知,这封信非常强调人的道德伦理。其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道德教训遍布全信,而不像其他书信那样附于教义讨论的段落之后”。[141]雅各从未打算将他的道德训令建立在教义启示的基础之上。他公开地指责社会的不公义,像旧约的先知那样激烈。这样看来,雅各被人称为新约中的阿摩斯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与基督教的关系
在基督教历史的早期,当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差异尚未完全为人所重视时,雅各书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使我们可以窥见使徒行传前面数章所描绘的犹太人基督徒的信仰状况。
那时人们并不认为基督教与犹太教对立,而是认为它是犹太教真正的完满形式。犹太教是花朵,而基督教是它结出的果子。基督教是犹太教盼望的实现,即其隐含的犹太启示之最终显明。按照这样的观点,这封信的特征就颇有益处。因此,这封信为新约正典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我们承受不了失去它所造成的损失。
语言与风格
作者的语气显示他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职位所具有的权柄,以及由此而来的责任(3:1)。他完全确信自己所传达的信息是真实而重要的;他的语气毫无防卫性,也没有任何征兆表明他的观点为人所诟病。这封信有108节,他在其中采用了54个祈使语气的动词,但是并不带有丝毫专横的味道。
他的语言清楚而锐利,鲜活而富有生命力,以精心选择的用词表达了分量十足的思想。他的句子简短而直接,显露出作者富有诗意的想象力。他对明喻和对比的选择颇有品味,偏爱具体而非抽象的想法,将自己的教导以绘画和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显然,他热爱大自然,敏于观察。豪森(Howson)说:“在圣雅各这封短短的书信中,单单从自然现象中拮取的意象,胜过圣保罗全部书信的总和。”[142]
这封信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就是对双关语的使用。所谓双关语,是在连续的分句或句子中反复使用同一个词或其同源词起头的做法。作为示例,请读者注意1:3-6:“忍耐”(3节)和“忍耐”(4节);“毫无欠缺”(4节)和“若有任何人缺少”(5节);“应当求”(5节)和“求”(6节);“不疑惑”(6节)和“那疑惑的人”(6节)。另见1:12、15、21-25,3:2-8,4:1-3。[143]
文学形式
根据开始部分的书信体问安,传统认为这件作品是一封“书信”,但是它缺少通常对读者的感谢致辞,也没有一般书信的结尾。它也没有按照惯例说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此信很可能取材于雅各在教会中原本为着教导事工而开发的材料。显然,将这些材料组织成现在的形式,是为了在收信的教会中公开地朗读出来。
此书的内容与所谓“劝勉文学”(hortatory literature)体裁有关。它与旧约智慧文学——特别是箴言、诗篇和其他劝勉的章节,以及某些旧约伪经——关系密切。它有着明显的痕迹,模仿了登山宝训以及保罗书信中的劝勉部分。此书的劝勉特征与一类叫做“训勉”的文学种类有关。松格列举了这一类文学作品的三个共同特征:(1)罗列道德格言,但并不强调它们彼此的关联;(2)基本的单元是各种祈使句;(3)选材是为了服务于作者的道德目的。[144]其选材的特征使得某些人宣称雅各书的内容取自于一组散乱堆砌的道德劝勉。[145]但戴维斯正确地指出:“其中的话语和箴言并不像迪贝利乌斯所相信的那样毫无关联、随意堆砌。”[146]基斯特梅克(Kistemaker)断定:“尽管这些训诫之辞似乎较少彼此的联系,其实雅各在呈现它们时,显示了依据某种线索推进和发展的意思。”[147]
有人指出,雅各书的文学特征似乎与希腊的哲辩形式(Hellenistic diatribe)有关。[148]哲辩形式常见于希腊通俗道德主义者的作品,其特征是使用简约的辩论形式与假想的对手辩论,有时也采用问答形式,并常常使用祈使句。这种形式在当时广为流行,特别是在犹太会堂里多有所见。尽管这种劝勉风格与雅各的写作目的甚为相符,但公平地说,这封信的特点并不能归于希腊的哲辩形式。按照亚当森的话说:“哲辩形式完全是希腊化的产物,而雅各书则本质上具有闪族和圣经的特点;雅各书与哲辩作品在风格上确实相当接近,但就像那些犹太会堂里的布道一样,这种相似大体上是十分肤浅的。甚至更为明显的是,这封信从整体上来说并不是一篇哲辩之文。”[149]
时代性
雅各书有别于新约其他书卷的地方在于其见证了基督教的多面性。对于承载完整启示的基督真理而言,它提供了必要的贡献。
雅各书对道德的强调,向今天的我们传达了关键和必须的信息。萨蒙在强调此书的重点所具有的时代性时提醒我们,“基督教的成功,有多少要归功于其教师们在灌输我们现在以为常识的教训时所承受的痛苦啊”。[150]后期的新约书信所体现的更完整的启示,并没有让雅各实践性的信息过时。“圣雅各和圣保罗的组合,是防止许多错误的防护栏。”[151]只要还有所谓的基督徒想要将信仰与实践截然分开,雅各的信息就不会失去其现实意义。
[1] Maurice Jones,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313-14.
[2] 这里的日期来自于以下资料:J. D. Douglas, ed.,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3] Alfred Wikenhauser,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p. 474.
[4] A H. McNei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p. 449.
[5] J. Cantinat, "The Catholic Epistles," in A. Robert and A. Feuillet,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pp. 565-66.
[6] Joseph B. Mayor, The Epistle of St. James.The Greek 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s, pp. xlix-I.
[7] Henry M. Harmo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Holy Scriptures, pp. 711-12.
[8] Douglas J. Moo, The Letter of James,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p. 17.(强调字体为作者所加。)
[9] 希腊文的参考文献,见Mayor, pp. lii-liii, Ivii-Ixii。
[10] James Moffat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New Testament, p. 467; Sophie Laws, 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James, Harper'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pp. 22 -23.
[11] Wikenhauser, p. 475.
[12] C. Leslie Mitton, The Epistle of James, p. 219.
[13] Moffatt, p. 468.
[14] Peter Davids, The Epistle of James, The 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p. 8.
[15] Donald Guthri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p. 738.
[16] Mitton, pp. 227 -28.
[17] James B. Adamson, James, The Man and His Message, p. 51.
[18] 参Adamson, pp. 47-48。
[19] Richard He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p. 165.
[20] Mitton, p. 223.
[21] R. J. Knowling, The Epistle of St. James, Westminster Commentaries, p. xxv.
[22] Theodor Zah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1:148. 也请参见此书所引用的信息。
[23] Davids, p. 9, n. 31.
[24] Everett F. 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p. 386.
[25] 见Adamson, pp. 21-24,以及该书第22页的注解111。
[26] Alexander Ross, The Epistles of James and John,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pp. 14-15.
[27] 请比较以下资料给出的相似列表:Ralph P. Martin, James,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pp. Ixxv-Ixxvi。
[28] Mayor, pp. lxxxiv-Ixxxvi.
[29] Guthrie, p. 744.
[30] Davids, p. 16.
[31] 见Adamson, pp. 25-52中详细的讨论。
[32] 见R. H. Gundry, "The Language Milieu of First-Century Palestine,"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83 (1964):404-8;另见J. N. Sevenster, Do You know Greek?How Much Greek Could the First Jewish Christians Have Known?。
[33] Burton Scott Easton and Gordon Poteat, "The Epistle of James," in The Interpreter's Bible, 12:6.
[34] G. H. Rendall, The Epistle of James and Judaic Christianity, quoted in Adamson, p. 36.
[35] Sevenster, p. 191.
[36] James Hope Moulton, A Grammar of the New Testament Greek, 1:8.
[37] A. T. Robertson, A Grammar of the New Testament Greek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p.123.
[38] Zahn, 1:111.
[39] W. E. Oesterley, "The General Epistle of James," in The Expositor's Greek Testament, 4:393.
[40] Easton and Poteat, p. 5.
[41] 证据来源参见Adamson, p. 36, n. 12。
[42] Mitton, p. 228.
[43] G. R. Beasley-Murray, The General Epistles, James, 1 Peter, Jude and 2 Peter, Bible Guides, p. 19.
[44] 同上。
[45] Sevenster, p. 12.
[46] 同上,pp. 13-14。
[47] Adamson, p. 37.
[48] Oesterley, p. 398.
[49] James Hardy Ropes,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St. James,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on the Holy Scriptures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pp. 33-34.
[50] Oesterley, p. 398.
[51] Heard, p. 165.
[52] R. V. G. Tasker, The General Epistle of James,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p. 20.
[53] Oesterley, p. 397.
[54] Easton and Poteat, p. 4.
[55] Harrison, p. 389.
[56] Knowling, p. xiii.
[57] Davids, p. 18.
[58] Martin Dibelius, "James, 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James," in Hermenia-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pp. 2, 21-22, 46.
[59] 若要便捷地浏览这一讨论所依据的材料,请参考Mayor, chap. 4。
[60] Moffatt, p. 466.
[61] Ropes, p. 23.
[62] Guthrie, p. 753.
[63] Moffatt, p. 472.
[64] 见Guthrie, Appendix C."Epistolary Pseudepigraphy," and R. D. Shaw, The Pauline Epistles, Introduction and Expository Studies, pp. 477-87, 以及上述两文所引用的文献。
[65] A M. Hunter, Introducing the New Testament, pp. 164-65; James Moffatt, The General Epistles, James, Peter and Jude, p. 2.
[66] Guthrie, p. 755.
[67] Moffatt,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New Testament, p. 474.
[68] Werner Georg Kümmel,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rev. ed., p. 409.
[69] A H. McNei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p. 194.
[70] Easton and Poteat, vol. 12.
[71] R. V. G. Tasker, The General Epistle of James, The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p. 35.
[72] William Barclay, The Letters of James and Peter, The Daily Study Bible, p. 39.
[73] Davids, p. 13.
[74] Zahn, 1:111.
[75] W. Boyd Carpenter, The Wisdom of James the Just, p. 12.
[76] G. T. Manley, ed., The New Bible Handbook, p. 396.
[77] 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小雅各”(James the Little),可能指他的个子矮小,也可能指他的年纪较轻。
[78] 对于这种观点的负面评价,见E. H. Plumptre, The General Epistle of St. James, The Cambridge Bible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 pp. 6-10。
[79] zahn, 1:101- 2; 106-7,以及Ropes, p. 45。
[80]“但是,甚至这种观点也有(少数)支持者,特别是来自西班牙罗马天主教会的支持者,以及著名的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约公元636年)。后者称雅各为孔波斯特拉的圣雅各(St. James of Compostella),声称他是当地的保护圣徒(patron saint)。”(Adamson, p. 9, n. 50.)
[81] John E. Steinmueller, A Companion to Scripture Studies, 3:324 25.
[82] Wikenhauser, p. 480.
[83] S. Barabas, "Alphaeus," in The Zondero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1:118.
[84] Robert Johnstone, Lectures Exegetical and Practical on the Epistle of James, p. 59.
[85] See George E. Evans, "The Sister of the Mother of Jesus," Review and Expositor, October 1947, pp. 475-85, and John W. Wenham, "The Relatives of Jesus," The Evangelical Quarterly 47, 1 (January 1975):6-15.
[86] 见以下资料的讨论R. C. H. Lenski,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 Paul's Epistles to the Galatians, to the Ephesians, and to the Philippians, pp. 61- 62; Martin, p. xxxviii.。
[87] Karl Heinrich Rengstorf, "Apostolos," in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1:422-23.
[88] John Calvin, Commentaries on the Catholic Epistles, p. 277.
[89] Tasker, p. 22.
[90] J. Sidlow Baxter, Explore the Book, 6:292-93.
[91] 这三种观点的历史沿革,参见Ropes, pp. 54-59, and Leslie R. Keylock, "Brothers of Jesus, The," in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1:658 -66; John W. Wenham, "The Relatives of Jesus," The Evangelical Quarterly 47 Oanuary 1975):6-15。
[92] 这是希腊东正教和其他东方教会的观点,也受到现代新教学者中一些人的强烈支持。见J. B. Lightfoot, Saint Paul's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 pp. 252-91; Knowling, pp. lxiv-lxvii, and H. Maynard Smith, The Epistle of S. James Lectures, pp. 33-37。
[93] 要了解这些伪托的作品,请参考Keylock, p. 660。
[94] Charles Harris, "Brethren of the Lord," in A 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the Gospels, 1:237.
[95] Keylock, p. 664.
[96] 这是众多现代新教学者的观点。见Samuel J. Andrews, The Life of Our Lord upon the Earth, pp. 111-23; John Eadie,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Paul to the Galatians, Based on the Greek Text, pp. 57 -100; Mayor, in chap. l; Johnstone, pp. 56-65, and H. E. Jacobs, "Brethren of the Lord,"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aedia,1 :518-20.
[97] Ropes, p. 54.
[98] Keylock, p. 662.
[99] Jacobs, p. 520.
[100] 这种观点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立场。越来越多的少数派天主教学者开始拒绝这种理论。
[101] J. 伊西多·姆伯特(J. Isidor Mombert)给出的补充说明,由以下资料引用:John Peter Lange and J. J. Van Oosterzee, "The Epistle General of James," in Lange's Commentary on the Holy Scriptures, 23:22。
[102] Wilber T. Dayton, "James," in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3:395.
[103] Mitton, p. 226.
[104] 约瑟夫,《犹太古史》,20. 9. 1。
[105] 同上。
[106] 优西比乌,《教会史》,2.23。
[107] James Macknight, A New Literal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Greek of All the Apostolical Epistles with a Commentary and Notes, 5:333.
[108] Salmon, p. 454.
[109] Moffatt, p. 464.
[110] Moo, The Letter of James, p. 30.
[111] J. Gresham Machen, The New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to Its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 235.
[112] Paton G. Cloag, Introduction to the Catholic Epistles, p. 48.
[113] Simon J. Kistemaker,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Exposition of the Epistles of James and the Epistles of John, p. 18.
[114] H. E. Dana, Jewish Christianity, p. 107.
[115] S. G. F. Brandon, The Fall of Jerusalem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 p. 238.
[116] T. Henshaw, New Testament Literature in the Light of Modern Scholarship, p. 357; Laws, The Epistle of James, pp. 25-26.
[117] Edgar J. Goodspee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p. 295.
[118] Mitton, p. 236.
[119] Moo, p. 35.
[120] Moffatt, p. 470.
[121] E. C. S. Gibson, "The General Epistle of James," in The Pulpit Commentary, 49:ix.
[122] Moo, p. 34.
[123] Marcus Do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p. 193.
[124] Lange and Van Oosterzee, 23:28.
[125] Robert G. Gromacki, New Testament Suroey, p. 341, and Easton and Poteat, p. 18.
[126] William Hendriksen, Bible Survey.A Treasury of Bible Information, p. 329.
[127] Harold S. Songer, 'James," in The Broadman Bible Commentary, 12:102.
[128] Goodspeed, p. 290.
[129] A M. Hunter, Introducing the New Testament, p. 96.
[130] W. Graham Scroggie, The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The Bible as a Whole, 3:290.
[131] Massey H. Shepherd, Jr., "The Epistle of James and the Gospel of Matthew," A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75 (1956):41.
[132] Glenn W. Barker, William L. Lane, and J. Ramsey Michaels, The New Testament Speaks, p. 29
[133] Martin, James, pp. ciii-civ.
[134] Howard Clark Kee, Franklin W. Young, and Karlfried Froehlich, Understanding the New Testament, p. 379.
[135] McNeile, p. 189.
[136] R. C. H. Lenski,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and of the Epistle of James, p. 538.
[137] George A Hadijiantoniou,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p. 305.
[138] Davids, p. 35.
[139] Moo, p. 43.
[140] Davids, p. 41.
[141] Guthrie, p. 767.
[142] John S. Howson, The Character of St. Paul, p. 8, n.
[143] 要完全了解希腊文中双关语的证据,请参见Mayor, pp. ccxxii-ccxxiv。
[144] Harold S. Songer, "The Literary Character of the Book of James," Review and Expositor 66 (Fall 1969):383 -386.
[145] Dibelius, pp. 5-11.
[146] Davids, p. 23.
[147] Kistemaker, p. 10.
[148] Ropes, pp. 10-16.
[149] Adamson, p. 104.
[150] Salmon, p. 467.
[151] 引自Mitton, p. 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