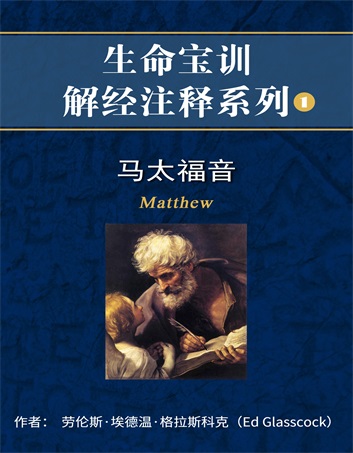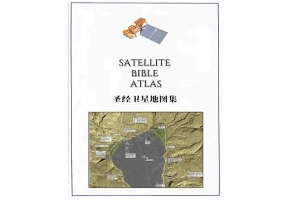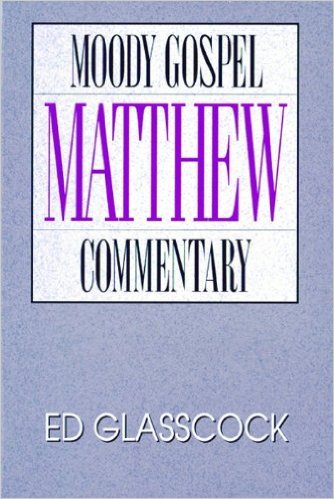导论
马太福音被置于新约正典之首,这是因为早期资料来源表明它是最先成书的。然而,现代学者已经对这个次序提出质疑,因此马太福音不再被视为同观福音书中最早的一卷。针对这卷记载主的生平与传道的书,人们对其来源和最初的性质提出了上述的问题,还提出了许多其他的问题。本注释的目的和构成不允许详细阐述所有这些问题,但将为有需要的读者提供高质量的资料,供参考。
如果一个人要想成为当代圣经学习领域的真正学者,那么他就必须对同观福音书成书的时间次序提出疑问,并假定它们不仅彼此依赖,还依赖着非正典的资料来源。人们当然不希望忽视任何一份有助其最完整并准确地理解圣经原文的资料。根据这一假设,我们可能有必要考虑与马太福音当前原文有关的一些问题。
原著语言
众多圣经学者争论的一个主要话题是:这部福音书的原著语言是希伯来文、亚兰文,还是希腊文。人们一般引用帕皮亚(Papias,希拉波利斯主教,居住在弗吕家的城市,2世纪初)的评论,来证明希腊文的马太福音并非原始的版本。优西比乌(Eusebius)说:“这是帕皮亚在谈及马可福音时所提到的,论到马太福音他说:‘马太福音收集了希伯来文的神谕,人人都尽其所能地诠释这些谕示。’”[1]
这个争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帕皮亚的原作已经失传,并且很多人质疑优西比乌对帕皮亚的引用的准确性,以及如何解释优西比乌的文字本身。优西比乌所用到的sunetaxsato(收集、创作、汇编)、ta logia(表示文字、说法或所包含的事件)和Hebraidi dialektō(希伯来方言,或亚兰文),这些词的意思含糊。学者对此各持其说,并都能为自己的观点提出某些合理的理由。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是把如此多的精力放在如此含糊的话题上是否合理?如果帕皮亚的文件本身存在的话,所花费的精力也许是值得的。然而对这个如此含糊的参考如此重视,这既不是好的学术研究,对时间和资源来说也不是好的利用。
没有现存的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抄本存在,对于一卷原著语言为亚兰文或希伯来文的福音书来说,这个事实使人们更难分析其可能性,尽管优西比乌的其他参考为此理论提供了更多支持。根据优西比乌的话,奥利金(Origen,又译“俄利根”)表明,马太福音是“以希伯来文写作而成的(grammasin hebraikois suntetagmenon,‘以希伯来文字〔或字母〕编成’)”[2]。他在书中的另一部分写道:“马太首先向希伯来人传道,当他准备向其他人传道时,他用母语写下了自己的福音书。”[3]同时,优西比乌保留了一个有关宣教士潘代努斯(Pantaenus)的惊人传统,此人受遣去印度传福音。当他到达那里后,他发现印度人已经从使徒巴多罗买那里接受了福音,巴多罗买为他们留下了一份“用希伯来字母”[4]写成的马太福音抄本。最后,优西比乌引用爱任纽(Irenaeus)的话说:“此时马太在希伯来人中间发表了一卷用他们母语写成的福音书,而彼得和保罗正在罗马传道并建立教会。”[5]
这些记载下来的评论似乎证明了马太福音的原始希伯来文(更可能是亚兰文)版本是存在的。但即便如此,人们对这些评论的众多争执也依然继续着,这使那些严肃寻求答案的学生备受困扰。人们可能会问:巴多罗买为何要为印度人留下一卷希伯来文的书?我们是否应当假设他们能够读懂?巴多罗买在离开印度前是否教过他们希伯来文(或亚兰文)?译成他们母语的译本,这不是更有可能吗?然而事实是,尽管不同的早期教会领袖被引用到,他们都仅出现在优西比乌的书中。亨德里克森(Hendriksen)评论道:“有意思的事实是,在许多具体的例子中,极力支持亚兰文理论的人们彼此排斥,认为对方的结论是错译。”[6]
塔斯克(Tasker)提供了他认为是新教学者中最主要的观点:优西比乌的评论参考了帕皮亚的观点,即马太并没有写福音书,他只是收集了耶稣的语录(ta logia),并且这些语录后来以历史记述的形式被写成福音书。因此,马太作为大部分材料的来源者,他的名字被附加在后来的著作上。[7]但是,斯坦(Stein)在其有关同观福音书问题的著作中给出结论:“人们已经广泛讨论了帕皮亚文字的解释,以及文字的准确性。”[8]当然,其他引用的问题依然很重要。他们的评论都以帕皮亚的评论为基础吗?这是很有可能的。
有的学者甚至对马太福音的“失落”版本进一步延伸出理论,并提出了没有根基的猜测,那就是除了约翰福音和路加福音的部分文字以外,所有的福音书最初都是用亚兰文写成的。[9]很多学者认为新约的语言带有浓厚的闪语风格,因此假设这表明其原著语言是亚兰文。如此的论断更多是逻辑上的跳越,而不是科学上的推理。人们应当预想到,闪语作者的记载会带有闪语的痕迹,不论他们使用的是什么语言。通用希腊文(Koine Greek)的基础思想是,它是各种方言元素塑造出独特性质的终产物。马太、马可和约翰是希伯来人。他们按照希伯来人的方式思考和表达。一个人学习第二或第三语言,不论他的第二语言变得如何流利,如果他没有保留其母语的独特表达,这是罕见的例外。亨德里克森的解释既符合逻辑又充分:
毕竟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释导致这些书带有的闪语特色。马太、马可和约翰是犹太人,不仅他们三人,而且路加也与犹太人有密切联系,并使用到犹太口头与书面资料。当犹太人说希腊话或写希腊文时,他们不会马上脱离希伯来文的语言背景。因此,新约的闪语风格可能被部分解释为希腊文的地方性变体。[10]
亨德里克森承认无法证明或反驳亚兰文马太福音的早期存在,但他同时强烈主张,“它不是希伯来文或亚兰文福音书的译文,这是显然的”。[11]
因此,人们要么花费时间发展或努力证明“原文背后的原文”这一有意思的猜测,要么花费时间和精力研究当前的原文。充分的证据表明,从上溯至4、5世纪成千上万份抄本中保存下来的希腊文本,是耶稣基督原始见证的准确代表作。所谓的“帕皮亚文本”缺乏可靠性,甚至引用他的优西比乌也质疑他在其他方面的可靠性,因为他倾向采用次经中的故事。[12]亨利·奥尔福德(Henry Alford)是一位致力于解决此问题的著名学者。在他所著的《新约注释》第一版中,他接受了亚兰文原始文本的观点。然而,当他进一步认真核查数据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我只能对这个有争议的话题表明自己的判断。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版中,我认同了古代证词看似不可否认的分量。但从那时起,我开始严谨地研究原文本身,并特别参考了原文在其他福音书中被改写的相似段落。我不得不说,我认为希伯来文是原著语言的观点已经大大动摇……总的说来,我发现自己不得不放弃第一版所持的观点,而接受希腊文为原著语言的观点。[13]
其他著名学者也接受马太福音的原著语言是希腊文。[14]本书也将把我们当前拥有的原文当作原始抄本的实际稿件来分析,而不会致力于尝试猜测或假设一些未知文件可能提到的内容。这并非贬低纯粹的研究,而是表明本书的重点和意图。如果有人对此问题的详细解释感兴趣,D. A. 卡森(D. A. Carson)提供了不错的讨论。他得出结论说:“虽然马太福音带有闪语色彩,诸多证据表明它最初是由希腊文创作而成的。”[15]
Q文件
这引出了另一个必须提及的流行理论,也就是被假设为马太福音资料来源的“Q文件”。Q代表的是德文Quelle,其意思为“来源”。在150多年的时间里流传着各种理论和猜测,也就是,存在着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书面资料来源,并且福音书的作者在构建各自的记载时借用了这资料。卡森认为这个想法源自莱辛(A. E. Lessing),后者(在他去世后于1776年和1778年出版的两篇论文中)“坚持认为,解释同观福音书之间相似之处与看似不同之处的唯一方法,就是假设它们都独立地源自一本亚兰文的《拿撒勒人福音》(Gospel of the Nazarenes)”[16]。埃塔·林内曼(Eta Linnemann)认为,其背后的原因是后启蒙主义“对福音书在历史上不可靠的指控”[17]。当我们考虑到主导后启蒙主义时代的反超自然主义,便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不愿接受“神创文稿”(正如圣经启示对福音书所宣告的)这种思想。当然,有些疑问和问题乍看起来似乎是不一致或矛盾的,但这些问题可以从严谨、客观的释经学获取答案,而不是靠苦苦寻找一部不存在的文稿。
颇有意思的是,当代对Q文件的研究动力并非同观福音书之间的不一致之处,而是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认为存在着一个供同观福音书共同提取信息的资料来源,这一理论一旦诞生,人们就更坚决地认为必然存在着一个书面的资料来源。斯坦评论道:“对同观福音书之间用词的一致性的更好解释,是作者采用了书面的而不是口头的资料来源。”[18]因此,Q文件的证据还没有借着抄本上的发现建立起来,也没有任何记载证明Q文件的存在,它的依据仅仅是由猜测构成,而这种猜测的基础是根据人类的推理,这推理要求见证的一致性。因此,一方面,同观福音书之间的不一致性导致其真实性受到质疑,而另一方面,其一致性却允许人们猜想出一部从未被证明存在过的文件。有人当然会解释说,这个问题实在是错综复杂,若没有高等评论学派的精深学识,是无法明白的。然而,这种复杂性是因为缺乏证据和历史文献而产生的。设想并支持没有事实基础的理论,这总是包含复杂性的。
斯坦认为,“人们对材料顺序的普遍赞同只能由一部共同的书面传说来解释”。[19]这是一个武断的假设,其基础是所猜测的内容,而不是材料证据所能核实的。神的启示难道不可能解释这种和谐吗?难道神的灵不能因为这些事件和语录带有目的和计划而分别指引作者记载它们吗?在所有证明并不存在的Q文件的长篇大论中,没有人考虑过任何圣经启示的超自然元素。对Q文件可能存在的支持已经减弱至什么在人类推理中是似乎有理的,以及宗教群体想当然的传统。寻找福音书的文学来源,实际就是表明它们不过是宗教传统。林内曼曾经专注于对资料来源的评论,她得出结论说:
我们现在发现了真相:Q这部假设的语录福音,是把基督教信仰从圣经的停泊点上撬移所需的杠杆。Q必须取代福音书成为信仰的新锚,因为Q既比福音书早,又与福音书不一致。Q解决了这个问题。[20]
尽管这种态度与Q的研究没有直接关联,它的一个极端表现是耶稣研讨会(the Jesus Seminar)。在这个研讨会上,学者们根据自己认为这部文件肯定、似乎或可能是原始记载,或者肯定、似乎或可能不是原始文件的一部分,而把彩色的珠子投进一个篮子里,以此投票决定这部文件的有效性。
这种重建新约的思想,其首要前提是福音书的记载缺乏可信性,因此必须找到其他的资料来源来证实其真实性。这个大概包含200名学者的群体作出了判断:至少“有82%的比喻、语录和其他警句,是新约抄写员假借耶稣之口说的,而这些话他从未说过”[21]。虽然这些学者宣称他们的判断建立在科学数据的基础上,他们却断定主的晚餐从未发生过,因为“非富人出身的耶稣不会习惯于晚宴招待”[22]。
如果这样的方法对保守福音派来说是荒唐的话,那么对Q文件的寻找也必然是荒唐的。这种努力的前提是,以现存抄本为基础的新约原文不过是早期基督教群体宗教观点的大大小小的见证的集合。无论人们把它称作对基督原始故事的搜寻,还是对历史上耶稣其人的搜寻,都是浪费时间。他们假设马太福音不是由使徒创作的,而是由一位编者在群体传统和一个不存在的文件的基础上对耶稣生平的重新创作,这种假设除了想象的猜测以外,别无根基。正如林内曼所指出的:
人们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才能作出这样的假设:尽管有许多的不同,那些因文学写作顺序相似而被认为属于Q的章节,都源自于同一个资料来源。然而,想象无法取代证据,并且对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这处或那处是从Q序列发散而出的猜想,不能证明Q的存在。[23]
反对这个理论的人在学术上并不低于接受此理论的人,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的中心是:处理保存下来的原文并接受最早见证人对此的宣告——它是一个目击者的著作,此人是一个名叫马太的使徒。卡森做出了以下的重要评论:
主要的编写评论研究都致力于定义福音书作者写作的历史环境,也就是促使这本福音书(被认为)于公元80年至公元100年之间写成的群体环境,这些研究却很少有益地注意到耶稣所在的历史环境。[24]
本注释的目的是集中讨论重点当在之处,即耶稣的生平与传道的背景上,以及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文字。本书作者希望读者从原文的注释中受益,同时对当代围绕此内容展开的理论有所了解,但不受其左右。
马可福音为资料来源
另一个被经常讨论的理论是,马太是否实际倚靠马可来获取福音书中的信息。如果人们接受马太的作者身份,那么如此的理论可能乍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是目击者,不需要倚靠任何的资料来源。但是,这个理论的基础是三部福音书之间的一致与不一致倾向。这些不一致之处不应当被视为启示上的错误,它们反映出在阅读1900多年前的文字时,要想清晰地理解这些问题通常是很困难的。在同观福音书中,事件的列举顺序和强调重点都有所不同。有时根据各福音书的目的,同一事件是从不同的角度被呈现出来的。在这些对比研究的领域,有些学者已经发现“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常同路加福音不一致,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常同马太福音不一致,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却很少同马可福音不一致的”[25]。大多数学者自然地得出这一结论:马可福音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共同资料来源。
尽管这个观点作为一种判断是被接受的,但人们必须记住:马可福音是共同资料来源的观点仍然是一个在观察的基础上建立的理论,并且它包含了一些预先的假设。马可福音居先的观点是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研究中才发展起来的。在那之前,教会一致赞同马太福音是居先的福音书。优西比乌再次提供了有关早期福音书的信息。他引用奥利金的观点说:“四部福音书在普天下神的教会中本身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从传统得知马太福音是最先写成的,马太曾经是一名税吏,后来却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26]但是,优西比乌后来却发表了一个似乎与此相悖的观点:“马太……用母语写下了自己的福音书,……并且马可和路加已经发表了他们的福音书,但据说约翰却一直使用没有书面记载的信息。”[27]这个观点可能暗示,马可和路加已经在约翰之前发表了他们的福音书。这个讨论一开始就主张,在十一个门徒中只有马太和约翰发表了福音书。因此,马太首先写下了福音书,然后马可和路加在约翰之前发表了福音书。
早期教会的推理是符合逻辑的:马太是一名使徒,又是目击者,他比其他人更多地保存了耶稣的语录;马可的记载仅仅是福音书的缩写;并且路加是后来才出现的外邦人。判断谁先写了什么并不会改变所写的内容。本注释所持的观点是:神的灵监督了这些福音书的写作,因此它们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权柄。此书的前提是:马太很可能首先写下了福音书,但是,没有结论性的证据对此提供支持或反对。
作者
人们普遍认为马太福音的作者是使徒马太,但是原文并没有显明作者是谁。正如蒙斯(Mounce)所指出的,奥利金、爱任纽、优西比乌和哲罗姆(Jerome,又译“耶柔米”)等早期教会领袖的见证支持使徒的作者身份[28],并导致一些学者认为马太的作者身份是被普遍接受的。[29]卡森指出:“早期教会的普遍证词是使徒马太写下了此书,并且我们最早的文字见证也认为他是作者(kata matthaion)。”[30]福音书中没有明显的文字引起对此的质疑,但有的学者看到一些隐含的不一致之处,并觉得这对承认马太的作者身份造成了困难。
迈耶(Meyer)认为,“很多关于时间、地点和其他方面的陈述模糊,与使徒身份的目击者和事件的参与者的活的回忆是不可调和的,哪怕假设作者有计划地主要按照主题进行了编排”,这证明原始文稿并不是出自马太的笔下。[31]然而,迈耶的观点并不具备结论性。如果作者是马太,那么他并没有写下容许我们进行风格比较的其他著作。认为他必须给出确切的时间与事件的假设是没有依据的。若认为他对事件的记载不及约翰或其他作者准确,这就是在假设他的写作目的与设计跟约翰相同,并且他必须使用与其他作者相同的表达方式。如此的假设是毫无必要的。
甚至连迈耶也评论道,Euanggelion kata Matthaion这个标题“是对此最早且最好的有利见证”[32]。尽管这样的标题并不属于原始文稿的一部分,但它确实证明了人们很早就把这部著作归属于马太。若有人认为不应当全部接受对作者身份如此早的证明以及教会领袖如此有力的证词,那么这种假设是奇怪的。亨德里克森的结论是: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部福音书被最早保存下来的教父著作(由巴拿巴〔Barnabas〕、罗马的克莱门〔Clement of Rome,又译“革利免”〕、伊格纳修〔Ignatius〕和波利卡普〔Polycarp,又译“坡旅甲”〕所写的著作)所使用。《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也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证明。事实上,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关这部福音书在早期被使用并且它一开始就被归属于马太的外证是毫无异议的。在此书写成之后的大概60年内,其真实作者的名字竟被遗失并由一个虚构的名字所取代,这是很难解释清楚的。[33]
蒙斯问道:“如果使徒没有写下这本福音书,那么他的名字是如何被附在书上的?”[34]这个问题问得合理。在现代学者开始揣摩字里行间之意、假定一些风格上的规则并接受含糊不清的证据之后,马太的作者身份似乎才开始受到质疑。另一个有意思的元素是,从来没有其他名字与此书相关,而且反对马太作者身份的内证或外证都不存在。
书中一些有意思的特征显然为马太的作者身份提供了内证。一个观察到的现象是,在马太被任命为使徒之前,路加和马可都使用“利未”这个名字来称呼他(可2:14;路5:27、29),但是马太从未使用“利未”这个名字。在提到他蒙召跟随耶稣时,他使用了“马太”(太9:9)这个名字。类似的态度还出现在保罗的著作中,他只使用自己信主以后的名字。迈耶解释道,根据犹太人的习俗,他们在经历人生重大事件之后会使用新的名字,因此马太的意图是要强调自己的新身份。[35]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值得一提,在所有的使徒名单中,马太总是被称作马太,而不是利未,但唯独在马太所列的名单中,他使用了“税吏”这个负面的修饰语。马太用这个头衔称呼自己,而没有别的人如此称呼他,是因为犹太人反感这个头衔,这是符合逻辑的。这仿佛表明,马太记得基督寻找他,尽管他在宗教领袖的眼中是不配的。这让人多少想起,约翰省略了自己的名字并称自己为“他〔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约19:26),马太似乎因为耶稣爱他并呼召他这样一个被鄙视的税吏来服侍主而激动不已。
有关作者身份的新异理论不计其数,然而对评论家或读者来说,追逐错综复杂和无休止的争论是不明智地浪费时间。对其发展有兴趣的人们可以通过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注释书了解相关的观点和理论。卡森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结论:
没有任何支持马太作者身份的观点具有结论性。因此,我们无法完全确定这部最早的福音书的作者是谁。但是,有确凿的理由支持早期教会把此书一致归属于使徒马太,并且根据严格的审查,反对的观点似乎都缺乏实质。[36]
这本注释将采用有关作者身份的正面观点,并明确接受教会的一致观点,那就是从税吏变成使徒的马太是原文的作者。
马太
使徒马太最初被称作利未,他曾经是一名税吏,并且是亚勒腓的儿子(太9:9;可2:14;路5:27)。他成为基督徒后的新名字可能是由闪语Mattathias缩写而来,其意思为“耶和华的恩赐”。还存在一种很小的可能性,即他是同为十二门徒之一的小雅各的兄弟(太10:3;可3:18;路6:15;徒1:13)。但由于“亚勒腓”(Alphaiŏs)这个名字很常见,并且没有任何一部福音书试图把马太与小雅各联系起来,如同把雅各与约翰或者彼得与安得烈联系起来那样,所以最好的释经方法是假定他们之间没有联系。
税吏被视为叛国者和罗马暴君的爪牙,由于他们典型的腐败,犹太人对他们深恶痛绝。艾得闪(Alfred Edersheim)如此评论税吏:
他是以色列被外邦征服的象征,这个事实虽然带有屈辱性,但犹太教的旧教徒对包税人(Moches)和税吏(Gabbai)这类人的极大仇恨,可能与税吏在缺乏良心的交易中厚颜无耻和肆无忌惮有更大的关系,这两种人都被完全排斥于犹太人社群之外。。[37]
税吏是确保每个市民上缴当纳的税金并从中额外收取工价的承包人。斯珀伯(Daniel Sperber)认为:
随着纳税的负担越来越难以承受,包税人或税吏也成为人们更加仇恨和害怕的人物……他们有时甚至设法通过严刑来收取报酬(见民数记拉比文献17:5;参斐洛〔Philo〕,《论特殊律法》〔spec.〕3,153-63)。既然税吏如此地不受欢迎,他的工作并不轻松。他有时确实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因为暴怒的百姓很有可能私下处决他。[38]
琼斯(Jones)赞许奥古斯都(Augustus)对罗马税法的改革,但他同时指出这些法律对农民来说相当不公:
奥古斯都的纳税制度虽然在原有的基础上进步很大,它却仍是不完备的……对大多数的纳税人(即土地所有者)来说,特别是对他们中间最卑微的农民土地户来说,这种制度可能是难以承受的。税金是一笔固定金,无论收成好坏,每年都必须上缴;而对于地中海的土地来说,收成情况变化多端。[39]
罗马主要征收两种税:tributum capitis(人头税/成年人的个人税)和tributum soli(土地/财产税)。琼斯再次解释道:
这些税建立在对人口、财产进行周期普查的基础上,普查会统计人口的数量并详细登记土地以及其他财产……认为奥古斯都确实引入了该制度的主要原因是,他是史上第一个被记载执行各省人口、财产调查的人。他于公元前27年和公元前13年在高卢执行调查,并于公元6年派遣使节居里扭在叙利亚执行调查。[40]
“税吏”(telōnēs)一词在马太福音出现了八次,在马可福音出现了三次,并在路加福音出现了十次,它从未出现在约翰福音中,而且总暗含着犹太人的鄙视。在新约中,税吏有八次与“罪人”、“妓女”和“外邦人”同列。根据拉比著作,税吏被视为“强盗”一类的人,没有资格充当证人。[41]当施洗约翰回答税吏的问题时,他表达了人们对税吏的普遍看法,即税吏收取的钱数超出了例定的数目(路3:12)。税吏到施洗约翰那里听道并希望受洗,他们问他应当做什么,于是他回答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路3:13)。要注意的是,施洗约翰并没有教导他们停止做税吏,而是要他们在工作上诚实。
耶稣也使用税吏为例来说明腐败和自私。他警告自己的跟随者不要只爱那些回报他们的人,因为“税吏……也是这样行”(太5:46)。耶稣解释说,若一个罪人被多次劝导归正却仍不悔改,他就要被当作“外邦人〔被拒在与神所立的约之外〕和税吏”(太18:17)。这种关联表明,在犹太人文化中,税吏(尽管他们通常生来是犹太人)被排斥的程度不低于外邦人。
然而,耶稣还表明他们是救恩的对象并配得他的陪伴。他说了一句令祭司长和长老震惊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太21:31)。他在第32节解释了自己的理由:“税吏和娼妓倒信他〔施洗约翰〕。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耶稣似乎有意地与这个被排斥的群体来往,他甚至被称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路7:34)。税吏(以及经常与他们来往的“罪人”)被频繁地描绘为“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路15:1)或者在属灵上真诚的人,迥异于法利赛人(路18:13)。
人们对这个特定的人群公开表达了如此强烈的情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常识会导致人们避免与这些道德名声和操守卑劣的人交往,以此来安抚宗教人士并赢得他们的支持。然而我们的主表明,他来不是为了安抚宗教人士或赢得他们的支持,而是为了拯救罪人。他接触那些被宗教领袖排斥的人,甚至亲自拣选了其中一人,即税吏利未,并使其成为他所亲近的门徒之一。在马太所列的十二使徒名单中,他把自己描述为“税吏马太”(太10:3),然而其他的福音书在使徒名单中都没有提到他的税吏职业,尽管这些福音书可能对其他使徒有描述性的评论。这可能反映出了马太的谦卑,因为尽管他被宗教群体所排斥,他却被拣选为使徒。
与拣选其他使徒一样,拣选马太为使徒不是偶然的。马太很可能是来到施洗约翰面前受洗的众税吏之一(路3:12),而这反映出他的品格。耶稣看见他坐在税关上,并呼召他做使徒(路5:27)。耶稣知道马太的品格,并很可能像观察拿但业(约1:45-50)那样观察过马太。人们甚至可能猜想,在路加福音18:10-13中,带有比喻意义的税吏可能就是马太。当然,我们不能过于重视这样的猜测。
奥尔福德提到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的一个评论,该评论表明马太加入了早期教会时基督教的一个禁欲犹太主义分派。[42]迈耶(Meyer)也提到了同样的资料来源,并指出这一宗派的主旨是遵循素食的规定。[43]这与早期教会的犹太性质是一致的,尤其在与耶路撒冷会议(Jerusalem Council)对新的教会发出的劝勉作比较时(徒15:29)。马太对主真诚并反对半信半疑的态度,这可能与雅各相似。但是,在克莱门的评论基础上认为马太已经成为律法主义者,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马太的福音记载如此强烈地谴责自我为义与律法主义,绝不会鼓励信徒有那样的生活方式。
有些资料来源宣告说,马太忠心侍奉主一直到老,他的传道覆盖了广泛的地区并结束于帕提亚(Parthia,现代伊朗北部靠近里海的地区)。[44]另有资料来源表明,多马进入帕提亚并在印度传福音,而马太进入埃塞俄比亚。[45]迈耶引用教父苏格拉底(Socrates)的说法,以此支持马太在埃塞俄比亚自然死亡的观点。[46]大多数人一致赞同,埃塞俄比亚是他的去世之地。
写作时间与地点
早期资料来源把马太福音列为第一部福音书,而当今有些学者争辩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写于马太福音之前。奥利金表明,经外传统支持马太福音是首先写成的书。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我们必须假定马太福音是教会的早期文献。优西比乌指出,马太为犹太信徒写下了福音书,在宣教旅行开始之前,他一直教导这些犹太信徒。[47]爱任纽认为,马太写福音书的时间与彼得和保罗在罗马传道的时间相同。[48]这也表明马太福音成书的时间早,因为保罗和彼得大约在公元67-68年殉道。但给我们留下的仅仅是理论性的结论。我们根据书中的内部数据难以推算时间,但对诸如以下问题进行分析是愚昧的,比如“三位一体洗礼模式的存在(28:19)以及教会在组织和敬拜上已经相当稳固地建立了道德规范和模式这一总印象,表明成书的时间相当晚”[49]。这些声明显然存在预先的假设,即马太没有记载主复活后亲口所说的话(太28:19),而只是表达了基督教群体在传统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洗礼与组织模式。如此的假设是没有根基与价值的。我们确实知道,伊格纳修在大约公元110年时引用了马太福音,所以此书在当时已经在流传了。
亨德里克森从一个相当标准的角度证明,根据圣殿或耶路撒冷城被毁(二者于公元70年为提图斯〔Titus〕所毁)从没有被提到,马太福音是在公元70年之前写成的。[50]然而问题在于,新约中没有任何一本书记载了这场灾难,这其中包括肯定在此事件发生之后才写成的启示录。重要的区别在于,马太福音包含了如此多的末世信息,尤其是与耶路撒冷和圣殿有关的信息(太24章),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地提到经文的应验,因此他不大可能不使用这一事件来进一步显明耶稣的弥赛亚身份。虽然确实没有太多的证据可供我们思考成书的特定时间,但正如前面所表明的,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卡森把时间定在60年代[51],这可能是正确的,并且本注释将把时间假定为大约公元65年。
尽管这部福音书的写作地点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信息,它却为一些次要问题提供了见解。很多学者一致认为,马太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写下这本书的,此地与使徒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52]有意思的是,第一个引用马太福音的人似乎是安提阿的主教伊格纳修,而安提阿是一个以希腊语为主的城市。[53]因此人们可能会问,如果这个地点是正确的并且希腊语是主要的语言,那么马太有可能用希伯来文(或亚兰文)写下这本福音书吗?这又为有关原著语言的讨论提供了另一个值得考虑的角度。但为了公平地对待涉及此问题的双方,我们应当提到,在安提阿生活着很大一群犹太人[54],因此用亚兰文写书并不是不寻常的,因为它是希伯来人的共同语言。安提阿肯定是基督徒的活动中心(参徒6:5,11:19-27;加2:11),因此人们不得不赞同卡森的话:“这是一个势均力敌的猜测。”[55]
写作目的与读者
马太福音突出的犹太特色反映出这本书的整体目的。认为圣经中任何一本书只包含一个目的或一个“主题”,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每个受默示写下经文的作者显然都领受了一个主要重点,而这一思想影响到记载的内容和对任一事件或话题的强调程度。马太的著作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提供了辩护。他不断提到有关弥赛亚的旧约预言的应验,强调了耶稣凭家谱对大卫王位的继承权,记载了许多有关国度的比喻和教导,并假定读者了解犹太人的节日和传统。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他的目的是要说服犹太人:他们的弥赛亚已经来临,他们却拒绝了他。卡森作出了这样的重要评论:“作者根据一个明确的计划下笔写作,即阐明耶稣确实是基督。”[56]
马太确实知道他的著作会超出犹太群体的范围,这是有所表明的。他提供的一些解释表明,他假定此书还会有非犹太人的读者(1:23,“翻出来就是”;27:33,“意思就是”;27:46,“就是说”)。然而,这些表达是比较少见的,因此马太福音所指向的读者仍然主要是犹太人。奥利金说,他所受教的经外传统表明,马太“为那些从犹太教改信的人们发表了此书”[57]。因此,马太的读者不会是未得救的犹太人,而是从犹太教改信的人们。奥尔福德得出结论说:
此书对犹太人习俗、律法和地名的解释少于其他的福音书。整个叙述更多地是从犹太人看待事件的角度进行的,并更加在意建立这个对改信的犹太人来说至关重要的观点——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58]
然而,写作目的仍然是为改信的新信徒提供辩词,用以应对那些质疑他们信耶稣的人。
福音书的特色与风格
毫无疑问,马太试图写下一部有关弥赛亚耶稣生平与传道的历史记载,他把他的写作放在时间与地点的事件中,也放在真实历史人物的语境中(太1:1-19,2:1、16等;2:22,3:1,4:12,9:9,14:1,26:57,27:2、11-26等)。斯科特(Scott)说:“他对福音书中事件的评论方式……表明他知道并且想要让它们具有严格的历史性。”[59]尽管有人认为,马太由于神学注释的缘故对他所记载的历史进行了润色,如此的指责从释经角度上缺乏有力的辩护,而且它们的基础建立在假设上,并通常由循环论证所支持。
可以提到的是,在更多的情况下,马太福音中的故事被润色这一假设,其主要基础是与世俗著作的比较,这些著作不属于神所默示的文学。它们编造故事的“自由”无法与圣经的叙述相提并论。除非经文被放在比喻、寓言或其他象征性的语境中,否则我们应当接受经文所宣告的内容是真实的表述。有些人认为马太福音的部分文字带有米大示(midrashic)的风格,他们对此观点的竭力辩护在释经学上令人难以接受,因为他们过于偏执地试图找到自由的文学创作缺乏客观性。
奥尔福德表明,马太福音“在写作方式和措辞上与其他福音书相同,即希伯来式或希腊式的希腊文”[60]。这种风格被一个生活在1世纪的犹太人所使用,这是在预料之中的。但是马太福音因为其写作风格而仍被视为“一部文学佳作”[61],这部分地是由于马太对材料的组织。他以大段的教导来呈现材料,并用叙述和编者注释来分隔各段教导。卡森也提到这种“高超的文学巨匠工夫”[62],并且这种艺术成就可以归因于原文不只出于人的创意。整本圣经已经被归为艺术文学的巨作,而且如此的荣誉已持续数百年,甚至在反对神默示的圈子里也是如此。
马太福音在写作风格上最引人注目又最饱受批评的特征之一,可能就是他大量引用旧约来证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蒙斯数出“至少50处清楚的引用”和“出自旧约的无数单词、短语和重复”[63]。威廉·巴克利(William Barclay)抱怨道:“他事先预备好,要使任何在言词上能够变为适合的原文来成为有关耶稣的预言,哪怕这些原文最初与此问题毫无关联,并且从未带有与此相关的意图。”[64]然而,如此判断马太福音的态度可能更多地反映出理解上的欠缺,而不是真正的圣经学术。卡森的话表明他确实离正确的方法更近,他说:“若不说更谦卑,至少这种假设是更有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因为对1世纪的背景缺乏充分了解,无法确切地把握原文的含意。”[65]威利斯(Willis)在此问题上提供了有用的讨论,并得出结论说:
因此,所有的引用在其语境中(马太福音的犹太读者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语境)都呈现了几乎相同的主题:神介入人类被掳的境况,从而带来拯救的盼望——马太福音把罪比作那俘虏者。[66]
我们确实不应当质疑圣经作者的智力和诚实,反而也许应该挑战自己对圣经预言性的理解。
根据马太对旧约的大量使用以及他对耶稣应验弥赛亚预言的强调,我们可以自然地承认他是从旧约到新约之间的过渡性先知。马太介绍了耶稣,即耶稣应验了神对大卫和百姓的应许,并且他担当了世人的罪。马太福音在正典中的地位是实至名归的,它是接续旧约的介绍性福音。那位差遣他儿子的神,是以色列的神。神没有忘记自己与百姓所立的约——弥赛亚耶稣就是凭证。
[1] 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 Kirsopp Lake, 2 v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75), 3:39; 16. 此重要评论的希腊原文为:Matthaios men oun Hebraidi dialektō ta logia sunetaxsato, h‘rm‘neusen d’ auta hōs ‘n dunatos hekastos。
[2] 同上,6:25; 4。
[3] 同上,3:24; 6。
[4] 同上,5:10; 3。
[5] 同上,5:7; 2。
[6] William Hendriksen ,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on Matthew (Grand Rapids: Baker, 1973), 85.
[7] R. V. G. Tasker,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1), 12.
[8] Robert H. Stein, The Synoptic Problem (Grand Rapids: Baker, 1987), 129.
[9] 本书作者曾经有过一位教授,此教授真认为理解新约的唯一方法是把它从希腊文翻译为亚兰文,然后再翻译为英文。
[10] Hendriksen, Matthew, 85.
[11] 同上,91。
[12] Eusebius, EH, 3:39;16.
[13] Henry Alford, The Four Gospels, vol. 1, The Greek Testament (Chicago: Moody, 1968), 29.
[14] 塔斯克得出结论说:“大多数现代学者很难相信,我们的马太福音是从一份亚兰文文稿翻译过来的。”(Matthew, TNTC, 1:13.)
[15] D. A. Carson, Matthew, EBC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4), 8:12.
[16] 同上,4。
[17] Eta Linnemann, “Is There a Gospel of Q?” BR, August 1995, 19.
[18] Stein, The Synoptic Problem, 43.
[19] 同上。
[20] Linnemann, “Is There a Gospel of Q?” 19.
[21] Jeff Lyon, “Gospel Truth, ”The Chicago Tribune Magazine, 17 July 1994, 10.
[22] 同上。
[23] Linnemann, “Is There a Gospel of Q?” 22.
[24] Carson, Matthew, 8:6.
[25] 同上,8:13。
[26] Eusebius, EH, 6:25; 4.
[27] 同上,3:24; 6-7。
[28] Robert H. Mounce, Matthew, NIBC.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1991), 1:2.
[29] Alford, GT, 1:24.
[30] Carson, Matthew, 8:17.
[31] Heinrich A. W. Meyer, The Gospel of Matthew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1983), 2.
[32] 同上,33。
[33] Hendriksen, Matthew, 96.
[34] Mounce, Matthew, 1:2.
[35] Meyer, Matthew, 1.
[36] Carson, Matthew, 8:19.
[37] Alfred Edersheim, Sketches of Jewish Social Life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1994), 51.
[38] Daniel Sperber, “Tax-Gatherers,” in EJ, ed. Cecil Roth, 16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15:873.
[39] A. Η. M. Jones, Augustu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0), 122.
[40] 同上,119。有关最后的这一评论,比较路加福音2:1-2。
[41] Sperber, “Tax-Gatherers,” 15:873.
[42] Alford, Four Gospels, 1:24.
[43] Meyer, Matthew, 2.
[44] Lives of the Saints, 集合了Butlers Lives和其他被认可的资料来源,并被教皇利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正式认可(New York: Benziger, 1922), 464。
[45]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The First Five Centuries (New York: Harper, 1937), 101.但是他选自优西比乌的文献没有被正确记录。
[46] Meyer, Matthew, 2.
[47] Eusebius, HH, 3:24; 6.
[48] 同上,5:7; 2。
[49] Mounce, Matthew, 1:3.
[50] Hendriksen, Matthew, 97.
[51] Carson, Matthew, 8:21.
[52] James Straham, “Antioch,” in Dictionary of the Apostolic Church, 2 vols., (Edinburgh: T. & T. Clark, 1926), 1:69.
[53] 同上,8:21。
[54] Strahan, “Antioch,” DAC, 1:69.
[55] Carson, Matthew, 8:21.
[56] 同上,8:79。
[57] Eusebius, EH, 6:25; 5.
[58] Alford, Matthew, l:30.
[59] J. W. Scott, “Matthew’s Intention to Write History,” WTJ, (1985), 70.
[60]Alford, Matthew, 1:31.
[61] Mounce, Matthew, 1:3.
[62] Carson, Matthew, 8:17.
[63] Mounce, Matthew, 1:4.
[64] William Barclay, Gospel of Matthew, The Daily Study Bible (St. Andrews, 1975), 36.
[65] Carson, Matthew, 8:17. 此评论提到难以理解并常引起争议的段落。
[66] Steve Willis, “Matthew’s Birth Stories: Prophecy and the Magi,” ET (November 1993),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