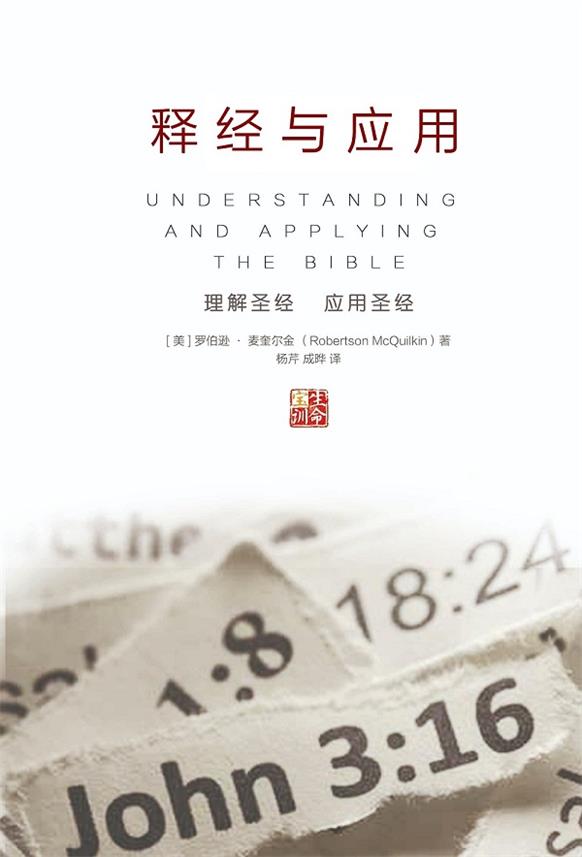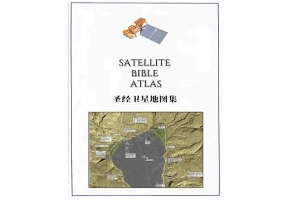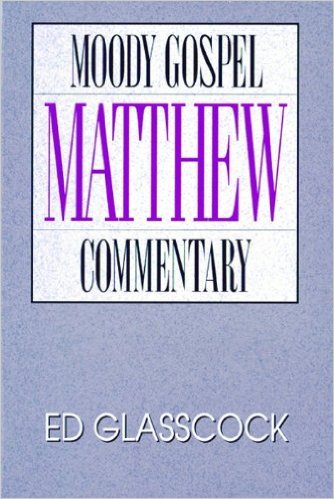第十九章:明确神既定的受众
指导方法:除非圣经在上下文或其他经文的教导中限定了受众,圣经的教导应当被普遍接受。
我们确定了经文的意思之后,就必须要在生活中应用。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探讨应用圣经真理的各项指导方法。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这段经文的信息是针对历世历代的人,还是针对某个特指的人或群体,而不包括我在内?”
为了回答这个关键问题,我们先看衡量的标准。这个标准建立的前提是,唯独圣经才是信仰和生活的最终权威。因此,我们必须让圣经来决定任何一段经文神既定的受众。确定神既定的受众有几种方法:上下文、圣经作者、历史和其他经文。
上下文
一段经文的上下文可能指明了被限定的受众。作者既可能直接陈明他既定的受众,也可能通过上下文暗示。
作者指明受众
马太记录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太5:3)时指出了受众,即所有在灵里贫穷的人都有资格得祝福。路加记录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路6:20)时,指明他的受众是世上所有物质穷困的人当中在场听到耶稣讲话的人。这里当然不是指所有贫穷的人都有福。人们对这两篇经文的混淆造成了颇多困惑,其实作者已经清楚地指明了它们的受众。
耶稣和保罗都从未结婚,他们也都教导了独身的优越性(太19:12;林前7:8)。然而,耶稣和保罗都在那些经文的上下文中限定了这一教导的应用。门徒评论道:“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因为不可离婚)。”针对门徒的这番话,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保罗说,如果男人们都能像他一样不娶妻室,那当然好,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一直守独身。所以这一教导并非针对所有男性基督徒,而仅仅是针对那些有恩赐的人。重要的是,我们要根据经文的上下文,而不是自己的神学、文化或者个人倾向,来确定作者既定的受众——是所有人,还是只有基督徒;是旧约时代的犹太人,还是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是1世纪的基督徒,还是所有基督徒;是仅限于经文指定的受众,还是包括其他人。
启示历史
圣经作者将神启示的救赎史记录下来,是要给我们榜样或借鉴(林前10:11)。圣经的所有记录都是真实的,而历史是照着圣经的记录发生的。但是,任何历史事件要成为具有权威性的行为规范、一个神给历世历代所有人的行为准则,必须由神授权的代言人指明。某个事件被记录为确实发生过,不一定就代表它是神普遍旨意的启示。圣经作者在记录历史事件时往往不评论神是赞同还是反对。例如,罗得女儿们的乱伦(创19:34)。即便圣经对某种行为做出了道德评判(称赞或批判),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也不一定会被记录。也许出于这个原因,圣经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暗示任何历史事件因被记录在圣经中就变成了所有时代所有人的标准。
至于圣经中没有提到的行为就应该被禁止,就更没有根据了。但是,热心高涨的研经者依然不断从诸如《使徒行传》等书卷中总结出一些标准。他们根据使徒所做的和没有做的总结出一系列本土宣教事工的原则,包括什么是必须做的,什么是被禁止的。例如,给归信之人马上施洗,教堂里禁用乐器以及许多其他细节,都基于它们是否为使徒教会的一部分而被立为标准。很多人因此根据《使徒行传》而建立了讲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必要标志这一教义。这可不是对圣经历史记录的合理应用(我们之后探讨什么是合理的应用)。让我们思考圣经中两种与历史有关的教导:历史事件以及针对特定的某个人或群体的教导。
历史事件。我想称这种文学体裁为“叙事体”,但是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环境中,此术语可能会让人误解。如前所见,当今的一些释经者将整本圣经视为“叙事体”,否认圣经中的其他文学体裁。本书所持的观点是将历史性叙事体看作文学体裁的一种。圣经中的很多篇幅就是历史记录,或者所谓的“叙事体”。问题是,神意在我们如何理解并应用这些经文?不管以利户对约伯的一番话是否能说得通,它都不具备启示真理的权威性,然而,《约伯记》本身是圣灵所默示的,意味着只有对人物语言的记录是准确的。
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把保罗对狱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310都必得救”(徒16:31)奉为准则,但拒绝将基督对青年财主相似问题的回答“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从我”当作规范性的。即便基督在《路加福音》12章33节中把它作为规范重申,我们依然如此。还有,为什么我们倾向于认为保罗的行为总是值得效仿,而彼得的行为则几乎总是相反呢?
一个事件或行为不应当单单因为被记录在圣经之中就成为现代人的行为准则。我们必须用圣经直接的教导来衡量它。
针对特定的人或群体的教导。圣经中的很多篇幅都是针对某人或某个群体的。只有当这些针对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的命令与圣经其他地方的普遍教导相同时,它们才可以被视为普遍真理,而不能单凭这些命令本身。当神对摩西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出3:5),或者基督对门徒说“解开(驴驹),牵到我这里来”(太21:2-3),大家都认同这些命令是特定历史性的,不能将它们应用在摩西或门徒之外的任何人身上。
但是,这条原则会被滥用,使得所有基督和使徒书信的教导被变成特定历史性的,而不是普遍的行为规范。有些人认为基督教导的对象是他的门徒或特定的某些人,这些教导如今不适用于我们。还有一些人试图区分使徒书信,称其中一些为“信件”,另一些为“使徒书信”。他们认为信件的权威性低于使徒书信,因为信件仅仅是针对历史上的特定情况,并不是针对普世教会,因此,这些教导当今对我们不具有权威性。
也有人对《诗篇》中的诅咒诗提出类似问题:诗人的做法是对还是错?[1]

我们必须视《诗篇》、基督的教导和使徒书信在应用上为普世性的,是我们今天的规范,因为早期的使徒们就是如此看待这些教导。这一点始终是正确的,除非上下文明确指出这段经文受众的历史局限性,即针对某个人或群体。例如,当保罗在书信的末尾列出具体问候的名单和吩咐时,其上下文显然将这些命令局限于某个人或场合。在受众不易区分时,为了维护圣经的独立权威性,我们应该假定该教导是针对所有人的,而不能轻易地将它搁置一旁。放宽这条原则的适用范围会危及圣经的独立权威性,是我们付不起的代价。
总而言之,圣经本身可能会在紧接的上下文中,通过作者的直接陈明或明显的历史背景的局限来限定受众。
后续启示
后续启示可能会澄清某一教导的受众是谁。例如,并非所有旧约经文都适用于新约时期的基督徒。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基督里废除的整套献祭制度(来9-10章)。但是,关于既定受众的任何变化必须由圣经来指明,那些没有圣经的授权、私自将任何圣经教导搁置一旁的人实际上窃取了圣经的独立权威。
有些人认为整部旧约都不具有规范性。他们认为,除非在新约得以312重申,否则基督徒不必遵守任何旧约教导。然而,这种要求是很危险的,新约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要重申旧约。新约作者和耶稣本人都把旧约(他们仅有的圣经)视为有权威的神的话语。没有新约中后续启示的授权,不允许废弃旧约的教导。许多旧约诫命并未在新约中重申,例如禁止与野兽苟合、禁止强奸,它们难道就不再是规范性的吗?我们必须按照圣经看待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它,视它为神的话语,对于基督徒生活具有绝对的权柄。
当然,新约可能会废除旧约中某一整体教导,因为将具体教导逐一废除是没有必要的。例如,所有描绘神与他的子民以色列国民关系的教导,都被新约中有关教会的教导所变更。基督说“我的国不在这世上”,旧约的情形并非如此。这一整体教导中的细节可能会在某处陈明,如基督叫人收起刀剑的命令。教会不应像古代以色列人那样用武力发展。但是,旧约中还有很多同属这一范畴的教导可能没有在新约中明确废除。尽管如此,它们也不再具有约束力,因为这一整体的教导都被新约变更了。例如,有关王位继承的教导只限于以色列,而不适用于今天的教会或政府,因为“基督的国不在这世上”。
在《加拉太书》中,保罗不仅不承认割礼为与神立约的必要记号,似乎还将包括割礼在内的整个体系都摒弃了。任何食物对于基督徒来说都不再有禁忌(可7:13;徒10:15),因此,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饮食律例虽然有借鉴意义,却不再是标准。这样,旧约中的一些特殊教导都在新约中被明确废止了,其中包括有关宗教仪式的条文,以割礼为象征的与某一特殊民族的立约关系,民事治理,饮食条例。
新约内也有后来发生变更的现象。在《马太福音》10章9-10节中,基督不是叫20世纪的基督徒出门都不带钱。我们之所以明白这一点,是因为之后他取消了最初的教导(路22:36)。但这里绝不是说让人们从圣经沉默之处得出荒唐无力的结论。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以后新约作者就再也没有提到方言为由,认为方言已被禁止,就是以外在标准强行改变一个明确的圣经教导。但是,如果圣经某处教导的教义或行为看起来与另一处教导的相反,又该怎么办呢?两个教导怎能都针对当代教会呢?有很多时候,圣经中的两段或更多的经文表面看来的确相抵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既然坚信这一基本教义,就应该尽一切可能解决这些表面上的出入,其中包括:运用所有释经原则以确定经文的含义,研究作者的写作意图、既定受众、语法、写作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如果经文的意思、受众或应用仍然不甚清晰,那么我们可以运用“信心类比”的方法(有关此概念的细节,参见第十六章)。塞莱里尔(M.Cellerier)在他经典的释经学手册中如此定义:
信心类比这一释经学方法借助真理的普遍特性来解释一段特定经文,其根据和权柄取决于它们所建基的经文的数量、一致性、明确性和分布。[1]
换句话说,在明显的出入无法调和时,更为清晰、更被强调的教导才是我们应该相信和顺服的。
在致力于解决圣经教导中的表面出入时,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合理的。314调和相冲突的教导的另一个合理方法是,看二者是否都针对同一既定受众。例如,保罗似乎指出,男子留长发是不合本性的(林前11:4)。但对于旧约时代的拿细耳人,蓄发倒是分别为圣的标志(士13:5;撒上1:11)。旧约与新约的受众不同,明白这一点有助于消除两处教导之间的张力。当然,这并不能解决另一个问题:若要在二者之间选其一,哪一个教导适用于今日的基督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运用已经学到的多个指导方法。但将两段教导进行比较是有益的,显明了长发本身并不是涉及历世历代所有男人的道德问题。
注意,我们在应用任何尚未被调和的教导时,应当带着尝试性,而不是武断地认为哪一个就是最权威的。本章的主题很明确:圣经是历世历代各个社会的标准,除非圣经本身限定了它的受众。这种限定可能出现在紧接的上下文中,也可能出现在圣经的其他部分。
但有很多人根据其他方法将圣经教导的受众限定在圣经时代。如果我们接受圣经为最终权威,任何这一类的方法就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要在学习当代受众应如何应用圣经教导的指导方法之前,先思考以下一些不可取的限定受众的方法。
限定受众、确定应用的错误方法
有些人认为,如果经文正确,就必须被相信和遵守,但如果有错,就不是规范性的。当圣经说到神创造了第一对男女、基督视邪灵俨然存在、保罗教导丈夫与妻子在婚姻中的角色有别时,他们就会说这些教导有误,所以不必相信和遵守。解放神学家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方法,他们的神学思想以神在现今世上的工作为起点,神在人类历史中(例如在社会变革中)的作为是他旨意的彰显。于是,圣经仅仅被当作资料来源,列举了神在历史上的作为。虽然这些方法推翻了圣经的权威性,它们却被自称为福音派的人所推崇。
还有一些方法不那么明显地背离圣经,我们无法一一细述。但是接下来,我们在此有必要指出在信徒中影响最大的两种错误方法。首先,我们简单考察两种用文化因素来定义经文意思、限定受众或应用的方法,然后再来看两种使用某些原则来定义经文意思、限定受众或应用的方法。
文化因素
用文化因素来确定经文含义、限定受众或决定应用
神在现今想要的回应。这种方法通过研究圣经字词来确定经文意思,但它的用意是发掘经文意思背后作者希望从原始受众那里得到的回应。一旦这种回应被确定,当今释经者就会通过被称为“动态对等法”的步骤提出以下问题:“我如何在今天的听众中产生同样的回应?”
这一问题的答案便是神旨意的启示,也就是针对当今的满有权柄的信息。
那些采用这种方法的人称这个概念为“文化限定”。释经者的任务是分辨圣经资料中能被普遍接受的文化因素,然后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中再现神想要的影响。
在这种方法中,圣经经文就如同其他人类作品一样,反映了作者的文化。因此,研经者的任务就是将圣经真理从文化包装中解放出来,让它能够被应用于当代生活。为做到这一点,所有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工具都用上了。当明确了作者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想要得到的回应后,我们就预备好以一种适合我们文化的方式在当今受众中寻求同样的回应。
例如,保罗教导属灵领袖应只有一位妻子(提前3:2;多1:6)。保罗是这么说的,这似乎是他的真实想法。但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一位解经家会说,保罗是希望确保教会领导人在信徒眼中是合格的,他在立下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合的领导人标准。今天又如何呢?在某个非洲部落,对于领袖的要求正好相反——男人起码要娶得起两个妻子,否则便没有资格当领袖。那么,人们该怎样遵循保罗在《提摩太书》和《提多书》中的教导呢?在这个部落,男人必须至少有两个妻子才能成为教会的长老。虽然这与保罗所说的相反,但没关系,关键是要通过文化分析来发掘这一命令的目的,并以与某个文化相适应的方法应用于今天。
在这种解释圣经的方法中,当前的文化理解取代了使徒,成为教会生活的权威。其最终结果不仅事关教会可以根据具体文化背景来决定是否给信徒施洗,或教会可以根据当地的文化风俗治理教会,一些更基本的神学教导也会借着文化理解被修改。例如,有人教导即使不认识耶稣基督,人们也能通过相信他们对神所认识到的和他们的文化允许他们所接受到的而得救。
普世文化模式。唯有反映了某一普世文化模式的圣经教导才是对所有人具有规范性的。这种观点仅接受圣经中那些能反映普世文化的常规教导(具有神确定旨意的权柄),“不可偷窃”(出20:15)就时常被用作一个例子。其他圣经教导则是受文化限定的,只适用于个别文化。
释经者的任务是将圣经教导从它的文化桎梏中解放出来,得到一个普世真理或原则。根据释经者的观点,基督反对离婚的教导、保罗反对同性恋的教导以及圣经有关妇女在婚姻中的规范角色的教导是受文化限定的,不具有规范性,所以不要求在所有时代和文化中被遵守。
这个观点与前一个相似,只不过释经者不是在经文意思的背后发掘想要有的影响,而只需要寻找经文意思中的普世原则。在这一方法中,经文的意思本身是成立的,但只有当它教导一个被普世文化接受的普遍真理时才是规范性的(可以普遍应用)。
在一次午宴上,我坐在一位顶尖的圣经语言学家对面。我们围绕着圣经中哪些教导具有规范性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我问道:“您认为哪些教导要求所有文化、所有部族中的所有人都遵行?”
他立刻回答说:“那些具有普世文化的教导。”
“比如说?”
“嗯,我不太确定。”他有些迟疑。
“比如不可杀人?”
“对,没错,那应该是被所有文化接受的。”
“听您这么说我感到惊讶,”我答道,“我还以为杀死甚至吃掉被杀者在某些人类社会是一种美德呢。”
“嗯,是这么回事吧。”
我们继续探讨是否有普世的文化标准,却没有确切的答案。既然圣经本身并没有区分哪些教导是普世的,哪些是针对特定文化背景的,由我们承担这项浩大的区分工作,辨认所有普世文化标准,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样将导致把圣经大部分教导变为文化相对性的,圣经的独立权威因而被弃之不顾。
在第八章中,我们学了如何通过文化背景来理解圣经作者的本意,又在本章的前半部分提出了通过了解历史背景来限定受众的方法。这些方法与我们刚刚批评的文化相对主义有什么不同呢?
文化因素的合理与不合理应用
另一种限定受众与应用的错误方法是误用文化因素。让我们思考一下文化因素的合理与不合理应用之间的区别。
历史和文化。历史与文化有合理的区分吗?历史不就是行为和事件的记录吗?文化不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吗?历史和文化相互交迭,息息相关,因此有时难以区分。但我认为,区分历史与文化对于圣经诠释是至关重要的。
什么是文化?虽然存在很多定义,但当代的释经者们用文化这个词的技术性含义来泛指任何一个人类群体的语言、行为、道德、价值观以及做事方式。
让我们初步认同,圣经中那些未经过评价和解释的文化因素,可能并不比未经过评价和解释的历史事件更具普世约束力。但是,二者之间有巨大的区别。圣经中的很多历史事件是未被评价和解释的,因此不具有规范性。但是,几乎所有圣经教导都在评价文化。圣经对人们的行为、道德、价值观和做事方式不断地进行评价、禁止或命令。若说神启示圣经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文化,创造属于神的特殊子民,这一点儿也不过分。神要改变文化,但同时他也使用人类文化作为启示他自己和他真理的载体。
圣经教导往往并非针对历史。没错,大多数历史事件显明了神的作为,但圣经仅仅是将事件的背景记录下来,而大多数圣经教导直接针对文化,因为圣经启示针对的是人类行为。
我认为,除非经文明确指出,否则圣经关于历史的教导并不具有规范性;圣经关于文化的教导则大都具有规范性,除非圣经本身设定了其局限性。我们已经看到,圣经在记录历史时往往不对行为的好坏予以评价,神必须主动通过启示才能使它具有规范性。大卫的多妻在经文中未受谴责,但它不能被用作今天的标准。保罗按犹太教规许愿也一样。但是,使徒们的回答“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虽然上下文中没有任何评论,它显然被视为应当效法的标准,因为在圣经其他地方有大量的教导。
的确,记录文化时,圣经也可能不加以评论,指出它是否应该被当作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与历史记录一样不具有规范性。主人命奴隶在田里工作了一整天之后伺候他吃饭,也不对奴隶表示任何感谢(路17),这是当效仿的雇佣关系的标准吗?我们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圣经中未经评价的文化行为远远少于未经评价的历史事件,因为启示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行为方式、一个文化。因此,不涉及价值观或者只具有文化相对性的记录并不典型。启示的目的就是改变文化,除非神主动通过启示显明,我们才可以说某一文化教导不具有规范性。
因此,神对于人类行为的教导具有最终权威性,只有在圣经本身限定了既定受众或神想要的回应时,我们才能不再遵行。如果任何人将这类“文化性”的教导置之不理,他本人就变成了审判圣经的权威。
大多数人或许认同吃饭前给别人洗脚、女士不剪头发等其他类似命令是针对个别文化的,因此不适用于所有人,尤其不适用于我们!然而,我们却发现几乎所有圣经教导都可以这种方式看待。仅以某个圣经教导是文化性的、只适用于某个特定文化背景为由将它置之不理,就是建立了一条可用来将任何一个甚至所有圣经教导置之不理的原则。带着这样的观点,释经者就变成了凌驾于圣经之上的权威,可以根据某些文化标准从圣经教导中推理出那些被证明为普世的元素或原则,将它们定为人类信仰和行为的规范。
因为圣经历史事件与文化教导之间的不同,我们能够说圣经中未加评论的历史事件不应该被当作普世准则。但是,我们必须认定圣经对于有关人类行为的教导(“应该发生什么”不同于“发生了什么”)是规范性的,除非圣经本身限定了受众和应用。圣经绝不受文化捆绑!相反,圣经作者写作的语言和上下文所体现的文化是神启示的载体,同时也是圣经教导要改变的对象。因任何圣经教导是文化性的而将它废置,就是使圣经受制于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方法。
有效文化论。难道关于文化教导的上下文完全没有价值吗?难道文化绝不能用来确定受众或神想要的回应吗?也许,当圣经的某一教导是建立在文化的因素之上时,文化才是重要的。例如,保罗用了一个文化论据来支持他要大家亲手做工的劝勉(帖前4:11)。圣经或许不会对某一教训加以解释,若是如此,所给的原因就成为教导的一部分。圣经在这里给出的原因不是什么普世道德原则,而是一个文化论据:“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4:12)。换句话说,基督徒应该努力工作养活自己,向非信徒做好的见证。此训诫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模式(行事端正),对于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来说,这意味着体力劳动。既然这一论据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如果文化环境改变,原则(而非命令本身)就应被当作为普世标准。在这个例子中,文化元素不是从外部强加的,而是保罗论点的一部分。保罗没有把这个命令的文化背景定为普世标准,因此,我们不必复制“要工作”这一命令的文化背景。
还有另一种情况,文化元素或许可以在确定受众时被考虑在内而又不夺取圣经的权柄。圣经可能只针对生活在某种文化或历史背景中的群体,而这背景在其他文化中并不存在。如果圣经没有在道德层面命令我们再造这种环境,那么,应该被应用在其他环境中的是支撑这一圣经诫命的普遍原则,而非受限于特殊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诫命本身。除非圣经明确将某文化形式本身视为持久不变的,否则我们应该遵守这一合理的原则。例如,圣经要求我们善待动物或奴隶,并不要求我们一定要拥有动物或奴隶。对于21世纪的信徒来说,恩慈的原则必须应用于任何依靠我们的人或动物。因此,我们无须变成农场主或奴隶主才能遵守这条命令。
这条释经原则的意义涉及如何理解使徒书信这一文学体裁。某些释经者将所有新约书信都归为“历史叙事”,从而把使徒书信变成了释经者手中随意造型的橡皮泥,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保罗、彼得和约翰带着权柄书写,确信自己的话是从神而来的真理。初期教会就是这样看待使徒书信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书信结尾处特定历史性的问安之类的经文是针对普世的教导,它们属于使徒指名的人。
“你们要亲嘴问安”(林前16:20)就是一个特定历史性的教导,不适用于普世。但是,这个符合当时文化的特定问候反映了神家中合一和以礼相待的原则。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说,有一个圣经原则埋藏在一个特定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命令中。
确定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如果某段经文的意思不清晰或带有明显与其他较为明确的经文有出入的教导(有关的详细探讨,参阅第八章和第十五章),为之提供背景的文化因素或许有助于我们弄清它的意思。但是,文化见解不能用来修正作者想要表达的直白意思,也不可用来决定神对某段经文既定的受众,这些必须由圣经资料决定,因为圣经才是我们的权威。
当前文化。明白当前的文化形式在两方面有帮助。第一,当前的现实挑战研经者重新考察已经接纳的解释。例如,科学理论驱使我们更加3仔细地考察对《创世记》的传统解释,正如废奴运动要求我们的先辈们重新思考神有关奴隶的旨意,女权运动也迫使人们重新考察女人的角色。
第二,如果我们要将永恒真理正确地应用在我们目前的环境中,那么准确解读当前文化元素就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代风俗和人类学理论不可成为规范,反过来改变圣经直白的意思。例如,关爱并珍惜妻子的命令(弗5:25、28-29)在不同文化中必须有不同的应用。在美国,如果丈夫从不在他人面前赞美妻子,且拒绝在机场大厅与她拥抱道别,那么他可能是在违背使徒的教导。但一位日本丈夫这么做可能就不是爱的表达,反而会让人议论,使家人蒙羞。真理必须合宜地应用在每一个文化背景中。但在这样做时,圣经直白的教导不能被搁置一旁。
最后,在运用文化工具时,我们必须持谦虚的态度,因为我们在语言、历史、文化和地理等各个方面都与圣经启示的原有背景相距甚远。我们必须运用这些工具,但拒绝被其所用。
运用某些原则来定义经文的意思、界定受众或确定含义
“只有原则可取,而非教导本身。”这个观点与唯有圣经的直接命令和教导才对现代基督徒的行为有约束力这一普遍看法正相反。当然,后者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圣经中充满了具有普遍原则的教导,而非具体命令。事实上,圣经不仅仅是格言、方程式和具体规则的结集,它更是原则之书。但是,与之相反的论点似乎渐渐流行:具体的教导和直接的命令不具有普世性,而只有直接教导背后的原则才具有普世性。
这个方法很吸引人,不仅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使生活变得更容易些,也因为这个方法中的一个重点是忠实于圣经的权柄。这种方法将规范性的教导限于圣经具体教导的原则,不是企图推翻或绕过圣经,而是落实圣经的权柄。
但是,圣经在何处教导了这样的方法呢?经文哪里告诉我们神的真理以及他对人旨意的具体宣告不是规范性的,而只有它们背后的原则才是呢?旧约与新约都将圣经的直接宣告视为规范性的。若基于上述理论不承认直接教导的权威性,就是不允许圣经有所选择。圣经既给出普遍原则,也给出具体教导。
从个别教导中提炼出普遍原则是合理的。但是,不能反过来让原则修订直接教导,甚至阻止人们应用直接教导。将任何圣经的直接教导置之不理,只承认从中推理出来的原则为规范性的,是强加了一个圣经之外的概念,违反了圣经的权威性。
只有基于神属性的教导才是规范性的。只有基于神的属性或创造次序的教导才是规范性的,其他教导有可能只是暂时的,也就是说不适用于今天的信徒。这种观点与前一个例子存在相同问题,即圣经本身从未提出过这种区别对待圣经教导的原则。这样一来,释经者就成了权威,审判可能在他看来不符合神的属性和创造次序的圣经教导。
不仅如此,在应用这一原则时存在一个问题。人类的堕落是基于神的属性,还是创造次序?尽管它本身是神学性的,却似乎并不基于任一者,是吗?难道有关圣餐和守圣餐礼的教导不是仅仅基于基督有权柄的话语?这虽然不像是以神的属性或创造次序为基础的,却是基督定为规范的一种文化形式。妻子当顺服丈夫的权柄以及同性恋行为是错误的,这两个诫命又如何呢?如果任何未被圣经本身限定的直接教导是规范性的,那么这两个教导就是规范性的。但是,若只有那些能证明在本质上是神学性的或者确定是基于神的属性或创造次序的教导,才被视为规范性的,那么这两个教导连同其他很多圣经教导,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争论。
在任何圣经教导中寻找神学基础、神属性或创造次序的基础,这样做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有益——能够显明这种根基可以巩固或澄清具体教导,有助于分辨具体教导背后的普遍原则,这种方法可与经文的其他因素一起,帮助人鉴别出经文是否具有规范性。但是,仅仅因为某一具体的圣经教导的神学本质无法被证实而将它置之不理,就是引入一个不符合圣经、违背圣经独立权威的释经原则。
总结
圣经本身必须决定神要让谁相信、顺服某一教导。如果上下文本身没有指明,我们可以借助其他经文。但最终,我们不应该将圣经之外的标准强加于圣经、不允许圣经被应用到现代人的生活当中。
圣经是神对全人类旨意的启示,因此,圣经中的任何教导都应该被视为当代信仰和生活的标准,除非圣经本身否认。然而,确定某一教导的既定受众并不自动显明它对于信实的门徒训练有何具体意义。神想要什么回应?第二十章将回答这一问题。
推荐阅读书目
Carson, Donald A.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hurch. Grand Rapids: Baker, 1988.
Cellerier, M. Biblical Hermeneutics. Charles Elliott, trans. New York: Randolph, 1881.
Larkin, William J., Jr. Culture and Biblical Hermeneutics. Grand Rapids: Baker, 1988.
Sterrett, T. Norton. How to Understand Your Bible.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