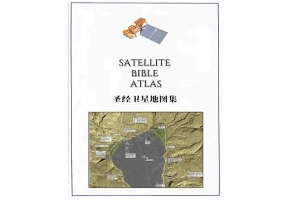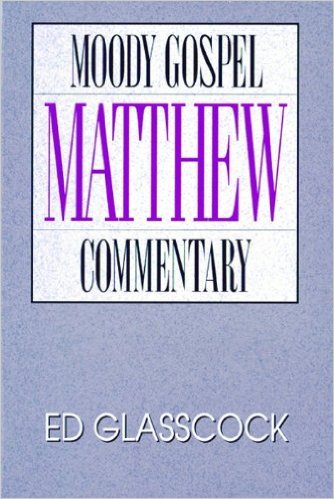第十一章 诗歌体在解经讲道中的运用
罗伯特·洛思(Robert Lowth)1753年的权威著作[1]展开了现代圣经诗歌体研究的序幕,但对圣经诗歌体的分析工作一直没有振兴起来。按照斯蒂芬·盖勒(Stephen A. Geller)的看法,部分原因是我们不会区别平行体的特点。比如,两个类型的平行结构,即“意思”上的语义平行体和形式上的文法平行体。[2]知道这些区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语义平行体是圣经诗歌的主要特征。
另一个原因是,归纳出一些类似古典文学的韵律通则几乎毫无结果。但遗憾的是,没有人能说服别人这通则应该是什么样的。不但如此,就算我们能导出一个通则,无疑也没有多大意义。因此,我们不打算用关于这个主题的种种惊人推测来占用解经者的时间。
诗歌分析的最大障碍是一种不明确的平行体,洛思主教把它称作“综合平行体”(Synthetic parallelism)。跟“同义平行体”、“反义平行体”这些稳定明确的分类不一样,这一类平行体从它被冠名开始,就是个问题。这类平行体所占的篇幅远比其他两类的总和还多,解经者在处理它们时遇到如此大的挫折,以至于开始怀疑整个方法。这个困难可以克服,但在讨论它以前,我们要先说明处理诗歌体经文的一个有序方法。
一、希伯来诗歌的特色
尽管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诗歌形式丰富,但大多数希伯来文圣经的翻译者或解释者仍然没有注意到旧约的诗歌体裁。中世纪时期的少数注释家,如亚伯拉罕·伊本·埃兹拉(Abraham Ibn Ezra)和大卫·金希(David Kimchi)等,曾发现一些具有平行形式的段落,但是这一发现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因为这个缘故,直等到1753年,就是在洛思指出平行体是圣经希伯来诗歌体主要特征的时候。
洛思所下的定义从未被超越:“一节与另一节、或一行与另一行彼此相称的情形,我称之为平行结构;当一个主题被提出,第二个主题就要对它增补或追加,它们或在意义上等同或相对照,或在文法结构上相似,我称这些为平行行;在对称的一行中,彼此对应的单词或短语叫作平行术语。”[3]从洛思的时代到今天,他所定义的平行体是旧约诗歌体的主要文体特征,这一点从来没有受到任何严肃的质疑。[4]
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个领域中唯一主要的发展,就是近代对乌加里特(Ugarit)文字的解读。这些诗歌文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14世纪,其用语和风格都很像圣经希伯来文诗歌,其中所体现的平行特征与旧约诗歌的许多特征一样。
乌加里特文本中的发现促使我们区别看待并确认希伯来诗歌的另一个独特特征。我们发现,这两个文献中都有好几百“对”单词,他们以固定的平行关系出现。这些传统上彼此关联的单词对,其相互平衡的关系是A单词出现在A行,平行的B单词出现在B行。辨认出“平行对”(parallel pair)极大地提高了我们解释希伯来诗歌的能力。[5]对乌加里特和希伯来经文的最新分析表明,这些词大约有七百对,虽然这些词出现的顺序不总是一成不变的,但目前非常清楚的是,确实有几百个词是平行成对出现的。[6]
除了平行结构和平行成对的词,希伯来诗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些很少或未曾出现的文法特征。一般说来,希伯来诗歌不用:(a)定冠词;(b)直接受格记号(אֶת或אֶת־);(c)连接词וְ(英文通常译为and);(d)所谓的关系代名词(希伯来文的אֲשֶׁר,英文通常译为which、who、that);(e)动词的连续或反转结构(就如未完成时态的反转waw,却在叙事上表示过去的时态;例如希伯来文的ניּאמֶר是“然后他说(过去式)”的意思)。这不是说这些形式从不在诗歌中出现,而只是很少出现,但它们在希伯来散文体中却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希伯来诗歌确实有其独特的标记,解经者不能仅仅为了方便、优美或卫道,就断定一段经文是诗歌体裁。
当解经者认为一段经文可能是诗歌体时,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断定它是否真是诗歌。1952年出版的标准修订本圣经(Revised Standard Version),是第一本将旧约诗歌部分完全以逐句分行的形式排版的英译本圣经(译者注:中译本中的吕振中译本,以及现代中文译本中的一部分,也是如此)。在此之前,只有旧约诗歌书才用这种形式,现在几乎所有希伯来文圣经的版本及译本,都试图指出诗歌形式的存在。这并不意味着解经者要将这些决定当作最终的和符合正典的,我们还是需要用前面所提的方法加以验证。
二、希伯来诗歌的诗段
1831年,弗里德里希·凯斯特(Friedrich B. Köster)的一篇文章[7]激发了学者们开始探究组成希伯来诗句的诗节(stanza)或诗段(strophe)。虽然有些学者仍怀疑这点,但从类似诗篇119篇之离合诗的存在可以看出,这种布局不但可能,实际上也有必要。因此,解释散文时怎样看段落,解释诗歌时就照样看诗段。
首先,最明显可以用来标明诗段的记号之一是“叠句”(refrains)。正如乌加里特诗歌以叠句来表示诗段的结构。圣经中用同样方式的有18首诗篇(诗39,42-43,44,46,49,56,57,59,62,67,78,80,99,107,114,136,144,145篇),先知书中也有同样的例子,如以赛亚书5,9-10章,摩1,2,4章等。其中诗篇46:7、11中的叠句是这样的: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更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诗篇42:5、11,43:5中三度重复的叠句: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燥?
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的帮助,是我的神。”
在以赛亚书9:8-10:4中,划分诗段的叠句出现了四次(9:12、17、21,10:4):
“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伸不缩。”
其次,除了用一再出现的叠句外,希伯来文的סֶלָה也常常用来作诗段结束的记号。“细拉”在诗篇第39篇及哈巴谷书3:3、9、13一共出现71次。但把这个不同寻常的词作为诗段的划分符号的问题在于,我们仍然不确定该词的意思,而且“细拉”这个词还出现在一些诗篇的诗题中,以致许多人认为它属于音乐上的指示。无论如何,如果“细拉”真的如一些人所猜测的那样是“上扬”的意思,那么它是音乐记号及诗段划分记号之说就可能不是不正确的,毕竟声音的“升起”或乐器的渐强很有可能出现在诗歌中某个思路的结尾,也就是诗节的末尾。因此,完全否认它作为诗段的划分符号是不公平的;因为有时它出现的地方,如果不是标志结尾的话就很别扭,它必定在其中一些例子中标志着诗段的结束。然而,在用“细拉”划分诗段时,必须非常小心。
第三种更为可靠的辅助方法,是字母的离合诗结构。采用这种结构的诗歌有诗篇9-10,25,34,37,111,112,119,145篇及耶利米哀歌1-4章。这种布局,第一节的第一个词以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头,第二节的第一个词以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开头,依此类推。在少数例子中,同一诗段的各行以同一个字母开头。不可否认,这几行应当组成一个诗段了。查尔斯·富兰克林·克雷夫特(Charles Franklin Kraft)又加了几个判断诗段的准则:(a)节拍或诗行的长度有显著的变化(一个诗段的最后一行可能会增长或缩短);(b)标语的重复(就如反复呼求“耶和华”,或开头、结尾有“耶和华如此说”或“这是耶和华说的”等语);(c)交错配列,或“内转平行体”(Introverted parallelism,例如一个四行的诗段,排列的方式是第一行和第四行彼此对应,第二行和第三行彼此对应,即A B B A的形式)。[8]
还有两种诗歌手法能帮助我们判断少数诗段的结构,就是行首额外音节(anacrusis)和“分隔平行体”(distant parallelism)。行首额外音节是一种作诗的技巧,将一个词(可能是疑问词或类似哀1:1“何竟”的感叹词)列在对句或诗段的基本平衡、平行形式之外。这些词的存在会影响后面所有的内容,这种手法常常出现在特别具有表达性的诗段中。[9]“分隔平行体”则被米切尔·达户(Mitchell Dahood)指称为平行成对的词彼此有些间隔的修辞手法。他举诗篇18篇מָחַצ(“打伤”)和צָמַת(“剪除”)的平行对作例子。“我要打伤”在39节(希伯来文章节),“我能以剪除”是在41节(同上),两者间隔四行。依达户看来,古代的听众或读者会认出这是一对平行的句子,并且本能地将这两句连起来。似乎“分隔平行体”也有可能作为我们检查诗段的第八个方法。[10]
以上种种都说明确定诗段是解经时不可忽略的事。就如段落都有一个中心思想,一切内容都围绕这个主题命题而组织。我们能肯定,诗段也展现了一个中心点,它的内容因此而组织起来。
由于基本上平行体由两行组成,偶尔也有三行的,因此最常见的诗段结构是两行或三行为一段。克雷夫特估计,诗篇中有70%-75%的诗歌是以两行为一个诗段的单元。[11]不太常见的是三行一段,也有极其罕见的四行或六行一段的例子(如诗19:7-9)。
还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是:那些由两行对句组成的诗(如诗18,28,39,40篇;也许诗2,16,17,23,26篇也属此)是否偶尔会将两对并作四行诗,而形成一个“诗节”?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像这样诗节的存在,大致上是可以肯定。至于对句会不会与三行混合、或偶尔甚至是单独的一行(因此不能看作是伪造的,也就是后人编辑的)合成一个诗节,就必须经过每一个单独诗段的检验,同时等待根据对同语系的语言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对希伯来诗歌更准确的分析而得出的明确答案。
三、希伯来诗歌的对句
现在,诗段的各种形式应该很清楚了。诗篇第2篇清楚地呈现四个三行段结构,[12]诗篇第20篇则有两个诗节(每诗节由一个四行段或两个对句组成)另外加上一行。克雷夫特把箴言第8章看成一首四节的长诗。
第一个诗节(1-9节):三个三行段。
第二个诗节(10-21节):六个对句,包括一个四行段(14-17节),组合成一个“套封平行体”(envelope parallelism)结构——四行段在诗节中间部分,两个对句在它的前面,两个对句在它的后面。
第三个诗节(22-31节):两个三行段(24-26、27-29节)套封在两个对句(22-23节和30-31节)中间。
第四个诗节(32-36节):两个劝诫用的结束对句。[13]
既然我们确定迦南和希伯来诗歌含有诗段,少数含有诗节,我们就必须问:我们当如何分析每个诗段和诗节的内容。这里我们不能像分析段落时那样依靠主题命题或主题句——至少不能像分析散文那样。
相反,解经者这时必须研究对句。对句是分析诗段时不得不考虑的,它由A、B两行构成,两者可能平行,也可能没有任何平行单元。然而,大部分对句呈“部分平行”(Parallelismus membrorum)现象;亦即两者的思想单元、意思单元和形式单元的均衡状况(三行段及四行段同此),但不像欧洲诗那种声音的平衡。
近年来,盖勒坚称,我们应该清楚地区分希伯来平行体的三种形式。[14]
(1)文法平行:指A行和B行的词在文法和形式上平行,意思上却不平行。例如,A和B两行的形式都是主语—动词—直接宾语,但这些词的意思并不相同。
(2)语义平行:指不仅是形式平行,连意思(或思想)也平行。
(3)修辞平行:这是用以产生一个特定文学效果的方法。[15]我们所说的“修辞平行体”(rhetorical parallelism)是指维系变语(Ballast Variant)、表记象征法(Emblematic Symbolism)、高潮平行体(Climactic Parallelism)、交错配列法(chiasm)、相代(Merism)及双关语(Paronomasia)等特点。
1. 语义平行体
文法平行对解经帮助不大。盖勒将洛思那稍微有点可疑的“综合平行体”(乔治·布坎南·格雷〔George Buchanan Gray〕称之为“形式平行体”),称为“文法平行体”,[16]但我们解经者对意思更感兴趣,把它称作“语义平行体”。它包括两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是“同义平行体”,它的第二行重复第一行的概念,意思上无所增减。当A行每一个“文法”单元都与B行同义时,它也是文法平行体,也有人称之为文法单元的“完全”匹配。下面是完全同义平行体的例子:[17]
|
a |
b |
c |
|
以色列 |
却不 |
认识 |
|
a׳ |
b׳ |
c׳ |
|
我的民 |
却不 |
留意(赛1:3) |
|
|
||
|
a |
b |
c |
|
行恶的 |
留心听 |
奸诈之言 |
|
a׳ |
b׳ |
c׳ |
|
说谎的 |
侧耳听 |
邪恶之语(箴17:4) |
平行体常常是同义的,却省略了一个关键单元(可能是主语、动词或及物动词的宾语)。这种情形称为“不完全”(即文法上不完全)的同义平行体。
|
a |
b |
c |
|
|
(位置调换,下同) |
连同充满其中的 |
|
a׳ |
b׳ |
c׳ |
|
〔 〕 |
世界 |
连同住在其中的(诗24:1原文次序) |
但这种情形在修辞上有其用意。这是居鲁士·赫茨尔·戈登(Cyrus Herzl Gordon)所谓的“维系变语”(ballast variant),[18]它的对句或三行段中,有一个文法单元没有可匹配的单元(如诗24:1的“属耶和华”),乌加里特和希伯来诗歌都常常在此加长这一行作为补偿,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出:
|
a |
b |
c |
|
|
A出去了 |
以色列 |
从埃及 |
|
|
〔a׳〕 |
b׳ |
c׳ |
d׳ |
|
B〔 〕 |
雅各家 |
从百姓 |
说异言的 |
|
(诗114:1原文次序;参耶17:10下) |
|||
注意,a单元在B行没有可对应的,但B行又为这个空缺加了一个补偿的维系词,我们就把“说异言的”这个短语以戈登的“维系变语”来称呼。相同修辞作用的另外一个例子在诗103:7(原文次序):
|
a |
b |
c |
|
|
他使知道 |
他的法则 |
摩西 |
|
|
a׳ |
b׳ |
c׳ |
d׳(维系变语) |
|
〔 〕 |
他的作为 |
子民 |
以色列的 |
语义平行体的第二种形态是“反义平行体”(antithetic parallelism)。这种形态的第二行与第一行的思想或意思相对或相反。最常出现反义平行体的地方是旧约的智慧文学部分,尤其是箴言10-22章。下面是一些“完全”反义平行的例子:
|
a |
b |
c |
|
回答柔和 |
使消退 |
怒 |
|
a׳ |
b׳ |
c׳ |
|
言语暴戾 |
触动 |
怒气(箴15:1;参15:2、20,原文次序) |
|
|
||
|
a |
b |
c |
|
公义 |
高举 |
邦国 |
|
a׳ |
b׳ |
c׳ |
|
但罪恶 |
羞辱 |
人民(箴14:34原文次序) |
有时相对的思想并不表现在对句的内涵中,而是外在的,表现在两个对句之间。以赛亚书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
a |
b |
c |
|
|
牛 |
认识 |
主人 |
|
|
a׳ |
b׳ |
c׳ |
d׳(维系变语) |
|
驴〔 〕 |
|
主人的 |
槽 |
|
a |
b |
c |
|
|
以色列却 |
不 |
认识 |
|
|
a׳ |
b׳ |
c׳ |
|
|
我的民却 |
不 |
留意(赛1:3原文次序) |
|
句子中间的反义词“却”的出现,使我们明白在两个对句之间有清楚的外在相对现象(其中一个对句有维系变语)。
2. 修辞平行体
除了形式、思想和意思有均衡的情形,希伯来诗歌还用了许多修辞手法来增加美感并简化其意思。我们已经观察到“维系变语”在两种平行体中的作用,尤其在同义平行体中似乎更为适合。
乌加里特(迦南)诗歌和希伯来诗歌,与其他闪族和古典诗歌形式不同的一个有趣特征是,它们有省略动词的情形。[19]因此,乌加里特诗歌有这样的例子:
|
a |
b |
c |
|
|
你要得 |
你永远的 |
国 |
|
|
〔a׳〕 |
b׳ |
c׳ |
|
|
〔 〕 |
你永恒的 |
统治(经文68:10或Ⅲ: AB,A: 10) |
|
|
|
|||
|
a |
b |
c |
d |
|
因一子 |
生了 |
给我 |
如我的兄弟 |
|
a׳ |
〔b׳〕 |
〔c׳〕 |
d׳ |
|
一枝 |
〔 〕 |
〔 〕 |
如我的亲族(Ⅱ D;2:14-15) |
希伯来文同样有这种情形:
|
a |
b |
c |
|
杀死 |
扫罗 |
千千 |
|
〔a׳〕 |
b׳ |
c׳ |
|
〔 〕 |
大卫 |
万万(撒上18:7下,原文次序) |
|
a |
b |
c |
|
大山 |
踊跃 |
如公羊 |
|
a׳ |
〔b׳〕 |
c׳ |
|
小山 |
〔 〕 |
如羊羔(诗114:4,原文次序) |
|
(行首额外音节) |
a |
b |
c |
|
诚然 |
壮年人 |
我杀了 |
因我受的伤害 |
|
|
a׳ |
〔b׳〕 |
c׳ |
|
|
少年人 |
〔 〕 |
因我受的创痛 |
|
|
|||
|
(行首额外音节) |
a |
b |
c |
|
诚然该隐 |
|
遭报 |
七倍 |
|
a׳ |
〔b׳〕 |
c׳ |
|
|
拉麦的 |
〔 〕 |
七十七倍(创4:23-24,原文次序) |
|
像这样,在迦南诗歌和希伯来诗歌中,对句的文法主语和宾语在两行中彼此相当或相同时,“第二”行的动词可以省略,但从不省略第一行。为了补足这个空缺,就再加入维系变语以保持对句的一般样式;事实上,有时动词甚至可能是特意省略的,以便对主语或宾语进行更充分的解释。
有些对句一行是字面的或事实的陈述,另一行则是喻意的说法,以明喻或暗喻的形式表达。这种方式称为“表记象征法”(emblematic symbolism)。下面的例子中明喻或暗喻部分以粗字体表示:
妇女美貌而无见识,
如同金环带在猪鼻上。(箴11:22)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
如鹿切慕溪水。(诗42:1)
有好消息从远方来,
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箴25:25)
表11·1
乌加里特诗歌和希伯来诗歌中高潮平行范例
|
irš • ḥym • laqht • ǵzr
irš • ḥym • watnk
bl mt • wašlḥt |
亚卡的少年人哪,求生命吧;
求生命,我便给你们;
不朽,我便赋予你们。
(Ⅱ Aqht 6:26-28)
|
|
bkm • tmdln• ʾr
bkm • tṣmd • pḥi
bkm • tšu • abh |
她哭着为驴子上鞍,
哭着为驴驹套车,
哭着把她父亲举起。
(ⅠAqht 57-59)
|
|
knp • nšrm • bʿl • ytbr
bʿl ytbr • diy • hmt
tqln • tḥt • pʾny
(wyql • tḥt • pʾny) etc. |
愿巴力折断鹰的双翼;
Hrgb
Sml
愿巴力折断它们的翅,
使它们仆倒在他脚前。
(I Aqht 107,114,118,122,
128,132,136,142,148)
|
|
bl • ṭl • bl • rbb
bl • šrʾ • thmtm
bl • ṭbn • ql • bʿl |
没有露水,没有雨,
没有两渊的澎湃
没有巴力声音的美好。
(ⅠAqht 44-46)
|
|
כִּ֤֯י הִנֵּה֪ אֹיְבֶ֡יךָ׀יְֽהוָֹה |
因为,瞧!你的仇敌,耶和华啊! |
|
כִּֽי־הִנֵּה֣ אֹיְבֶ֣יךָ יֹאבֵ֑דוּ |
因为,瞧!你的仇敌都要灭亡。 |
|
יִ֝תְפָּרְד֗וּ כָּל־פֹּ֥עֲלֵי אָֽוֶן׃ |
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 |
|
|
(诗92:9〔10〕;参乌加里特经文68:9) |
|
נָשְׂא֤֯וּ נְהָר֨וֹת׀ יְֽהוָ֗ה |
大水扬起了,主啊, |
|
נָשְׂא֣֯וּ נְהָר֣וֹת קוֹלָ֑ם |
大水扬起了它们的声音; |
|
יִשְׂא֖֯וּ נְהָר֣וֹת דָּכְ֯יָֽם׃ |
大水要扬起它们的波浪。 |
|
|
(诗9:3) |
|
שִׁ֣ירוּ לַ֭יהוָה שִׁ֣יר֯חָדָ֑שׁ |
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哪: |
|
שִׁ֥ירוּ לַ֝יהוָֹה כָּל־הָאָֽרֶץ׃ |
要向耶和华歌唱,全地啊。 |
|
שִׁ֣ירוּ לַ֭יהוָה בָּרֲכ֣וּ שְׁמ֑וֹ |
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 |
|
|
(诗96:1-2) |
|
כִּ֬י֯בָׄא |
……因为他来了, |
|
כִּ֥י֯בָא֮ לִשְׁפֹּ֪ט הָ֫אָ֥רֶץ |
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 |
|
יִשְׁפֹּֽט־תֵּבֵ֥ל בְּצֶ֑דֶק |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
|
וְ֝עַמִּׄים בֶּאֱמוּנָתֽוֹ׃ [ ] |
按他的信实〔〕万民。 |
|
|
(诗96:13) |
另一个修辞的技巧是“高潮平行体”(climactic parallelism),或称“阶梯式平行体”(staircase parallelism),涉及一行中的两三个词在其后的数行(通常是三四行)中重复出现或发展。留意这样的重复能帮助解经者更好地理解该诗歌的重点和美感。[20]一行行重复的现象,在迦南和希伯来诗歌中十分常见,表11.1中列了一些例子。
圣经诗歌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交错配列(Chiasm)。指下一行中颠倒对应词语的次序,或甚至指四行段中一、四行互相对应,二、三行互相对应(或一与三行,二与四行对应),英文名称chiasm就是由希腊文字母χ(chi)而来的,因为它的形状类似英文字母x。表11.2中列出简单型、线型及二对句四行段等各种的交错配列,其中最后一个例子的“拉哈伯”不能相当于“海”(יָם),而是“海中”的活物,也许是像大鳄鱼一类的大型海中动物。同样,“快蛇”也不是天的本身,而是天上的一种“现象”,可能是日食。
“相代”(merismus)是一种类似“举隅法”(以部分表示全体,或以全体表示部分的叙述法)的表达技巧,它只列出全体的各部分,甚至更多时候只列出其中的几项(常常是第一项和最后一项,或更显著的部分),以此表明全体。
“相代”最好的例子是玛拉基书1:11,说到神国的得胜是“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也就是“遍及全世界”。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类似的说法,就是他的王权从“此岸到彼岸”。
|
表11.2 希伯来诗歌交错配列范例 |
|||
|
简单型(abba或abccba) |
|||
|
|
a |
b |
c |
|
A. |
以法莲 |
必不嫉妒 |
犹大 |
|
|
c׳ |
b׳ |
a׳ |
|
B. |
犹大 |
也不扰害 |
以法莲(赛11:13下) |
|
线型(abba) |
|||
|
A. |
我儿 |
“智慧”若存在你心 |
|
|
B. |
也甚欢喜 |
“我的心” |
|
|
C. |
也必快乐 |
“我的心肠” |
|
|
D. |
当说时 |
你的嘴 |
“正直话”(箴23:15、16,原文次序) |
|
二对句四行段(abab) |
|||
|
A. |
用他的能力, |
“大海”就平静。 |
|
|
B. |
借他的通晓, |
他击伤 |
“拉哈伯” |
|
C. |
借着他的嘘气 |
“天空” |
就晴朗 |
|
D. |
他的手 |
又刺杀了 |
“快蛇”(伯26:12-13原文) |
“相代”包含表示时间、地点、人、事物甚至某些动作的实词。这样,一般概念就可以包含在特殊概念里面,而不必使用抽象概念。 这种表达法(或修辞手法)在诗歌及散文中都出现过。[21]
希伯来诗歌的巧妙和优美,可以由它惯于使用“双关语”(paronomasia)及谐音字而略窥一二。东方人特别喜欢这类俏皮话。
很多时候,先知将声调类似的词摆在一起,让人明白他的意思。先知在以赛亚书5:7宣称,神指望“公平”(מִשְׁפַּט)和“公义”(צֽדָקָה),却得到“暴虐”(מִשְׂפָּח)和“冤声”(צְעָקָה)。
耶利米蒙召时,神给他展示一根“杏树枝”(שָׁקֵד),并把这与他正在“留意保守”(שֹׁקֵד)他的子民的这一事实联系起来,若他们不赶快悔改,神要叫审判速速来临。用个不太恰当的中文谐音字(在声音和文化上,犹太的杏树枝像我们的杏树,也就是春天最先开花的果树,是春天的预兆),这比喻可以这样说:神指示耶利米一根“杏树枝”,并说:“如果我的百姓不赶快悔改,我要这样‘迅速治’他们”(参耶1:11-12)。
因此,解经者现在有六种修辞上的方法,可以帮助他捕捉神信息的微妙了,但在研究的时候,心思还是要集中在每个诗段的中心点上,这样才能从中得着信息的要点。此外,为了发展次要点,解经者还必须分析圣经诗歌所采用的形式。例如,若是诗歌用反义平行表达出相反的陈述,解经时也必须讲出其间的对比。
在一个诗节或较大的诗段中若找不出哪一行是主题的陈述,这时修辞的方法可能有帮助。例如,诗篇第2篇有四个三行诗段,前面两段都以一句宣言结束:3节是背叛者的宣言,6节是神的宣言。因而前面两段的主题分别集中在3节和6节,结果1-2节和4-5节就是扩充主题的分支。
同样,面对不平行的单元,解经者必须再次大量依赖修辞的方法。当然,如果所有表面结构特点(包括文法平行和句法)都没有什么线索,我们就必须考虑语义结构(即意思、逻辑)了,只是要注意,主观思想远不如扎实的解经可靠。
四、圣经诗歌的宣讲
圣经中最出名的诗歌是大卫的诗,但诗篇中还包含其他作者的诗歌,该卷书也只是有时被称为智慧书的一卷,智慧书还包括约伯记、箴言、传道书和雅歌。
然而,智慧书并没有囊括圣经中以诗歌形式写成的大量诗歌体材料。历史书中也有诗歌,如“拉麦自负歌”(创4:23-24)、“雅各祝福众子歌”(创49章)、“摩西之歌”(出15章)、“底波拉之歌”(士5章)、大卫所作“扫罗与约拿单的哀歌”(撒下1:19-27)等。更重要的是,在旧约的16卷先知书中,有14卷书含有大段的诗歌。其实旧约只有7卷书完全没有诗歌,即利未记、路得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哈该书和玛拉基书,旧约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以诗歌形式写成的。
新约中也不乏诗歌的例子。虽然新约中没有哪卷书可算是诗歌体裁,但诗歌还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弗兰克·盖布兰(Frank E. Gaebelein)的分类,新约的诗歌可以分成五类。
(1)引自古诗句。克里特的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徒17:28);基利家的亚拉图〔Aratus〕和斯多亚派的克里安西斯〔Cleanthes〕说:“因我们是他所生的。”(徒17:28);埃庇米尼得斯又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多1:12);以及雅典的喜剧诗人米南德(Menander)所说:“滥交是败坏善行。”(林前15:33)
(2)引自不详诗歌(可能是1世纪信徒的赞美诗)的句子(弗5:14〔参19节〕;腓2:5-11;提前3:16和提后2:11-13)。
(3)采旧约诗歌模式的段落(路1:46-55的马利亚颂;路1:68-79的撒迦利亚颂;路2:14的荣耀归主颂;和路2:29-32的西面颂)。
(4)没有押韵或韵律,却具有丰富情感,有高尚、宏伟形式的篇章(如八福,甚至全部登山宝训;路13:34-35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以及“楼上谈话”的片断,约14:1-7)。
(5)启示性意象,如橄榄山谈话,或启示录中的赞美诗(如启4:8、11,5:9-10、12-13,7:15-17,11:17-18,15:3-4,18:2、8、14-24,19:6-8)。[22]
新约部分的大多数诗歌都很受范围的限制,它们不够长,不足以作为讲道的唯一焦点。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橄榄山谈话和登山宝训。
但一般说来,新约诗歌的主体是赞美诗和歌曲。如果诗歌的风格很像希伯来诗歌,我们可以像研究旧约诗歌那样对其进行研究。但是,如果诗歌是非散文形式和智慧材料(如登山宝训)或预言象征(如橄榄山谈话)的结合体时,解经者就必须特别注意各个不同文学类型(如智慧文学、启示文学)的特点和细微差别。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解经者常会在智慧文学中遇到单元小得多的材料,甚至比诗篇中的对句和三行段还小。箴言中的各个对句虽然可组合成一个诗段,但每个对句本身却常常是一个单一的独立单元。
箴言10-22章更是如此,其中反义平行例子极多,各对句“之间”常常很难找出可察觉的关系。对这种特例,上下文分析就没有什么用了。这时候解经者要谨慎行事(解释登山宝训和雅各书也是如此),不仅要充分重视诗歌形式,还要考虑到一系列的比喻表达方式,以及夸张和极端的修辞手法,来说明优先、相似、对比及因果等关系,并且依行为和境遇将人加以刻画。
也就是说,箴言是高度凝练的。它是从一整篇教训中提炼出来的,以达到强调的目的。因此,若不将它放回完整的背景中,就很容易误解。所以下面的步骤可以帮助我们硏究智慧诗歌。
(1)首先要断定箴言材料的性质。是比喻(传9:13-18),还是寓言(箴5:15-18)、明喻(箴25:13、19、20、25),或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停顿思考才能抓住其比较或隐喻的难题(箴26:8)。
(2)如果上下文有帮助,就使用它。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箴言16章,其中有一系列关于“谋事在人,成事在神”的箴言。
(3)如果看不出跟上下文有任何关系,就使用希伯来平行体中比较明显的一行来解释比较困难、费解的一行。
(4)在应用智慧经文中的原则时,要注意,它们并不意味着适用于所有的场合。例如,箴言16:7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但显然还有例外。箴言的本质是:如果“其他一切情况都相同”,那么这会是对的。
圣经中的诗歌形式,无疑比大多数散文给解经者带来的问题更多。尽管这增加了解经的负担,但诗歌形式也带来了额外的优美和情感色彩,这是散文形式通常难以传达的。原则上,解释诗歌的步骤与解释散文是一样的。
(1)确认该诗歌的范围。
(2)把诗歌划分为诗节或诗段。
(3)找出平行结构中的主题行或基本主张。
(4)说明主题命题在诗歌中如何发展或解释。
(5)把主题重述为不受时间、人物、文化、空间限制的原则。该原则的表述形式还应当引导会众,以某种方式回应那位首先赐下这些话语的永生神。
[1] Robert Lowth, Lectures on the Sacred Poetry of the Hebrews.译自 De sacra poesi hebraeorum praelectiones academicae (Oxford:Clarendon, 1753)。
[2] Stephen A. Geller, Parallelism in Early Biblical Poetry, 页375-376。他又尝试将平行的“程度”依人所设定的语义等级加以区分,他也提到“修辞”上的关系。
[3] Robert Lowth, Isaiah:A New Translation, with a Preliminary Dissertation and Notes, Critical, Philological,and Explanatory,第10版(Boston: Peirce, 1834),ix页。
[4]自洛思以来硏究希伯来诗歌的一些重要论述,列在T. H. Robinson, “Hebrew Poetic Form: The English Tradition,”的研究报告中。
[5] “平行对”更深入的讨论,见H. L. Ginsburg, “The Rebellion and Death of Ba’lu,”Orientalia 5(1936):171-172;以及Mitchell Dahood的权威文章 “Ugaritic-Hebrew Parallel Pairs,” 收录于Ras Shamra Parallels: The Texts from Ugarit and the Hebrew Bible, 目前有二册,Loren R. Fisher所编,Analecta Orientalia:Commentationes Scientificae Derebus Orientis anti- qui, 49 (Rome: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 1972-),1:73-382。
[6]除了Mitchell Dahood在“Ugaritic-Hebrew Parallel Pairs,” 所列的624对平行对以外,他又列了66对在Ras Shamra Parallels中Fisher编,2:3-39;及同作者之Paslms,.共3册,The Anchor Bible, William Foxwell Albright和David Noel Freedman编(Garden City, N.Y.: Doubleday,1966-1970),3:445-456。乌加里特文和希伯来文共计有690对平行对。
[7] Friedrich B. Köster, “Die Strophe, Oder der Parallelismus der Verse der Hebräischen Poesie,” Theologische Studien und Kritiken 4(1831):40~11。近代有Kemper Fullerton, “The Strophe in Hebrew Poetry and Psalm 29,”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48 (1929):274-290;和Charles Franklin Kraft, “Some Further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Strophic Structure of Hebrew Poetry.”
[8] Kraft, “Some Further Observations,” 65-66页。用交错配列法检验诗段结构,陈述于Nils Wilhelm Lund, “The Presence of Chiasmus in the Old Testament,” 尤在104-109页中。然而,克雷夫特认为,D.H.Müller, Hans Möller和Albert Condamin的意见流于极端。
[9] R. K. Harrison, “Hebrew Poetry,” 收录于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Merrill C. Teruicy编,共5册(Grand Rapids:Zondervan, 1975),3: 82。
[10] Dahood, “Ugaritic-Hebrew Parallel Pairs,” 80-81页。
[11] Kraft, “Some Further Observations,” 71页。
[12]同上,85页。
[13]同上,86页。值的一提的是,克雷夫特从乌加里特文献“巴力和亚拿始末”(Cyrus Gordon’s Text 51 : IV — VI :59)中之185行所作清楚可靠的分析,在同书74-84页。克雷夫特写道:“三个对句后接四个三行段,或其他对句,然后是两个三行段;之后进入争论的高潮。只有短对句,独立行,甚至只有单独诗句存在;接着又有一个三行段和一个含有对句的独特三行段,后面是一个对句、两个四行段和一个结尾对句。”(83-84页)
[14] Gel Ier, Parallelism,15-16,31-34,375-377页。
[15]同上,32页。
[16]同上,375-385页。
[17]这些例子尽量照希伯来原文的次序,由译者直译。
[18] Cyrus H. Gordon, Ugaritic Textbook:Grammar, Texts in Transliteration, Cuneiform Selections, Glossary, Indices, Analecta orientalia: commentationes scientificae de rebus Orientis antiqui, 35 (Rome: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 1965), 135页。
[19]同上,§13 : 105。另见Edward L. Greenstein, “Two Variations of Grammatical Parallelism in Canaanite Poetry ind Their Psycholinguistic Background,” 89-96页。
[20]进一步的讨论见Greenstein, “Two Variations,” 96-105页;Samuel E. Loewenstamm, “The Expanded Colon in Ugaritic and Biblical Verse.”
[21]圣经例子更广泛的讨论,见A. M. Honeyman, “Merismus in Biblical Hebrew.”
[22] Frank E. Gaebelein, “Poetry, New Testament,” in Zons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Tenney编,4:813-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