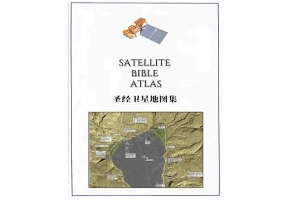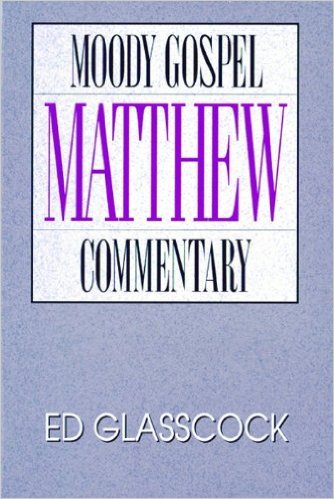第六章 神学分析
如果一个阐释者作过一番够水准的文法、句法、文体结构和历史背景的分析,而所预备的信息却令人感到平淡无奇,那么不会有什么比这更叫他受挫和气馁的了。当解经者费尽心思翻译经文、分析动词、硏究历史背景,又追溯句法关系,结果这一切努力却不能给现代人带来一个可信的、能够引起共鸣的信息,实在会叫他自己觉得不够忠心。很明显,他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那是什么呢?
大多数讲章在预备时所缺少的就是神学解释。特别是对那些刚从神学训练机构获得崭新证书的新传道人而言,最诡诈的圈套莫过于历史主义或纯粹的“描述主义”。许多受训的神职人员致命的弱点就是,无法将圣经文本从公元前或公元1世纪的背景中带出来,并将其直接合适地应用在今天。
很不幸,如果圣经学习把所研究的段落分解成各种文法、句法、历史和体裁等,然后不能再进一步研究了,那么圣经学习变成了“种子”。我们一点也不过分地说,前面各项工作不过是“完成文本的研究、以便宣讲经文”之最关键步骤的一个预备工作。如果在这一点上停止,就像把“临门一脚”交给神的子民——也许还挥挥手,把事情交给圣灵,期望他在每一位信徒心里作善工!
其实,这种情形下所发生的事实十分可怕。我们把一大堆五花八门的圣经事实陈列在神子民面前,其中夹杂着现代的琐事和幽默轶事,却不帮助他们辨认出圣经中哪些内容时至今日仍然是规范且带权柄的。他们若得不到进一步的帮助,如何能够明白神在经文中对他们具体而直接的指示呢?
这问题在引用旧约经文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很多牧师、教师尽量避免引用旧约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毕竟不是个值得嘉许的办法,因为很明显,他们故意略过75%的神旨意,他们怎么能在神面前证明自己无罪,像保罗一样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说”(徒20:27)!
有些牧师和解经者试着不落入史实主义和描述主义的圈套,就再借助各种当受指责的方法解经,比如赋予道德含义、寓意化、心理化、灵意化和对所选经文加以主观编辑等。很快地,许多所谓的“翻译者”就非常熟练地掌握了其中的一种甚至全部作法。这些可恶的方法还有另一个更大的诱惑,对于那些已经忙忙碌碌超负荷作工的牧师来说,是真正节省时间的方法。他们的时间很容易就分割成千百个片段,而不需要每周不得不抽出二三十个小时来预备两篇坚实的圣经信息。于是,各种不请自来的见证渗透到神学训练机构,在这些“新上手”的节省时间的解经者中,一些人以前就是那里毕业的。他们的信息是:“预备讲章时,要忘掉所有历史、文学、文法等方面的工具,这些都没有用处!”
结果很明显,这些解经者发现,准确地定位圣经作者所在时空情景中的文本,耐心地识别文体形式和文法结构,这些专业作法所得的结果纯粹是分析性的。我们不能对他们的想法进行苛责,毕竟他们至少还能感觉到需要一些别的东西。只是他们选择了眼下最容易的路,凭己意给经文赋予各样属灵或实践价值,不管圣经原作者心里可能有什么想法。这太遗憾了!幸运的是,对于他们和听众来说,同样的标准多半可以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找到,只要他们知道在圣经的哪里找得到。然而,会众和牧师仍得意于他们自己的方法,没有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从所查考的经文中体验神的话,而是从圣经中一些未知的地方引入材料,并将这些材料混入所查考的经文中!
同时,可能是传讲者和会众关注焦点的文本,本来可以为神子民揭开神的话语,但因为它的意思没有解释,反而被更深地埋在传统、轶事和流行的烦絮中——只有期待在传讲时能有神的权柄了。
至此,很显然哪里出错了。神学训练机构的解经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和实践神学系(讲道学),在解经与讲道程序最重要的步骤上出了问题。我们相信,最常见的问题出在神学解释上。
成功的解经,一定要有确定经文的中心信息或核心的步骤。只有确定经文的核心,并确定“写作经文的那个时代”已被视为正典的各卷书,解释者才能认定神所规范的话语。然而我们要再次强调,在处理经文时,将一个神学框架强加于经文,绝不可以代替通过归纳过程努力找到一个统一的神学原则。仅仅将一个神学框架强加于经文是愚笨而懒惰之解经者的特征,必须被谴责。我们还要抵制把看似有相似的词或主题的经文随意牵联在一起(通常叫作经文自证法),因为尚未证明所有引用的经文确实是在传讲一个相同的神学主题或实际内容。
一、前述经卷类比
解决我们前面所提问题的一个方法是使用“信仰类比”(analogia fidei)的原则。这个词显然最早是由早期教父奥利金(Origen)[1]使用的,他从罗马书12:6(“按着信仰的类比”,和合译本译作“照着信心的程度”)中借用了这个词。不过,在保罗使用这个短语的上下文中,它指的不是神学真理的体系,而是指属灵恩赐的运用,要照着个人信心的程度。
宗教改革者广泛使用了这个短语,在他们的时代,这个短语的意思与一系列非常独特的环境有关。天主教发布了“标准注释”(Glossa ordinaria),这是一部注释,要求在所有与信仰和生活有关的事项上保持一致。但是,宗教改革者反对这个“信仰规则”(regula fidei),因为它被认为是“独立”于圣经之外的权柄。他们坚称,所有信仰和实践的准则都必须“惟独圣经”(sola scriptura),但圣经仍然需要解释,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宣称“以经解经”(Scriptura Scripturam Interpretatur)。于是,“信仰类比”就成为“以经解经”的结果了。
但是,信仰类比的定义并不总是清晰的。约翰·约翰逊(John F. Johnson)有一种定义方式:简单地说,“类比”或“信仰准则”是指“清楚的经文”本身;这指的是那些在经文中找到的、明确处理个别教义的“信条”(sedes doctrinae,基本教义)。个别的教义是从这些基本教义中提取出来的,必须根据基本教义来判断。任何教义,如果不是从明显涉及该教义的经文中抽取的,一律不予接纳作符合圣经的教义。[2]依照约翰逊的看法,信仰类比受限于我们所说的坚持,即教义最初来自于将该教义叙述得最完全的大段经文(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我们的问题是,信仰类比是否是一个开启所有经文的解经工具。
在这个特定的问题上存在混淆,这种混淆导致过去和现在对这一准则的滥用。许多人忘了,宗教改革者所用的信仰类比是一种“相对”的表述,是特别针对当时“传统的专制”而说的,“只是为了要推翻‘传统是圣经的解释’之说”。[3]因此,这并不意味着圣经的所有教导在各处都表达得同样清楚,也不是要摒弃使用文法书、注释书或训练有素的神职人员来帮助解释和理解圣经,否则宗教改革者很难解释自己为何写了注释书,还使用了各种解经工具。
更重要的是,它的意思并不是如威登堡(Wittenberg)和耶拿(Jena)的希伯来文教授马蒂亚斯·弗拉齐乌斯(Matthias Flacius)在他的《圣经之钥》(Key to the Scripture,1567)中所写的:“关于圣经所说的一切,或以圣经为基础所说的一切,都必须与要理问答所宣称的或信条所教导的一致。”[4]这样的说法完全本末倒置,回归到一套传统,这些传统不仅重新独立于圣经行使权柄,而且在有关圣经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之间充当解释者和仲裁者。
我们的看法是,当“信仰类比”被用作解经程序的一部分时,用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的术语来说,最好将其重新定义为“会通”各处圣经经文的神学。[5]布莱特认为,每一段圣经经文中都含有某个层面的神学,以这种方式构成经文内容整体的一部分。该神学虽然不能从整段经文中被剥离,但它往往根源于该段经文的“前述经文”。
关键就在“前述经文”上。要纠正过去和现在以神学解经的名义所发生的滥用,我们所知的唯一方法是严格地限制解经程序,使它:(1)检查在所解释的经文中明确的声明;(2)将该声明与“较早期”著作中相似(有时不尽完全)的声明作比较。因此,释经学(hermeneutical)或解经学(exegetical)使用信仰类比(如果我们仍然可以在解经学也如系统神学般地使用这个词,虽然在系统神学中它似乎更合宜)必须在年代顺序上严密控制(亦即我们必须认识启示过程中各时期的顺序)。这一点太重要了,为此我们更倾向于把释经学用到的这个步骤另起一个名称,叫“(前述)经卷类比”(analogy of [antecedent] scripture),免得在概念上有任何可能的混淆。不管用哪一个名称,最重要的是它的定义。
当然,如果我们只从所查的经文和更早期的经文中做神学观察并得出结论,那么大部分解经者一定能看见其中的智慧和好处。但许多人惊讶地发现,这个方法并不能帮助我们找出经文的“前述神学”。在这里,我们要再说,神学必须从经文中客观得来,而不是解释者主观地强加给经文。
在经文中的前述神学有几个线索。
(1)特定词的使用,即已经在救赎历史中具有特别意思,并且开始具有术语地位的词(如“后裔”、“仆人”、“安息”、“基业”)。
(2)为了做出相关的神学陈述,直接、间接地提到启示过程中的先前“事件”(如出埃及记,西奈山的显现)。
(3)直接或间接地“引用”经文,以便使它们适合于新情况下相似的神学点(例如,“要生养众多……”;“我是你们祖宗的神”)。
(4)论到“约”,在其中累积的“应许内容”,或它的语式等方面的语句(例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你)从埃及地(迦勒底的吾珥)领出来”;“我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住在你们中间”)。[6]
我们现在所主张的,不仅仅是把圣经神学作为我们解经的一部分,而是要求圣经神学全面融入解经的过程中。正如我们所以为的那样,从这门学科及其在神学课程中的特殊使命看来,它必须按照历史年代来编排,以便使它的主要贡献不是为了系统神学(如以前有时所说),而是为了解经学这一领域。
这样,圣经神学应该为解经者搜集所有切题的神学材料,并将它们按照历史加以分类(如族长时期、摩西时期、王国前时期等)。但是,这样的教义汇集绝不只是以某种方式与以色列或教会的信仰及生活模糊联系的大杂烩。
只有当手中所有累积的神学体系有一个正典中心(canonical center)时,这种“会通神学”才有意义。但其中存在着另一个现代问题,当今这个领域的作者都不愿把任何具体元素当作组织原则或圣经神学的中心。没有人能怪罪大多数圣经神学家的不情愿,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理由害怕陷入曾经非常普遍的诱惑,所以不愿把任何哲学或神学框架加在经文中。过去曾有经文以外的体系被置于经文之上,试图从圣经中得出神学效益。每个人都知道这和罪一样不能被接受,它最多不过是照个人喜好的理论框架或特定教义重新构建经文。但是,当经文经过如此主观的处理之后,还有何权柄与指导可言呢?
然而,这种过度行为可以成为抛弃“寻求圣经自身的神学中心”的正当借口吗?我们以为不然,因为如果圣经的旧约、新约,或者两者真的有所谓的圣经神学,我们最终的目标就应该是找出并确定那种内在的统一,将所有不同的作者、主题和历史联系在一起。我们不能说,最终这统一对我们来说仍是隐藏的,或者说神自己就是这统一;因为前一种情况从根本上否定了“启示”的概念,这与经文中声称神向人类开启和昭示的内容相悖;后一种情况只说明了神学主体是谁,却没有给我们任何形式的谓词。
直到最近,圣经神学家们极力推崇的统一原则是:“历史”是神启示的主要媒介,可能是将不同圣经作者的各种“神学”凝聚在一起的因素。但即使是这种看法,也遇到严峻挑战。[7]
然而,旧约和新约的神学,确实存在一个正典中心,它不是外加的,而是可以从仔细阅读圣经作者们的作品中归纳出来,那就是神“赐福”的话语(在亚伯拉罕之前的内容中尤为突出使用的词语)或“应许”的话语(总结了旧约内容的新约用词),神要“作”以色列的神,要为以色列“行”事,并要“借着他们”为地上“万国”行事。起先,这话是神给人的惊喜;之后,这话的内容以不同的方式在整本圣经中重复。这固定语式一再地出现,新的条款不断地加入、累积,历史则说明了它在过去和现在的应验,一切事物都围绕着这个中心。[8]
因此,圣经神学这一学科必须与解经神学齐头并进。就教会而言,如果没有“会通神学”(informing theology)支持,解经神学(Exegetical theology)将仍然是不完整的,其结果实际上近乎贫乏。解经者应该在他的书桌上放一本标记清晰的圣经神学参考书,以及词汇和语法书,而且如果参考书有经文索引和主题索引,那将是最有帮助的,这样解经者就能迅速使用这一工具,不必翻阅整本书来查找所硏究主题的相关注解。
我们所说圣经神学这个新角色的重要性,以及它对解经过程的影响,总不会言过其实。它应该足够填补在宗教改革时期和宗教改革之后早期极擅长神学解经的解经家留下的空白。我们相信,此处推介的这个方法能更充分地呈现这些作者心里的想法。
如果有人抱怨说,没有一个基督徒解经者能够或应该忽略比所研究经文更晚期、更完全的经文。我们的回答是:“当然,没有人希望解经者忽略它。”神学启示的后续发展(晚于所研读的经文)可以(其实是“应该”)放在“结论”或“总结”之中,这是在经文的正确意思已经通过解经确认之后。我们的确有整本圣经,而且听众又(常)是基督徒,因此在总结的时候,我们应该指出该启示的后续发展,目的是更新,把内容放在更完整的背景中。晚期教训无论如何不能用来解明所研读经文的意思,或用来增加我们所研读之经文的用途。
二、神学词典
另一个解读经文神学意思的方法就是求助于本世纪才有的独特工具书:词汇书。这类书不应该跟词典、圣经词典、注释书和经文汇编混淆,它们有独特的形式和目的。词汇书通过以下途径试图对圣经中前导的神学概念(leading theological concepts)加以定义:(a)追溯这些词汇在论及它们的主要经文中的意思;(b)追溯这些词汇在圣经著作中的历史演变。[9]所以,这类工具书能帮助解经者核对圣经神学方面已经完成的工作,包括对所研究的经文中的词汇所下的结论。
现存最早的这类参考书是赫尔曼·克里默(Hermann Cremer)所著的《新约希腊文圣经神学词典》(Biblico-Theological Lexicon of New Testament Greek)。[10]克里默试图在神学词汇的圣经外用法中找到各个词意思的独特细微差异。他希望能借着探讨圣经内外的全部意思,指出这些词的圣经用法和经外用法之间的确切联系和差别。然而,克里默并没有将他的硏究范围扩大到教父时期的希腊文。[11]
格哈德·基特尔(Gerhard Kittel)和格哈德·弗里德里希(Gerhard Friedrich)扩大了克里默的开拓性著作,编著了多达十册的《新约神学词典》(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12]囊括了神学上每一个重要的名词、动词、介词,甚至许多在救恩历史中具有神学意义的旧约人名都包含其中;其基本构想是尽可能从旧约、七十士译本、古典文献、希腊文献、拉比经典,最后是新约本身的用法上,来研究每一个词。
基特尔认为,他的作品与约瑟夫·亨利·塞耶(Joseph Henry Thayer)、沃尔特·鲍尔(Walter Bauer)、乔治·阿博特·史密斯(George Abbott-Smith)等人所编的词典截然不同。他的作品关注的是“内在词义学”,以说明每个神学概念的独特性。弗里德里希接手了基特尔死后的研究工作,他不同意克里默的结论,即新约词汇具有现代一般希腊文所没有的特殊意思。弗里德里希的结论是:语言的任何新意,都应当归溯到它与耶稣基督的新关系。
如果圣经的用词真有新意,那会是什么?克里默采用了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关于“基督教的语言塑造能力”[13]的概念,以及理查德•罗特(Richard Rothe)关于“圣经使用圣灵的语言”的结论,来加以解释。然而,阿道夫·戴斯曼(Adolf Deissmann)从蒲草纸文献中发现,新约希腊文其实是口语化的、通用的,或现在一般所称的“通用希腊文”(Koine Greek)。[14]
但是,这结论可能又下得太强了。接续詹姆斯·霍普·莫尔顿(James Hope Moulton)完成《新约希腊文文法》(Grammar of New Testament Greek)第三册的奈杰尔·特纳(Nigel Turner)对于新约词汇新颖而独特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声称:“我们现在必须承认,不仅圣经的内涵是独特的,而且用来写作或翻译它们的语言也是独特的。”[15]
正当特纳说这话的同时,詹姆斯·巴尔也批评基特尔所著《新约神学词典》的基本方法。[16]巴尔对基特尔基本的批评是,词汇本身所提供的知识很有限,只有把词联结成句子,我们才开始了解特定的词对作者的特殊意义。
不但如此,巴尔特别不满(理当如此)他所谓的“不当的整体转变”,[17]亦即主张一个词在一段上下文中的语义价值,可以加在同一词在第二、第三处上下文中的语义价值上,而所有价值的总和就叫作在每处单独经文中的独特价值。巴尔用ἐκκλησία(教会)这个词的例子指出这种主张的错误。该词在不同的经文中有三个意思:(1)基督的身体;(2)神国最初的雏型;(3)基督的新妇。根据巴尔的看法,这些意思全都能适用于“教会”这个词,但在每处单独的经文中不能“全部”用作教会的意思。比如,马太福音16:18就是一例。
巴尔持定词汇的意思是在从句和句子(亦即一个词要看成是整个从句或句子的一部分)中找到的,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也不能批评得太过分,毕竟词汇确实有一个相当有限的指称范围,任何给定的上下文都只能在某些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对其加以修饰。[18]
我们还要知道,词汇书(以及圣经神学类的书籍)不能代替解经者自己对紧临的上下文的研究。如果他不先全盘查考紧临的上下文,就会很容易接受一个词可能有的所有的神学意思,而且在该词出现的每一处都读进所有的意思。因此,词汇书是供人参考的工具,但绝非懒惰解经者的拐杖。
那么,在参考这一类词汇书以前,个人如何进行词汇硏究呢?
首先,必须选择意义重要的词。一个词如果合乎下列条件之一,就算意义重要了:(a)它在所查的经文中起着关键作用;(b)它在上文中曾多次出现;(c)按照到目前为止所启示的,它在救赎历史中是重要。如果解经者是新手,他在这个过程中最好着重在条件(a)。随着解经者阅读范围的扩大,以及在解释圣经的许多卷书中经验的积累,他就可以更多地应用后面两个条件。同时,最好研读一两本圣经神学方面的书籍,培养对神学主题或词汇的感觉。
第二步是根据单词在“紧临的上下文”中的功能来对其下“定义”。一定要考虑同一个词在同一卷书中的其他用法,一定要“像阅读不断扩大的同心圆一样”继续阅读该卷书其他每一个大段。这样做的理由是作者对这个词的用法可能会有所发展,在同一卷书中可能有意思上的细微差别。
第三步是查考同时代其他作者对同一词的用法。这时我们需要用到更多的工具书来帮助我们学习。
第四步是硏究单词的词根或词源,这样的研究可获益良多。但是,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免得犯了“词根误判”(root allacy),因为字词的意思在其使用历史中常常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安东尼·西塞尔顿(Anthony C. Thiselton)曾用一些例子说明这个陷阱。比如,英文的nice(美好的)是由拉丁文nescius(无知的)演变而来;hussy(贱妇)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主妇”;又如good-bye(再见)原来是God be with you(神与你同在)的缩写。[19]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针对词源先入为主的偏见作了有力的辩驳。他将语言学比作国际象棋:重要的不是棋局的历史,而是棋局的当前局势。[20]
然而,语源学的考虑可能会有所帮助的一个地方是同音异义(homonymy)的情况:两个拼法相同、意思不同的词。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讲解者就要对这种研究十分小心——虽然弗朗西斯·布朗(Francis Brown)、塞缪尔·罗尔斯·德赖弗(Samuel Rolles Driver)和查尔斯·奥古斯塔斯·布里格斯(Charles A. Briggs)等学者似乎支持这种方法,按他们所认为的每个词的词根来对他们的词汇加以分类。事实是,经常没有人知道词源是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无妨,在几乎所有这些情况下,都不会叫解经过程的基本要素有所损失。
现在进到第五步,参考一个详尽的汇编,求取下列资料:
(1)该词在圣经中出现的总次数;
(2)出现最频繁的时期;
(3)出现特别多的一段经文——这很可能就是对该词有最完备教导之处;
(4)在我们所查的经文之前用到该词同样用法的经文。
这里的原则跟我们谈“(前述)经卷类比”时所主张的相同。晚于我们所查的经文只能拿来比较,此外别无用处。求取项(4)的目的,是要确定我们在研究中没有忽略相关的资料。
我们还要再提醒一件事,就是解经者在硏究一个词时,必须注重从上下文中得到的意思,而不是它在语义所有可能范围的意思。我们把一些对解经者有用的索引列在本章后面的书目中,以供参考。[21]
第六步,对于有经验的解经者来说,就是参考各种同语系的语言(cognate languages),以找到额外(包括对比)的用法,尤其是那些在圣经中很少出现(甚至只出现一次)的词时,更需要如此。以希伯来文来说,人们可以查阅乌加里特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巴比伦文和亚述文)、阿拉伯文、亚兰文、埃及象形文字的语法和词典,有时甚至要查阅科普特人(Coptic)的文字。[22]
这里我们应当提到埃德温·哈奇(Edwin Hatch)和亨利·雷德帕思(Henry A. Redpath)所编的《七十士译本经文汇编》(Concordance to the Septuagint),[23]因为新约希腊文的用法常常源自公元3世纪的旧约希腊文译本。此外,通用希腊文(Koine Greek)在它的词义范围中也有部分与蒲草纸文献上的通俗用法相同。这方面能够给作词义研究的学生带来丰富内容和许多有益见解,有戴斯曼的《来自古代东方的亮光》(Light from the Ancient East)和莫尔顿与乔治·米利根(G. Milligan)的《希腊文圣经字汇》(Vocabulary of the Greek Testament)。[24]比如,保罗答应腓利门要偿还阿尼西母从他那里拿的所有东西(18节),戴斯曼引用有同样措辞(“归在我的账上”)的蒲草纸文献,说明保罗既然亲笔这样写(19节),腓利门就可以像我们今天持有支票一样用它,要求保罗对阿尼西母的债务担负经济上的责任。虽然这个例子只在文化层面上发挥作用,但其在神学层面上也有相近的例子。
我们现在应该准备好检查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且与别人所做的进行比较。为了方便学生使用,我们把一些著名的词汇书列在下面的参考书目中。
三、参考书目
1. 旧约汇编
Lisowsky, Gerhard, and Rost, Leonhard. Konkordanz zum hebräischen Alten Testament. Stuttgart: Württembergische Bibelanstalt, 1958.
Mandelkern, Salomon. Concordance on the Bible. Edited by Chaim Mordecai Brechcr. 2 vols. New York: Shulsinger Brothers, 1955.
Wigram, George V., ed. The Englishman’s Hebrew and Chaldee Concordance of the Old Testament. 5th ed. London: Bagster, 1890. Reprin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2.
2. 新约汇编
Moulton, W. F., and Geden, A. S. A Concordance to the Greek Testament According to the Texts of Westcott and Hort, Tischendorf and the English Revisers. Revised by Η. K. Moulton. 5th ed. Edinburgh: Clark, 1978.
Schmoller, Alfred. Handkonkordanz zum griechischen Neuen Testament. 14th ed. Stuttgart: Württembergische Bibelanstalt, 1968.
Wigram, George V., ed. The Englishman’s Greek Concordance of the New Testament. 9th ed. London: Bagster, 1903. Reprin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0.
3. 旧约词汇书
Bauer, Johannes B., ed. Sacramentum verbi: An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Theology. 3 vols.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0.
Botterweck, G. Johannes, and Ringgren, Helmer, eds.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Translated by John T. Willis and David E. Green. 4 vols. to dat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4-.
Girdlestone, Robert Baker. Synonyms of the Old Testament: Their Bearing on Christian Doctrine. 2d ed. London: Nisbet, 1897. Repri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48.
Harris, R. Laird; Archer, Gleason L., Jr.; and Waltke, Bruce K., eds. A 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2 vols. Chicago: Moody, 1980.
Wilson, William. The Bible Student’s Guide to the Mor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by Reference to the Original Hebrew. 2d ed. London: Macmillan, 1870. Reprint. Old Testament Word Studies. Grand Rapids: Kregel, 1978.
4. 新约词汇书
Brown, Colin, ed.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3 vol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5-1978.
Kittel, Gerhard, and Friedrich, Gerhard, eds.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eoffrey W. Bromiley. 10 vol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4-1976.
Robertson, A. T. Word Pictures in the New Testament. 6 vols. New York: Smith, 1930-1933. Reprint. Nashville: Broadman, 1943.
Trench, Richard Chenevix. Synonyms of the New Testament. 9th ed. London: Macmillan, 1880. Reprint. Grand Rapids: Herdmans, 1948.
Vincent, Marvin R. Word Studies in the New Testament. 4 vols. New York: Scribner, 1887-1900. Repri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46.
Vine, W. E.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Westwood, N.J.: Revell 1956.
[1] Origen, De principiis, 4、26。
[2] John F. Johnson, “Analogia Fidei as Hermeneutical Principle,” 253页。
[3] Herbert Marsh, A Course of Lectures, 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and Systematic Arrangement of the Several Bra ehes of Divinity…,共七部 (Boston : Cummings and Hilliard, 1815), 3 : 16。
[4]引用在Daniel P. Fuller, “Biblical Theology and the Analogy of Faith,” 收录于Unity and Diversity in New Testament Theology: Essays in Honor of George E, Ladd,编者Rohert A. Guelich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8) 198页。Fuller对这问题的讨论,对改教家在释经上一些困难的地方有卓越的分析。
[5] John Bright, The Authority of the Old Testament,143,170页。另见Walter C. Kaiser, Jr., Toward an Old Testament Theolog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8),14-19页。
[6] Kaiser, Toward an Old Testament Theology,32-35页。
[7]更清楚、深入的讨论,同上,25-32页。
[8]见我对“应许”的详细讲论,同上,1-69页。
[9]这些书的介绍和综览,见James P. Martin, “Theological Wordbooks: Tools for the Preachers,” Interpretation 18 (1964) : 304-328; Xavier Léon-Dufour, “Introduction,”于Dictionary of Biblical Theology中,编者Xavier Léon-Dufour,译者P. Joseph Cahill (New York: Desclee, 1967),XV-XXi页; Gerhard Friedrich, “Pre-history of the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刊于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编者Gerhard Kittel和Gerhard Friedrich,编译者Geoffrey W. Bromiley,共十册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4-1976), 10: 613-661;并James Barr, The Semantics of Biblical Language (New York: Oxford, 1961)。
[10] Hermann Cremer, Biblico-Theological Lexicon of New T'estoment Greek,第三版,译者William Urwick (Edinburgh: Clark, 1883)。
[11]这工作的开展,迟至G. W. H. Lampe, A Patristic Greek Lexicon,共五册 (Oxford: Clarendon, 1961-1968)。
[12]详细资料见注9。
[13]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Hermeneutic und Kritik mit besonderer Beziehung auf das Neue Testament,编者Friedrich Lücke, Sammtliche Werke, Erste Abteilung zur Theologie, 7 (Berlin: Reimer, 1838)。引用于Martin, “Theological Wordbooks,” 305页。
[14] AdoIf Deissmann, Light from the Ancient East:The New Testament Illustrated by Recently Discovered Texts of the Graeco-Roman World,修订译者Lionel R. M. Strachan (New York: Doran, 1927; Grand Rapids: Baker, 1978再版)。另参James Hope Moulton和George Milligan, The Vocabulary of the Greek Testament, Illustrated from the Papyri and Other Non-Literary Sourc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30;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49再版)。
[15] Nigel Turner,在James Hope Moulton, W. F. Howard和Nigel Turner, A Grammar of New Testament Greek,共四册 (Edinburgh. Clark, 1906-1976) ,3 : 9。引用于Martin, “Theological Wordbooks,” 308页。
[16] James Barr, The Semantics of Biblical Language (New York: Oxford, 1961)。
[17]同上,218页。
[18]这一点得自Gustaf Stern, Meaning and Change of Meaning, with Speci l Reference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Indiana Universit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Linguis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31),85页;以及Stephen Ullmann, The Principles of Semantics;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Meaning,第二版 (Oxford: Blackwell, 1959) 218页。这些出处系引自Anthony C. Thiselton,” Semantics and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收录于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Essays on Principles and Methods,编者I. Howard Marshall,75-104页。西塞尔顿的文章颇具权威性。
[19]引用于Thiselton, “Sense and Nonsense,” 17页。参Stanley Toussaint, “A Method of Making a New Testament Word Study,” Bibliotheca Sacr 120 (1963) : 35-41;和Ernest D. Burton, “The Stud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Student 12 (1891) : 136页以下。
[20]引用于Thiselton, “Sense and Nonsense,” 17页。参Stanley Toussaint, “A Method of Making a New Testament Word Study,” Bibliotheca Sacr 120 (1963) : 35-41;和Ernest D. Burton, “The Stud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Student 12 (1891) : 136页以下。
[21]关于七十士译本、武加大译本,和英译本的经文汇编,其进一步的讨论参考Frederick W. Danker, Multipurpose Tools for Bible Study,第二版 (St. Louis: Concordia, 1966),1-17页。
[22]其中部分基本工具书的书目列在前书,106-111页。
[23] Edwin Hatch和Henry A. Redpath, A Concordance to the Septuagint and the Other Greek Versions of the Old Testament,共三册 (Oxford: Clarendon, 1897)。
[24] Adolf Deissmann, Light from the Ancient East: The New Testament Illustrated by Recently Discovered Texts of the Graeco-Roman World,修定版译者Lionel R. M. Strachan (New York: Doran, 1927; Grand Rapids: Baker, 1978再版); James Hope Moulton和George Milligan, The Vocabulary of the Greek Testament, Illustrated from the Papyri and Other Non-Literary Sources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30;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49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