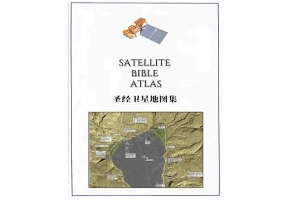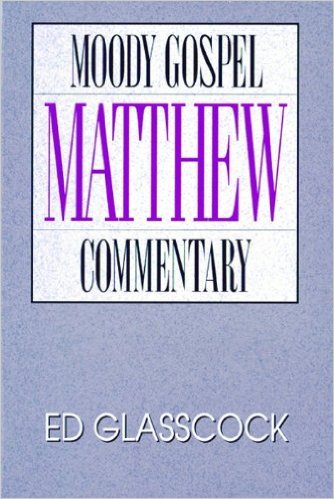第五章 字面分析
文字和习语是所有语言最基本的语义单元。作者用文字和习语的组合来表达他心中独特的思想。
一个词在特定情况下的特定意思,通常是由它所处的文法结构明确规定的。现代语言学家称这个为语义的“句法符号”(syntactic sign)。[1]所以,同一个stone,可能在一个句子中作名词(石头),但在另一句中则可以作为动词(用石头打)。在这些例子中,一个词的意思是由文法表达,也就是由句法结构来决定。
另有一些情况,一个词的意思受它与上下文用词的相互作用所影响,这称为意思的“语义符号”(semotactic sign)。这里的关键因素不是这个词的文法用法,而是该词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中出人意料的应用,从而传达出新的意思。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和查尔斯·泰伯(Charles R. Taber)曾举例说明周边影响(semotaxis)在表达上的影响:“一‘串’(hand)香蕉;‘主持’(chair)会议;藤蔓从门上‘爬’(runs)到门外。”
一个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能有许多种用法,这可以用“板”(board)这个词来说明。[2]“板”可以是一片锯开的木材,也可以是放食物的桌子(a festive board),在上面吃饭的人往往必须支费餐(pay their board);但是当人们聚在桌边谈生意时,他们就成了董事会(a board of trustees);人们踩着踏板登船(step on board),甚至可能从甲板落入海中(fall over board)
另外“快”字也一样:他必须切得很“快”,因为客人“快”来了,但他发现他的菜刀不够“快”,因此他大感不“快”;有些人跑得快(fast),而自信的人快速(fast)成交;有些人把船牢牢地(fast)固定住,而另一些人则在特殊的日子里禁食(fast)。
显然,词语像人一样,是物以类聚的。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作者所用的相邻词(即,在一起的一组词),在我们确定作者自己用词的意思时,他是最后的决断者。
一、作者原意
但作为解经者,我们如何有把握地肯定作者自己使用这些词的意思呢?
1. 一些通用的原则
这里有一些通用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词汇。
(1)词的意思,首先是由作者写这些词时的风俗习惯和一般用法所决定的,没有一个聪明的作者会故意偏离这种“习惯用法”(usus loquendi),也就是,在某一特定时代当时流行的用法——除非他有很好的理由说明可以这样做,或者给出一些明确的解释表明他已经这么做了。
(2)在赋予一个词的意思时,解经者最可靠的基础是作者本人对该词的定义。比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5:14将“完全”定义为:“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
(3)一个词的意思,可能在相邻的所有格短语、同位短语或别的定义性描述中有所解释,这种情形有时称为“注释”(glossing)。以弗所书2:1是个例子,当保罗宣称“你们死了”时,他立刻加上了“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注解。有时作者会用解释的方式来附加说明(editorial comment)。比如,在约翰福音2:19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在21节解释道:“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另外,在约翰福音7:37-38中,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知道这对没有听过耶稣讲道的人会造成困扰,所以他在39节加以解释:“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4)正如我们讨论句法符号时已经看到的的,一个词的文法结构可能是其意思的另一个线索。比如,“牧”(shepherd)可以用作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此外,主语或谓语会限制或定义一个词,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有不同的意思。米尔顿·特里(Milton S. Terry)曾经指出,马太福音5:13的μωραίνω意思是“失味”,因为它与主语“盐”相关;但是当它用来指人时,就如罗马书1:22,它就指“成了愚拙”(参林前1:20“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3]
(5)有些词的意思可能是由上下文的对照或对比来断定的。有些段落主要就是用对比法展开的。在哥林多后书3:6-14中,“字句”(γράμμα,不是γραφή)与“灵”相对;属死的职事与属灵的职事相对。而且罗马书8:5-8中保罗将“随从肉体的人”与“随从灵的人”对比。
(6)在旧约诗歌中,决定词义最好的方法往往是借助希伯来文的“平行体”。希伯来诗歌的特色不在于A和B两行之间在声韵上的押韵,而是通常使用同义平行体(Synonymous Parallelism)或对偶平行体(Antithetic Parallelism)。在“同义平行体”中,与第一句相同或类似的思想在第二句中以略微不同的方式重复。“对偶平行体”则将与第一句思想相反或相对的思想在第二句中呈现,形成诗歌中的对偶。这个主题我们会在单独的一章中更明确地陈述。
(7)仔细比较“平行段落”(Parallel Passages)也可能有助于解经。作者可能在他作品的另一处又回到对同一个词的讨论(“字面平行段落”〔verbal parallel passage〕),或者至少是对同一主题事件的讨论(“专题平行段落”〔topical parallel passage〕);别的作者也有可能提到同样的词或主题。虽然是一个不太确定的过程,但在这种情况下,平行段落仍然可以拿来进行比较。如果经过仔细硏究,发现该词或主题确实是相同的,或非常相似,那么在一段经文中已经清楚的词句,就可以用来阐明另一段经文中晦涩不明的词句。(关于这方法应用上的提醒,参本章“平行段落”标题下的内容及第六章“前述经卷类比”标题下的内容。)
2. 一个老旧的谬论
回过头来,我们又要面对那个老旧的谬论,即,主张圣经中的每个字词都有几层意思,而这些意思连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说到支持这种经文多层理论的学者,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甚至连鼎鼎大名的布鲁克·韦斯科特(Brooke Foss Westcott)也相信这种错误的理论。他说:“我当然不该坚持认为,像在希伯来书这样的书中,作者能够完全理解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全部意思。……没有人能把诗歌语句中的教训限制在作者头脑中所想的那些;更不能认为,一个受默示、要传神信息给各时代的人,能够明白启示给众人的真理的全部。”[4]
直到现在,不断有人持同样的看法。在天主教徒中,没有人比雷蒙德·布朗(Raymond E. Brown)更热衷于这个解经问题了,每一个认真的解经者都不怀疑他的坦诚,他说:“让我们用‘更充分的意思’(sensus plenior)来形容他(作者)所写的经文的意思,按照一般解经的规则,这不在作者明确的意识或意图之内;但按照另外的标准,我们可以断定这是神有意要说的。”[5]
但是,对当代的圣经读者来说,最后是谁来决定他们应该遵从的规范和权威呢?如果情况变得太糟糕,天主教学者有法规、传统和大公教会可以依靠。而新教的学者应该用什么来取代这些呢?
诺贝特·洛芬克(Norbert Lohfink)是耶稣会(Jesuit scholar)的一位学者,他阐述了人一旦宣布一句经文是自由的、独立于作者的,那么找出规范和权威将是何等令人头痛的事。起初,洛芬克推想,默示现在必须限制在圣经经文的“最后编辑者”表达的意思上;然而,由于历史批判学(historical criticism)和文学批判学(literary criticism)的影响,他最终将自己的立场转向了整个圣经的教导。因此,洛芬克宣称,在解经学建立的圣经陈述的原始意义之上、背后和之外,一定有其他的意思,那就是整本圣经的教训。这意思是由另一个解经方法得知的,不能用我们平常以作者的词句找出其意的方法得知。[6]
但是,有哪些圣经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所教导的内容,不同样是在个别卷书或个别段落的文法和句法中教导的呢?洛芬克被自己的逻辑所困,就像一些福音派学者所做的(只是理由完全不同而已,至少在这一代是这样),转向一种超越原作者意识的“更充足的意思”(sensus plenior)或“更充分的意思”(fuller sense)。
这个“更充足的意思”(sensus plenior)理论使受默示的作者成为解经过程的次要因素,有时甚至是一种麻烦;而神,作为首要的作者,被认为在人类作者原有意图之外直接向解释者提供许多额外的意思。根据这个观点,虽然硏究的是同一个词,但解经者挖掘“更充足的意思”所得的收获是正常的解经原则无法做到的。
布鲁斯·沃特(Bruce Vawter)在一个卓越的分析之中指出,这个理论是误用了旧的经院哲学类比(the old scholastic analogy)的“工具因果”(instrumental causality)。他说:“……如果这个更深层、更充分的意思是神留给自己的,而且完全不在作者的思考范围之内,那么我们难道不是在假定圣经上的话不受人类作者的意念和判断力所控制……因此并非真正由‘人’写成?如果真如经院哲学家所定义的,圣经是神与人的‘合著’(conscriptio),那么当我们接受‘更充足的意思’时,岂不是拿走了这个所谓‘经文意思’的一个基本要素,以至于在逻辑上根本不能称之为经文意思?”[7]
沃特断然否定“更充足的意思”就是经文意思,无论人怎么看待这更深层的意思,它都不是“圣经意义上的”意思。圣经上的话可能像是触发因素,促进个人接受天上各样启示,或类似的其他情形;但没有任何已知的解经的方法可以证明,任何一段文字都能产生“更充分的意思”。根据定义,这一点是被承认的。所谓通过“更充分的意思”得到的“神的意思”,并不能从圣经中找出。
约瑟夫·科庞(Joseph Coppens)发现了使用“更充分的意思”方法的主要困难:如果它在新约和旧约之间开辟了信仰和神学和谐的新视野,为什么事实上这些“更充分的意思”不被这些虔敬的作者察觉呢?难道他们不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作的?科庞归纳后认为,只有在使徒和先知写得比他们所了解的“更好”时,“更充分的意思”才可能存在;而这一事实,应该是后人通过履行真道、熟读经文并且系统地硏究圣经的整体概念之后,才能发现。[8]
但我们要抗议,如果作者“写得比他们所了解的更好”,启示就不再是披露或揭示。我们从哪里来证明这一点呢?彼得前书1:10-12绝不能用来证明先知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甚至不知道他们所写的。当然,他们希望启示包含了“时间”因素,但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是神在旧约中所启示的救恩。他们知道这与基督的死和得胜有关,这对即将进入教会的信徒也有影响(12节)。
同时,我们所理解的也不会比作者所理解的“更好”,除非所谓的“更好”是指我们能完成并详述圣经经文所涉及的主题和主题的未完成部分,或是指我们可以澄清一些作者所用的某些假设或指导原则,而无需刻意探讨或明确说明这些假设或原则。[9]
有一种更圆滑的说法避免了以上所提的困难,就如韦斯科特所示意的,主张语言本身即有生命,与使用者无关。这种观点的极端形式是,它宣称一部文学作品完全独立于其作者,必须脱离作者的意图和写作的背景来理解。
戴维·克莱恩斯(David J.A. Clines)曾提出一个更完善的说法:
一旦我们认定经文不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是有自己的生命,就有可能谈论经文的意思,就好像它只有一个意思……〔但〕认为意思不在于经文本身,而是在于经文对读者的意义……因此原作者的意思,也就是平常所说经文的意思,就绝不是经文理当拥有(或更确切地说是“创造”)的唯一意思。我们甚至不能肯定一段文字(或任何艺术作品)“最初”——无论是什么——对作者来说意味着一件事,也只是一件事;甚至连作者心里也可能对它赋予多重的意思……〔因此〕这不是完全的对与错的问题,而是看有多少恰当的解释……取决于文学作品在新情形下的表达是否清晰。[10]
早期教父和中世纪教会中曾有人主张经文有四重(或更多)意思,以上的说法岂不正暗暗地申言复古吗?安提阿学派(Antiochian School)所倡导的经文单一意思(即作者原意),从方法论上、历史上和神学上,都远比寓意化的亚历山大学派(Alexandrian School of allegorizing)好得多。
不管是采用语言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法,主张语言即使脱离了其使用者“人”,也有其本身的能力和意思;还是采用“怀特海的过程—形式”(Whiteheadian process-form)来了解语言,主张语言应该重在诱发读者的情感,[11]其次才是经由逻辑关系表达事实。无论我们赞成哪一方,最根本的问题仍旧是:哪一个意思?哪一种用法?经文的哪一个吸引人的、个人感兴趣的特征是有效的,因而可以成为我们这一代的规范,并具有神圣的权威?
这些问题粉碎了一些不假思辨地畅饮现代主义之解经者所持的一切,迫使那些解经者面对现代主义想要逃避的问题。所有的解经者都必须承认,只有那些与作者使用的语言符号所表达的经文意思相一致的提议,才能作为对规范性做出任何决定的依据。巴里·伍德布里奇(Barry A. Woodbridge)抱怨说,这种主张是一种倒退,无异于“崇拜过去”。[12]
我们不能同意。如果我们不是正好用这种释经法(Hermeneutic),我们就根本不会准确地听到对我们立场的任何抱怨。我一直很诧异,攻击“单一意思”理论(也就是回到作者原意的主张)的解经者,却要求所有阅读他们的论文和著作的读者明白他们的意思是单一的,并且必须按字面来理解。但是,虽然我们允许他们有此特权,他们却反过来希望我们按照他们提倡的那样,按照新的多层意思理论来解释所有其他的文本。
所有成功的解经者都必须面对“意图”的问题。我们深信,任何给定单词的意思(包括它的文字和上下文)都分别包含在作者的“单一意图”之中。如果这个意图在别处可以找到,并且是用与通常的解经法不同的方法得出,那么尚没有人能够说明这个过程是怎样运作的,或者我们如何验证这个过程所得出的附加意思。
但我们还要逼近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一些比较困难的方面,是什么构成了作者的意向性,从而构成了经文的词义?[13]在面对意图的问题时,我们应不应该考虑一些事,像古代世界观、受文化制约的言论、伪科学分类的考量、不严谨的表达方式、数字的精确度等?是否有可能区分作者最首要的意图,即在信仰和实践中传达神圣真理的意图,与他心中可能想到的其他意图,如单单要说明愚昧人在心里说了什么的意图?我们现在必须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
二、文化词语
在对风俗、文化和圣经准则的讨论中,常常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倾向于将圣经中的所有特点,包括文化习俗和措辞,与圣经的其他教训一同当作准则来教导;另一个极端则倾向于抓住圣经中任何可疑的文化制约的描述,就以此为借口,把与该经文相联的教导降低为不过是对现已不复存在的情形的报道。这两个进路,都是负责任的圣经解经中当禁止的例子。
可以肯定的是,圣经中有许多与文化有关的细节,包括饮食、衣着、礼仪、社会、经济、政治和风俗等。当这些事物只是传达其所含真理的文化载体,那么解经者的任务就是明确的。在这些情况下,,解经者必须认清经文中的文化状况,同时不让其中包含的任何一点神圣启示受损。
关于这一点,“说”往往比“做”要容易多了。但这个困难不能让我们偏离我们的任务。彼得解释保罗书信时也承认有困难(彼后3:15-16“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信中有些难明白的”),但他承认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麦克唐纳(H. D. McDonald)提醒我们,cultura一词的原始意思是“犁田以备种植谷物”,但是cultura一词的现代意思扩大为“构成各人所生存之社会环境的舆论氛围,以及思想和价值的体系”。[14]
神在圣经中的启示有区别地使用了作者当时可能得到的文化材料。因此,他们很高兴地借用、改造并重新应用了那些文化材料,诸如迦南的大海兽(诗74:13以下)、神话中的拉哈伯龙(伯26:12-13)、赫人的附属国条约(申命记中的契约结构即为此形式),以及异教的“神之子”称号,作为对专制、不负责的地方官的称谓(创6:1-4)。
但是同样明确的是,圣经拒绝落入某些可能因此减少信息内容的文化局限中。一个好例子就是,圣经不接受“三层宇宙观”。在圣经的某些诗歌部分,我们看到哥白尼以前的宇宙模型,即天是固体的圆顶,地是平的,地底下是深渊(圆顶有柱子撑着,还有透进雨和星的裂缝),这要么是解经者的编造,要么就是没有看出比喻语言的使用。[15]
因此,解经者需要问,在什么时候采用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是恰当的。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指出圣经中的段落,一些圣经译本偏重“动力相当”(dynamic equivalent),而另一些译本则偏重“形式对应”(formal correpondence),例如,根据《威洛代尔报告》(Willowdale Report),以罗马书1:17为例,[16]英文RSV(Revised Standard Version)根据希腊原文逐字逐句翻译,“因为在这福音里,神的义是因信而显明出来的”(中文直译);而TEV(Today’s English Version)则放弃了严格的“形式对应”,通过“动力相当”捕捉到保罗的原意,“因为福音揭示了神如何使人与他自己和好:这从头到尾都是透过信心”(中文直译)。
然而,有些圣经的形式应该保存下来,因为它们直接与其中包含的真理有关。例如,十字架、神的羔羊、杯。有一个更困难的决定必须做出,那就是关于“血”的概念,这个词在旧约献祭制度和主耶稣自己的献祭中都可以找到。这里的问题是,接触到经文的当地文化(如笔者的西方文化)对“基督的血”的表达可能会有错误的领会。西方人听到会立刻想到医院,把这个词和通过输血赋予生命联系起来。但是,圣经的意思刚好相反,是指“倾倒生命以至于死”说的。在这个例子中,真理明显与旧约献祭的文化形式有直接关联,也许值得花功夫去解释文化形式,而不是试图用意译法保存真理,把“血”翻译成“牺牲生命从而使他人得生”。
我们在此试着归纳出解经时考虑文化背景所应当遵照的几个原则。
(1)那些反映特定时代、文化和外在形式的词意应当被分辨出来。但要记得,不是所有属于文化的词意都不具有永恒的原则和教义——即使是文化“形式”的一个词意,仍可能保留着它对现在的意义。如何处理这些词意,最后的裁定者必须是作者和上下文。
(2)要区别文化的形式与内容[17],可以用下列几点来区分永恒的真理与暂时、偶然的事物。
A. 解经者必须确定,作者何时只是在“描述”某些事物,并为他的永恒原则设定背景,何时是在为当时及之后“指示”某些事物。例如,早期教会的治理机构及其任职者,是被赋予某些应当严格遵行的行政命令,还是迹象表明这些通知中的一部分或者全部仅是“描述”而已?
B. 解经者必须用当时文化的例证来判断这段经文是否在阐明某一神学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该例证是否在以后继续出现,原则依然不变。例如,现在教会虽然不再要求有钱的会友坐下位,好让穷人高位的事,但谦卑的原则仍然存在(雅2:1-7)。
C. 解经者应该自问:同样的神学原则,今天是否仍然可以通过一个类似却在文化上不同的媒介,得到同样充分的承认?例如,作为一种问候的方式,握手在西方文化中的作用可能相当于东方文化的圣洁亲吻之举(林前16:20);仆人式的态度可能相当于洗脚的风俗(约13:12-16)。
D. 当圣经本身,在后来的历史情形下,对同一件事的处理有不同的惯常作法或处罚时,我们仍能需要从中学习一些东西。例如,关于乱伦的教导,在新约仍然提到,却不按旧约规定的方式(处死)来处理,而是吩咐要赶出教会,直到他公开悔改为止。
(3)一个常例或文化上的命令,如果说明“理由”,并且该理由基于神不变的本性,那么这个命令或常例就是针对各个时代的所有信徒说的。创世记9:6要求政府对所有犯下一级谋杀罪的人处以死刑的理由,“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既然男人、女人继续照神的形像被造,这种惩罚就会被使用——不是作为对受害者哀伤家属的补偿,不是作为对其他潜在罪犯者的警告,不是作为对受到威胁的社会焦虑的缓解,而是因为人是照神的形像造的。在此,我们联想到利未记中一再吩咐的“你们要圣洁”,然后又说:“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4)有时某些命令可能会附加“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的原则。虽然命令是基于神的本性,本不该有例外,但有时这些律法的应用会根据情况而改变,只有在神的话指明特殊的时间或状况时,这些律法才有效。例如,神吩咐说,除了祭司,没有人能吃“陈设饼”(利24:5-9),但对大卫这批饥饿的人来说,就有权宜的措施(撒上21:1-6),甚至耶稣还引用它作为在安息日应付急切需要的例证(太12:1-5;可2:23-25;路6:1-4)。起先看来是不能有例外,但实际上,这要有“其他条件不变”的原则来配合它。然而要注意,对于这个原则的应用一定要小心,并要严加限制。[18]
(5)每当解经者碰到可能是单纯文化方面的事物时,一定要特别注意“上下文”。新约中最需要考虑上下文的例子,莫过于论到女性权柄的范围问题。
A. 如果在讨论区域性或文化性问题时穿插了明显的教义或神学阐述,那么即使该风俗的形式不再延续,其教义仍旧不变。例如,哥林多前书11:3宣称“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个关于妇女的段落很快带来了各种情感反应,因为它对今天的教会仍存有永恒的价值。不止这一节,第7-9节、第11-12节和第16节都有显著的教导和神学性质,因此,关于这个段落的任何看法,都必须体现对其中包含的神学教导的尊重。
B. 如果一段经文的上下文反对这段经文中所说的风俗或常例,我们就能肯定这个风俗或常例不是信徒的准则。我们之前已经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解答了一连串信徒写信问的问题,他有时用περὶ δὲ(论到)为开头(林前8:1,12:1,16:1),有时也不用这个开头,而是直接引用信中的话。比如,在哥林多前书6:12和10:23中,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是他又立刻反对这个论点说“但不都有益处”;同样,在哥林多前书14:34-35中,保罗又引用哥林多人的来信。哥林多人一定引用了拉比律法,要求女人除非在家,就不要讲话,保罗的答复几乎是无情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原文μόνους指仅有的一群男人,不是阴性的μόνας)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就该知道(以上的事)。”我们把这一处和哥林多前书11:5合起来看,保罗在那一处是允许女人公开讲道的(如林前14:3的定义——予人鼓励和盼望,使人在信仰上被建立)。而且在哥林多前书14:31中,学道理得劝勉的“众人”与作先知讲道的“都”是同一个词(all),很明显,该经文是反对(而非教导)一种文化习俗。[19]
C. 如果邻近的段落除了解释性的从句或句子外没有别的限定,那么要做出断定就更困难了。提摩太前书2:8-15就属于这一类。保罗说完男女同样可以公开祷告(9节的开头有“同样”一词,和合本未译出)之后,他吩咐“女人要沉静学道”(11节),又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12节)。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后面的γάρ(因为)。解经者必须用心思考,以确定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理由决定前面的吩咐是永远的,还是暂时性的。我们是在讨论创造的次序,还是在讨论提摩太所在的教会中,男人像亚当,有女人所没有的教导,女人则像夏娃,更容易受到引诱和诡诈的伤害,因此才需要用这些话来吩咐呢?无论一个人的答案如何,都说明上下文的解释(“因为”是解释不许女人讲道的理由)是判断什么是永久的、什么是暂时的关键。
D. 最后,我们要密切注意圣经在上下文中对该词汇所下的“定义”。这些词汇常常很容易被现代价值观所取代。例如,有些解经家想为同性恋建立一个圣经案例,就将保罗的用词“本性的”(φυσικὴν,罗1:26、27)加以解释,以为性关系是天性使然,来自个人的生物本性、早年的经验和生活的导向。但是保罗所用的“本性”是整体的、道德的,而不是说到个人(堕落的)天性。[20]这种对经文的改动出自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和现代意识形态(modern ideologies),不是圣经本身的意思。
我们要说的是,圣经中一些伦理的诫命和一般的教训,其历史或文化方面的本质不应该使解释者感到困扰。特例无非是一般原则的特别应用而已,因此解经者不可(在相当数量的例子中,不该)把圣经中所有的讲论或描述加以普世化或“原则化”(当然,许多的确需要当作不变的真理)。
如果下判断,只能基于作者本人所提供的上下文线索。[21]对经文的解释因文化和社会不同而异,这种看法是错误的。[22]这种相对主义与圣经作者对经文的至高宣称是不可能调和的,经文不能因为现代的技术而改变。
三、借喻与比喻性词语
在所有的语言中,单词的用法都是有规律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单词的一般状况叫作文法规则(laws of grammar)。然而,为了增加一些词的力量和塑造形象的能力,作者有时候会有意识地故意不照文法规则而用词,语言的新形式因此产生。这种偏离词的字面或原有意思的解释,希腊人叫作“借喻”(Trope,源自希腊文τρόπος,意思是“转换”),罗马人叫作“比喻”(figura,“形像”或“图样”;或fingere,“形成”)。希腊人把这些新形式归纳出一门科学,并为两百多种的比喻法命名。罗马人承继了这门科学,但到了中世纪时期,这门学科便几乎失传了。
比喻法故意偏离自然或固定的文法和句法的规则,不可能仅仅是文法错误,也不可能是由于无知或大意造成的;相反,它是为了特别的目的“合理地偏离”平常的用法。所以它们的数量不多,可以根据已知的例子来描述、命名和定义。[23]
我们如何确定什么时候是比喻性的?解经者可以依照以下各点来判断。
A. 若以自然的方式解释句子,主语和谓语之间是否不相配?比如,“神是我们的磐石”一语,有生命的主语(神)被认为是无生命的谓语(磐石)。
B. 一个生动的词后面,是否紧接着该词的定义(因而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例如,“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C. 若按照字面解释,是否显得荒谬,甚至与其他的启示或创造的正常规律矛盾?例如,“大山拍手”(当然,这不包括超自然和神迹的介入)。
D. 在文章的这一点上,有理由使用比喻吗?例如,此处是否需要一个更强烈的感觉、一种戏剧性的强调、一些辅助记忆的安排来加强信息?
E. 这个比喻说法的例子,有没有在别处出现过?
语言的问题是,普通人只有两万到四万个词可以用来识别、描述和讨论他的个人世界中成千上万个需要识别的组成部分、经历和事件。由于缺乏语言单元,我们就开始说我们感到“忧郁”(blue),桌子有四个“腿”(编者注:这里的英文是blue和legs,不容易看出词性的改变)。
比喻法不但传达了一个意思,还为读者或听者描绘出一幅图画。当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还容易”时,他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故意作夸大的描述。但是,把一匹骆驼牵过针眼的有趣景象对于任何一个愿意停下来思考的人都是有效的。
有一本比喻法方面的最佳参考书至今仍未过时,就是布林格(E. W. Bullinger)所著的《圣经所用的比喻说法》(Figures of Speech Used in the Bible, Grand Rapids: Baker, 1968 reprint)。布林格将两百多种比喻说法按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名字加以分类、定义,并举出圣经应用的大约八千个例子!这本书应该在每一个解经者的书架上,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字典、文法书并列。
在此,有必要给出一些处理这些比喻的建议。
(1)正确判断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是比较、外添、关联,还是相对?
A. 比较性的比喻(Figures of Comparison)
明喻(Simile)——两件事物之间“明显”或“正式”的比较。A像B,“他要像一棵树”(诗1:3)。
暗喻(Metaphor)——暗示或未明说的比喻;一件事物引申为另一件事物,不直接说“A像B”,而作“暗示性”或“不明显的”比较,即A是B,“告诉那个狐狸”(路13:32)。
B. 外添性的比喻(Figures of Addition)
赘言(Pleonasm)——为在听者的心中达到特定效果而用不必要的更多文字作多余的表达。“酒政却不记念……竟忘了”(创40:23)。
谐音(Paronomasia)——重复发音相近、意思未必相同的字。“凡事常常充足”(παντὶ πάντοτε πᾶσαν,林后9:8)。
夸张(Hyperbole)——故意夸张以加强所说的效果。“我因唉哼而困乏……流泪把床榻漂起”(诗6:6)。
重名(Hendiadys)——用两个词指一件事物。“硫磺与火”(即焚烧的硫磺,创19:24)。
C. 关联性的比喻(Figures of Relation)
举隅(Synecdoche)——用一个有关联的概念取代另一个概念,作为以一概全或以全示一。“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路2:1)。
换喻(Metonymy)——用一个相关的名词取代另一个名词。“他们有摩西和先知”(指这些人所写的书,路16:29)。
D. 对比性的比喻(Figures of Contrast)
反语(Irony)——使用与字面意思相反的词。“那人已经成为我们中的一个”(创3:22,直译)。
间接肯定(Litotes)——贬抑一件事物以强化另一件。“我诚然是灰尘”(指亚伯拉罕,以显出神的伟大;创18:27)。
婉词(Euphemism)——将尖锐、不易接受或粗鲁的词语换成较温和、可接受、庄重的表达方式。“他在遮盖他的腿”(士3:24;撒上24:3,直译)。
(2)寻找用同样比喻的段落(最好是同一位作者)。比较这个比喻在几个例子中的用法和理由。
(3)参考几种有关比喻的著作,如布林格的这本书或约翰·本格尔(John Albert Bengel’s)的名著《新约之晷》(New Testament,这本书索引中定义了一百种比喻)。
比喻对于翻译者可能是愉悦的,但我们绝不能为了逃避困难就认定一段经文为比喻。两手一摊,两肩一耸,说:“这只是比喻,我们不必管它。”这解决不了问题。其实,当我们肯定一段话用的是比喻时,我们才刚刚开始而已;接着,我们必须辨认它,定义它,并且说明哪些经文证据促使我们说作者在这里用的是比喻。
最重要的是,解经者接着必须说明比喻代表什么,或它的用意。如果最自然的意思不是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就必须断定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比如,创世记2:7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我们说这是比喻性的表达,因为神并没有一个有手有口的肉身。到这里只是解经程序的一部分,下一步是要断定这个比喻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很明显,这段经文是迁就我们的软弱,要使我们可以明白神把他自己描述得像一个人(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这段经文的意思是,神直接又即刻地给人形状、生机、气息和生命。我们认为,这才是解经者研究比喻所应该进行的步骤。
四、平行段落
如果紧临的上下文中的有关字句不能帮助解经者发现经文的意思,他可以利用圣经中别处的平行段落。平行段落有两种:字面平行(verbal parallel)段落和专题平行(topical parallel)段落。
1. 字面平行段落
字面平行段落是指在相似的语境中使用相同的词、或提到相同主题的段落。在保罗书信的一段经文中,“奥秘”一词可能令人不解,但是在他对这个词的其他19种用法中,其中一种用法可能会解释得更清楚。然而,若推想出现该词的每处经文都互相平行,或仅仅因为这个词在上下文中重复出现就推想两句彼此有关,这些都是很危险的。
2.专题平行段落
专题平行段落具有相似的事实、主题、观点或教义,尽管所硏究的段落中的单词、短语和从句可能不同。最主要的例子是旧约中彼此对观的历史书(撒母耳记、列王纪、历代志),以及新约中的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此外还有段落重复的情形(诗14和53篇,诗18篇和撒下22章,诗96篇和代上16章,犹大书和彼得后书)。
通常,措词上的细微变化并不是因为传抄的错误,而是有意选择措词,以帮助读者理解作者讲论主话题时的微妙差别。在这些情况下,解经者可能会获得所需的视角,以便更好地理解所研究段落的平行上下文中含糊不明的字或概念。
有件事需要再次提醒,就是有些段落彼此之间虽然有近似的地方,其实并不平行。箴言22:2(“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和箴言29:13(“贫穷人强暴人在世相遇,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这两节似乎相同,但不能因此下结论说,因为这两节中都有穷人和在世相遇,所以“富户”就是“强暴人”,也不能说“造”等于“光照”。虽然“创造”和“光照”是同一位上主所为,但它们并不是同一个作为。同时,两个“在世相遇”未必都指在坟墓中。
专题平行段落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即路加福音14:26:“人……若不恨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说法,好像违反第五诚命。)以及马太福音10:37:“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此外,马太福音7:13-14和路加福音13:23-25也是真正平行的段落,虽然它们的上下文不同,但意思明显相同。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断言:“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路加福音记载,有人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问耶稣这个具体的问题:“得救的人少吗?”答案是“是少的”,因为“门是窄的”。
如果解释者细心,在词义含糊或上下文不能给主题提供什么亮光时,平行段落就能提供小小的(却是很有用的)帮助。
最难处理的就是圣经中“只出现一次的词”。由于字典、词典和相关的工具书是都是基于从大量上下文中收集用法实例,因此这些工具书有时也会因为缺少合适的示例而使我们失望。
有一个词只出现一次,用在主祷文中:“我们ἐπιούσιον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同样的请求出现在马太福音6:11和路加福音11:3。主耶稣指的是日用的、足够明日所需的饮食(由ἐπὶ+εἶμι“往前,趋近”的字根导出),还是必要的、所需的饮食(得自ἐπὶ+εἰμὶ;参οὐσία,指“存在、生存”)?其实没有人能肯定。该词的这个形式未出现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未出现在同语系的相关语境中。然而,就算我们不知道主耶稣所说的是哪个用法,但基本上我们还是知道主的意思。[24]
五、神学关键词
有许多专用词在它们第一次出现时或在随后的使用中被赋予重要的意义,成为引发性的词,促使读者想起之前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会通”它们所出现的文本的先前神学(下一章会更详尽地谈到“会通神学”〔informing theology〕)。这些关键词在介绍弥赛亚教义和救赎教义的经文中尤为重要。
这些应该特别注意的词汇,其本身(也许它们是头一次出现在一个决定性的评论中,或者列在一个关于应得之报应的信息中)有一个特定的样式。这不是说它们和上下文毫无关联,如詹姆斯·巴尔(James Barr)在其《圣经语义学》(Semantics of Biblical Language)[25]一书中所批评的;事实上,情况正相反:因为先前所说的话的整个语境,使该词在新的语境中更加重要,新的作者无疑很乐意回顾之前已经就该词所指明的,并以此作为基础,继续在神的启示下说话。
C. S. 路易斯(C. S. Lewis)把词义扩充的相关过程称为“分枝”(ramification),他提醒我们,这种作法不像昆虫的蜕变,而像树长出新枝一般。[26]
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定义一个神学词汇的过程。解经者若想硏究这些有许多“前述神学”(antecedent theology)背景的词汇,可以由下列词汇开始,如“后裔”、“仆人”、“圣者”(חָסִיד)、“枝子”、“地”、“安息”、“基业”、“家”(王位)、“耶和华的日子”、“敬畏耶和华”、“相信”、“慈爱”、“赦免”、“赎罪”、“凭据”、“和好”,以及其他许多词汇。[27]重点是在整个正典中存在着一个神学中心,在展开这个中心的关键段落中紧紧依附着一些词,就像紧紧地吸在船体上的藤壶一样,不肯放手。解经者所应该学习的就是这些字。首先,通过硏究、分析关键的上下文;其次,通过培养圣经神学研究和实践的一些技能。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一类型的分析。
总而言之,单词是组成意思的基本单位。我们要再次强调,单词绝对不能与它们所处的上下文分开,否则它们就变成不可信任的向导。但是,如果我们是以更广的上下文来看待和处理单词,那么单词对解经大有益处。
[1]比如Eugene A. Nida和Charles R. Taber所撰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Helps for Translators, 8 (Leiden :Brill, 1969) 56-98页。
[2] Milton S. Terry, Biblical Hermeneutics: A Treatis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New York: Phillips & Hunt, 1890;再版,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64) 191页。
[3]同上,186页。
[4] Brooke Foss Westcott,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The Greek Text with Notes and Essays,第二版(London: Macmillan, 1892;再版,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0),vi页。
[5] Raymond E. Brown, “The Sensus Plenior in the Last Ten Years,”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25 (1963) 268-269页。
[6] Norbert Lohfink, The Christian Meaning of the Old Testament,译者R. A. Wilson (Milwaukee: Bruce, 1968) 32-49页。
[7] Bruce Vawter, Biblical Inspiration, Theological Resources (Philadelphia: Westminister, 1972) 115页。相关问题的分析,见Walter C. Kaiser, Jr., “The Fallacy of Equating Meaning with the Reader’s Understanding,” Trinity Journal 6 (1977) : 190-193。
[8] Joseph Coppens, “Levels of Meaning in the Bible” 收录于How Does the Christian Confront the Old Testament?编者Pierre Benoit, Roland E. Murphy和Bastiaan van lersel, Concilium: Theology in the Age of Renewal: Scripture, 30 (New York: Paulist, 1968) 135-138页。
[9]关于这些观念的精辟讲论,见Otto Friedrich Bollnow, “What Does It Mean to Understand a Writer Better Than He Understood Himself?”
[10] David A. Clines, I, He, We, and They: A Literary Approach to Isaiah 53,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补充系列1 (Sheffield: Sheffield University, 1976) 59-61页。亦见同作者,“Notes for an Old Testament Hermeneutics” Theology, News and Notes (March 1975) : 8-10。
[11]见Barry A. Woodbridge, “Process Hermeneutic: An Approach to Biblical Texts”收录于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977 Seminar Papers, Paul J. Achtemeier编(Missoula, Mount: Scholars, 1977) 80页。
[12]同上,82-83页。
[13]这方面的讨论,部分起因于Gerald T. Sheppard, “Biblical Hermeneutics: The Academic Language of Evangelical Identity,” Union Seminary Quarterly Review 32 (1977) : 85-86。
[14] H. D. McDonald, “Theology and Culture,” 收录于Toward a Theology for the Future,编者David F.Wells和Clark H. Pinnock (Carol Stream, III.: Creation, 1971) 239,241页。另见Edwin M. Yamauchi, “Christian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23 June 1972,5-8页; John R. W. Stott和Robert T. Coote所编 Gospel and Culture: The Papers of a Consultation on the Gospel and Culture, William Carey Library Series on Applied Cultural Anthropology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1979) 5-33页; Alan Johnson, “History and Culture in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收录于Interpreting the Word of God: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Steven Barabas,编者Samuel J. Schultz和Morris A. Inch (Chicago: Moody, 1976) 128-161页。
[15]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讨论和相关资料,见Walter C. Kaiser, Jr., “The Literary Form of Genesis 1-11,” 收录于New Perspectives on the Old Testament,编者J. Barton Payn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Symposium Series (Waco, Tex.: Word, 1970) 52-54页,62-63(注16-20);另见John N. Oswalt, “The Myth of the Dragon and Old Testament Faith,” Evangelical Quarterly 49 (1977) : 163-72; Bruce K. Waltke, Creation and Chaos (Portland: Western Conservative Baptist Seminary, 1974),1-17页。
[16]原书举英译本之例,见Stott和Coote所编Gospel and Culture 8页。
[17]见Robert C. Sproul, “Controversy at Culture Gap,” Eternity 21 (May 1976) : 13-15,40。
[18] James Oliver Buswell, A Systematic 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共二册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62-1963) , 1: 368-373。
[19]见Walter C. Kaiser, Jr., “Paul, Women, and the Church” Worldwide Challenge 3 (1976) : 9-12。
[20]见对这项错误的优秀评论,在Mark Kinzer, “Misunderstandings of Scripture’s Ethical Teaching: A Case Study: Scanzoni’s Views on Homosexuality,” Pastoral Review 3 (1979) : 93-98。Charles H. Kraft常用文化语境的角度断定经文,但这颠倒了本书所提倡的解经程序。见他所撰“Interpreting in Cultural Context,”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21 (1978) : 357-367;和他的“Toward a Christian Ethnotheol ogy”收录于God, Man, and Church Growth: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Donald Anderson McGavran,编者A. R. Tippett (Grand Rapids:Eerdmans, 1973) 109-126页。
[21]参以下著作之讨论:Elmer A. Martens, “The Problem of Old Testament Ethics,” Direction 6 (1977) : 23-27;和Philip Nel, “A Proposed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Context of the Wisdom Admonitions,” Journal of Northwest Semitic Languages 6 (1978) : 33-39。
[22]正如Charles R. Taber在 “Is There More than One Way to Do Theology? Anthropological Comments on the Doing of Theology,” Gospel in Context 1 (1978) 4-10所主张的。见拙作评论,在Walter C. Kaiser, Jr., “Meanings from God’s Message: Matters for Interpretation,” Christianity Today, 5 October 1979,30-33页。
[23]本段叙述特别得助于E. W. Bullinger的定义,在Figures of Speech Used in the Bible: Explain and Illustrated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898; Grand Rapids: Baker, 1968再版),xi页。
[24]该词近代的硏究,见Werner Foerster, “Epiousios,”收录于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编者Gerhard Kittle和Gerhard Friedrich,译者兼编者Geoffrey W. Bromiley,共十册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4-1976), 2 : 590-99;或Wilhelm Mundle, “Epiousios,”收录于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编者Colin Brown,共三册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5-1978), 1: 251-252,253(参考书目)。关于如何使用辞典,如何从中找寻的卓越硏究,见John Edward Gates, An Analysis of the Lexicographic Resources Used by American Biblical Scholars Today,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Dissertation Series, 8 (Missoula, Mont.: S 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972)。
[25] James Barr, The Semantics of Biblical Language (New York: Oxford, 1961).
[26] C. S. Lewis, Studies in Wor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60),8-11页。
[27]值得硏究之建议,见David Hill, Greek Words and Hebrew Meanings: Studies in the Semantics of Soteriological Terms, Society for New Testament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1967); Norman H. Snaith, The Distinctive Ideas of the Old Testament (London: Epworth, 1944);和James Kennedy, Studies in Hebrew Synonyms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