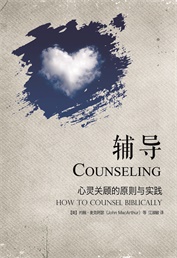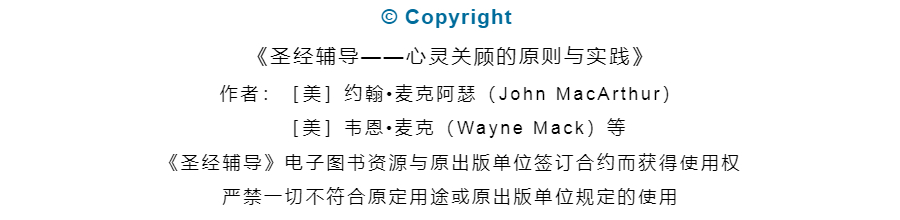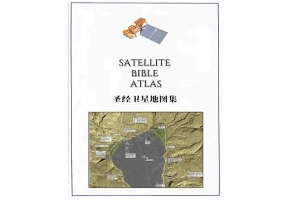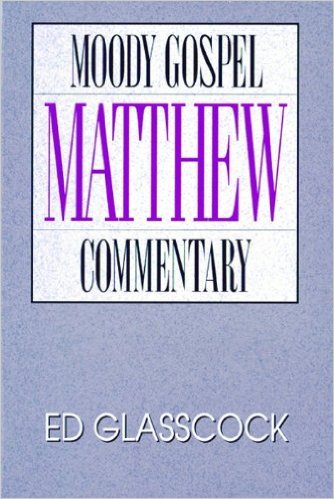过去二十五年当中,发生了一件值得庆幸的事,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重新发现了圣经辅导。如果我们重新发现什么东西,那意味着它曾经遗失过。圣经辅导是如何在教会中遗失的呢?想要一探究竟,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历史。
依照个案需求来提供教牧关怀,在讲英语的信徒当中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许多新教伟大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作者总能敏锐地将圣经与各式各样的“个案”联系起来,典型的例子包括:托马斯·布鲁克斯(Thomas Brooks)所写的《对抗撒旦的宝器》(Precious Remedies Against Satan’s Devices),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基督徒指引》(A Christian Directory),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宗教情感》(A Treatise Concerning Religious Affections)等。上述每一位作家,对于上帝所关注的事都持以热情,并且对于教义的真确、道德公义、自律而敬虔的生活以及基督化的服侍都抱以坚定的信念。不仅如此,他们更满怀着大牧者充满智慧的爱——在深刻了解人们需要的同时,还能感知渐进成圣(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的道路。[1]
上述著作中,爱德华兹的著述已有将近两百五十年的历史,而其他著作更在三百年前便已完成。早在19世纪初就有了圣经辅导。杰·亚当斯以伊卡博德·斯宾塞(Ichabod Spencer)为例,说明“在基督教事工盲从于精神治疗之前,一位长老会的牧者如何提供咨询辅导。斯宾塞在他所写的《牧者的素描本:个案研究》(A Pastor’s Sketches)当中描述了人们各式各样的问题,并讨论他如何面对及处理”[2]。史宾塞的著述完成于19世纪50年代,当时圣经辅导的智慧之泉仅剩几股细流,最终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内枯竭。
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基督徒,基本上已失去了过去对真理与技巧的应用,也就是说,虽然保守的教会在名义上仍持守着正统的教义、圣经道德的纯正、灵性的纪律以及使命的呼召,但失去了足以医治灵魂的实用智慧。教会失落了教牧技巧的关键元素,即一种能够洞察人的处境、人如何改变以及如何帮助人改变的智慧。一位牧者所具备的技巧,是一种应用的艺术与科学,一种带着丰富知识与敏锐判断的爱。然而这种在“个案”上应用真理的能力已经退化。事实上,到了20世纪初,自由派神学(liberal theology)与世俗心理学在辅导领域大行其道[3],先前残存的智慧遗迹只有在保守的基督徒身上隐约可见[4]。
世俗心理学占据了辅导的领域,宣称拥有辅导专长与透测人性的本领。保守的基督徒也许保留了一些爱德华兹的正统神学(formal theology),但是承续爱德华兹,对于人进行仔细观察与思考的人,却是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5]基督徒只保守了圣经,而心理学家则攫获了人心——这对任何地方需要帮助的人来说,都不是件好事!这个日益增长的教牧关怀优势,并非在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牧者当中,而是在世俗,或是在自由派(secular or liberal gospel)牧者身上。他们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其他尚在萌芽阶段的心理治疗法,来牧养一群没有牧者的人。心理卫生运动(the mental hygiene movement)、哈利·爱默森·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的教导、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关于自我治疗的福音,都是20世纪前叶典型的例子。
心理学家不仅夺取了辅导领域,更在其中贯彻了他们的理念。社会学家菲力普·里夫(Philip Rieff)给自己描述20世纪美国的著作起了一个再恰当不过的书名——《治疗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在此书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拥抱信仰的人生来为获得拯救;现在,拥抱心理学的人生来为接受取悦……如果治疗得胜,那么心理治疗师必然成为世俗的精神导师。”[6]里夫带着怀旧之情悼念基督教文化之死,但他只是顺应时势的现代人,而非召唤人们归向永活上帝的先知。[7]圣经辅导的目标、真理、方法,甚至是实行的可能性,都在心理学革命当中遗落。事实上,圣经辅导不仅消失无踪,甚至还变得令人不可思议。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有人重新发现圣经辅导之时,它在三个已经心理学化的社群当中,以外来者的姿态出现。当时所谓的辅导或心理治疗的文化背景就像是三个同心圆——在一个基本共识上存在各不相同,甚至对立的观点。涵盖最广、起主导作用的大圆代表世俗心理学,在此圆当中,理论创建者、大学及研究所的课程、资格认证、心理保健的制度与期刊书籍,决定了研究的基本方向。中间的圆则包含自由派教牧神学(liberal pastoral theology),它定义了当时教牧辅导的领域,甚至在保守的神学院中也是如此。最小的圆涵盖了身为心理学家或治疗师的基督徒。
上述的大圆主导着发生在另外两个小圆中的学术议题及治疗方法。就这样,基督教辅导者加入由心理学家、社工人员、咨询师及精神科护士所组成的大军团,成为灵魂医治行业中“征召”入伍的一员。军团中担任“指挥官”的,是精神科医师与人格理论专家,他们为一切心理保健活动提供知识内容及哲学思考基础。任何人想要讨论辅导的议题、阅读辅导的书籍、加入咨询师协会、接受咨询辅导训练,或是从事辅导,都逃不出这个大圆圈。圣经辅导就是这样以外来者的身份,出现在这片陌生的领土。
世俗心理学主导着咨询辅导活动,决定了关于人及其问题的一切论述。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以及医学在当时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权力、学术声望及自我肯定。正因如此,世俗关于如何了解及帮助人的观点,包围并渗透20世纪所有的辅导活动——各式各样的心理治疗法(世俗的教牧工作)淹没了圣经对灵魂的医治,各式各样的心理学理论(世俗的理论)代替了圣经对人性的解释,各式各样的治疗机构(世俗的教会团体)取代教会成为帮助人解决问题的地方。
那些观察最为敏锐的心理学家承认并坦言他们真正能做到的是什么。就连弗洛伊德也否认精神分析师可以被清楚地定义为医疗工作者。他曾声明,精神分析师是“世俗的教牧工作者”,而不是医生。[8]举例来说,弗洛伊德知名的学生艾瑞克·埃里克松(Erik Erikson)所接受的是人文领域的训练!卡尔·荣格(Carl Jung)与弗洛伊德有着类似的看法:“病人迫使心理治疗者担任起牧师的角色,期望并要求治疗者将他们从困境当中解救出来。这正是为什么身为心理治疗者的我们,必须去探讨那些严格说来属于神学领域的问题。”[9]斯金纳(B. F. Skinner)在他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中刻意提出了取代基督教信仰中的真理、技巧与组织的替代品。事实上,在斯金纳建构的乐园当中,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就扮演着牧师的角色。[10]世俗心理学这个大圆建立在一个世俗的宇宙观之上。扮演领导者的心理学家与精神科医师,是那些期望帮助世俗人们的属世之人。他们之所以提供了一个替代性宗教,是因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属于宗教。[11]
令人惋惜的是,自由派教会在一开始便加入了这个心理治疗革命,因而衍生出第二个圆——自由教牧神学(liberal pastoral theology)。这些教会的领导者摒弃了圣经真理与权威,而转向社会科学寻求权威及指引。福斯迪克提倡的神学自由主义(theological liberalism)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基要主义与现代主义(fundamentalist-modernist splits)的分裂。他同时也是心理卫生运动领导者之一,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福斯迪克在他的讲坛上大肆宣扬新兴的心理治疗性基督信仰,他对心理学的宣扬与信奉,其实与他对基督教基本信仰的怀疑是一体两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教牧辅导这一概念被定义为世俗心理学家对自由派神学的整合,其代表人物是卡尔·罗杰斯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大体说来,当时保守的基督徒干脆不涉及辅导这个主题,既不谈论也没有相关著述[12],而到了真正开始思考并从事辅导工作的时候,他们便撷取主导性的世俗心理学与自由神学理论作为典范。这些辅导的概念与做法的理论前提,既未受圣经真理的分析考验,也未遵循圣经的教导。没有人试图从根基上建立起一个关于圣经辅导的应用神学。大圆中的世俗心理学与心理治疗一直在与辅导相关的论述中扮演主导的角色。在此同时,属于第二个圆的自由神学,也不断影响着福音派的辅导概念与做法。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心理学研究所(成立于1965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显示世俗心理学与自由派的强势典范如何牵制了信奉圣经的辅导者。
[1]若查阅关于此传统的介绍,见本书第二章及Timothy Keller,“Puritan Resources for Biblical Counseling,”The Journal of Pastoral Practice 9 , no.3(1988):11-44。
[2] Jay L. Adams, The Christian Counselor’s Manual(Phillipsburg, N. 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1973),130(中译:亚当斯著,周文章、薛丰旻、郑超睿译,《胜任辅导》,台北:华神出版社,2004)。伊卡博德·斯宾塞(Ichabod Spencer)所写的《牧者的素描本——个案研究》(A Pastor’s Sketches)第一册及第二册分别于1850年及1853年出版。“素描”是斯宾塞用来代表个案研究的词。欲从历史观点对斯宾塞做更详尽的认识,请参考 E. Brooks Holifield, A History of Pastoral Care in America From Salvation to Self-Realization(Nashville: Abingdon,1983),第四章。
[3]关于此教牧职责被心理健康从业人员所取代的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可在Andrew Abbott,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一书找到发人深省的分析。请阅读第十章“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rsonal Problems Jurisdiction”(280-314页),特别是294-314页。作者谈到19世纪末的牧者在帮助人们解决个人问题上如何处于优势。“然而教牧式的分析当时还停留在初期发展阶段。在个人问题的解决逐渐成为一种专业之际,并没有人真正严肃地从神学观点将这些问题概念化。神职人员无法为其助人解决问题的种种事工提供任何学术基础,最终导致这些事工的消失”(286页)。于是,新兴的心理健康行业接管了这个领域。作者接着谈到稍后出现的“教牧辅导追随世俗心理学之风”以及“神职人员有意地摒弃传统事工”等现象。(310、313页)。
[4]举例来说,请比较托雷(R. A. Torrey)写于世纪之交的一本书 Personal Work: A Book of Effective Methods(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n.d.),以及本文所引用的早前著述。虽然托雷的著作有些弥补的作用,但它对于人、圣经、教牧事工以及改变过程的阐述与了解,却是十分匮乏。
[5]乔纳森·爱德华兹在《宗教情感》(三联出版社,2013)当中所使用的方法(与主题)被威廉·詹姆士接收于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n.p.,1902)一书,而此书成为现代心理学的奠基著述之一。
[6] Philip Rieff, The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 Uses of Faith After Freu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24 f.
[7]身为社会学家同时也是护教者的葛尼斯(Os Guinness)将里夫(Rieff)的洞见转为一种在许多层面上叫人悔改的呼召。见 No God But God, ed. Os Guinness and John Seel(Chicago: Moody Press,1992)一书中的“America’s Last Men and Their Magnificent Talking Cure”,111-132页。
[8] “‘世俗的教牧工作者’一词亦可作为一种概括用语,来形容身为精神分析师的医生以及非专业人士在与大众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Sigmund Freud,“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ostscript,”The Freud Reader, ed. Peter Gay(New York:W. W. Norton,1989),682 f。
[9] Carl Jung,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33),241. 此书最后两章“The Modern Spiritual Problem”与“Psychotherapists or Clergy”的论点强而有力。荣格将“神经官能症”视为精神层面的危机,而非医学上的问题。心理治疗企图赋予生命意义。荣格谈到治疗师该怎么做,当他们发现病人的问题衍生于“没有爱,只有性;没有信心,因为害怕在黑暗中摸索;没有希望,因为这个世界与生命已使他幻灭;没有了解,因为他无法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225页及以下),他力劝心理治疗师肩负起帮助世俗人们获得爱、信心、希望与了解的使命。
[10] B. F. Skinner, Walden Two(New York: MacMillan,1948),199(中译:斯金纳著,苏元良译,《桃源二村》,台北:张老师,1992)。
[11] Charles Rosenberg 关于 精神 医学 史的 创新 论述“The Crisis in Psychiatirc Legitimacy”应受到更广泛的阅读(此篇文章刊登于 American Psychiat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d. George Kriegman et al.〔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75〕,135-148; reprinted in Charles Rosenberg, Explaining Epidemics and O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Rosenberg 首先写道,精神医学扮演着人们所赋予的极度重要的社会角色——处理人类灵魂的各种问题。然而,精神医学在知识与治疗效果上却并没有什么建树。其次,精神医学的正当性在于其医学基础,然而它却无法真正地以医学专业的方式对病情提供解释与改善。再者,精神医学中最易被清楚划分为医疗活动的是照顾医院里具有慢性器质性症状的病人,它却属于较不受重视的精神医学,而享有崇高地位的精神医学,是那些哲学性、 教牧性与类神学性最为浓厚的领域。“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医学著作,都包括了对人类处境的广泛论述”(142页)。Rosenberg 几乎是在无可选择之下接受了精神医学的正当性。大体而言,并没有另一种提供人生意义的思想架构供人选择,因为旧有的信仰价值“对多数美国人而言,似乎不再具有影响力了”(147页)。不过,对于仍旧信服于传统信仰价值、相信基督的天父上帝的人而言,这种有别于精神医学的选择,是更加令人喜悦的。
[12]见 Holifield, A History of Pastoral Care: from Salvation to Self Realization,正如其副书名所透露的,此书本质上在描述心理学化的自由派如何取代了正统教义。Holfield 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陈述。例如他说:“当哈利·爱默森·福斯迪克将讲道形容为大规模的辅导时,他却忘了,新教(Protestant)最好的讲道,是诠释这本不能被降格为心理学的古老圣经”(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