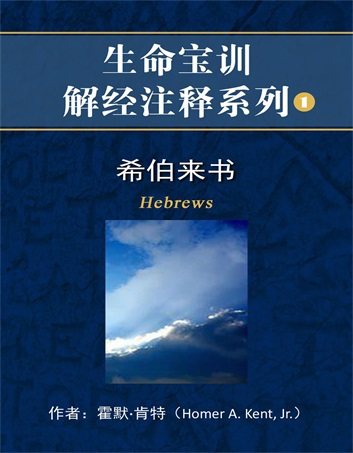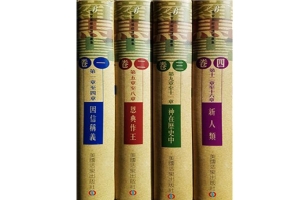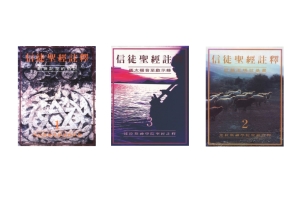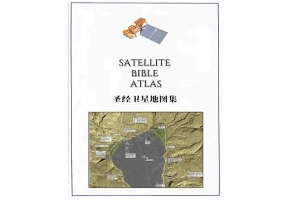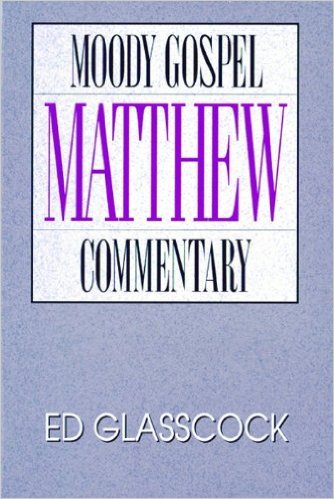导论
犹太基督教的早期历史对圣经学者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部分原因在于第一代基督徒是犹太基督徒这一历史事实。因此,了解基督教运动在犹太选民中的发展,就是了解基督教会的开端。使徒行传开篇几章为巴勒斯坦记录了这个精彩的故事。雅各书反映出在散居的犹太人圈子里的教会是如何理解和应用福音的。
然而,对于早期犹太人基督教感兴趣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们对其了解太少,尤其是关于公元1世纪的犹太基督徒。使徒行传后半部分大多在描述使徒保罗向未受割礼之人的宣教,只用吊胃口的寥寥数笔让人瞥见了犹太教会基督徒的态度(徒15:1-29,21:17-26)。虽然新约中有很多写给各地外邦教会的书信(从中可以看到那些教会特有的优点、弱点和问题),但没有一封可以肯定地说是写给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教会的。甚至雅各书和彼得书信[1]也不是只针对某个教会,而是针对散居各地的犹太读者。因此,任何关于公元1世纪犹太教会性质和特点的描述,特别是具体针对某一间教会,描述他们的思想和问题,都是受欢迎的。
犹太基督教有重要的意义,还因为基督教运动的基本特质。耶稣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他的到来应验了神向那王朝的统治者大卫具体的应许。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太5:17)。他教导说,他的死将会成为赎价,应验了旧约献祭体系所预表的(太20:28)。基督教因此是深深地扎根于旧约启示的,它的第一批追随者也是这样理解它的。在基督复活几周后的五旬节,彼得向信徒解释他们刚刚经历过的,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徒2:16)。然而没过多少年,基督教运动的总体特征就有了不同的色彩。随着保罗的宣教旅程,外邦人迅速涌进教会,最终使一个本质上的犹太人教会变成了一个犹太人数目不断减少的教会。
这样的转变若没有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有关这种冲突的证据在使徒行传第11、15章和加拉太书第2章,以及其他经文中都有记载。但我们还对许多问题感到好奇,特别是涉及犹太基督徒思想和态度的问题。在犹太基督徒必须要应对的问题中,以下几点必然包括在内:(1)如何根据许多旧约经文的教导来理解基督;(2)旧约体系中的宗教、文化和先祖的吸引力,特别是敬拜的可见特征与基督徒敬拜的属灵特征的对比;(3)基督教运动和耶利米预言的新约之间的关系;(4)来自犹太弟兄的迫害,以及想要放弃基督教信仰以免受迫害的诱惑;(5)旧约献祭的效力;(6)归信的外邦人和犹太教各种礼仪的关系;(7)犹太基督徒和外邦社会的关系。
希伯来书针对这其中的许多问题给出了极其宝贵的信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信中的犹太味儿是很明显的。它较早的成书时间也得到了证实。其恢弘的风格及其传达的信息,使之成为新约正典中最璀璨的宝石之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关于这封书信的一些基本特征的信息犹如石沉大海,使人不得而知。它的作者不详,最初的读者也难以确定。因此,我们必须逐一简短地看一下这些问题。
正典性
在新约之外的早期基督教书信中,罗马的《克莱门一书》(the First Epistle of Clement)清楚地引用了希伯来书。只举一个例子,在第36章,克莱门(Clement,又译作“革利免”)说完“耶稣基督,为我们献祭的大祭司”之后,开始引用希伯来书1:3、4、7、5和13[2]。公元1世纪的最后十年来自罗马无误的证据表明,西方的基督徒有幸使用这封书信。但奇怪的是,西方教会(显然)是最早获得这封书信的,却是最后普遍承认其正典性的。
其他知道希伯来书的早期作者包括:波利卡普(Polycarp,又译作“坡旅甲”)[3]、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查士丁”又译作“游斯丁”)[4]、提阿非罗(Theophilus)[5]、潘代努斯(Pantaenus,又译作“潘代诺”)、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6]和奥利金(Origen,又译作“俄利根”)[7]。优西比乌(Eusebius)(公元260~340)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是我们关于基督教时代开始几个世纪很多知识的来源,他将希伯来书列在已被教会主流观点认可的保罗书信之中,虽然他解释说有些人反对将这卷书列入正典,因为罗马的教会并不认为它出自保罗。[8]它没有出现在《穆拉多利经目》(Muratorian Canon)中,但这份公元2世纪晚期的文献是不完整的,让人很难评估它为什么被遗漏。在公元3世纪的蒲草纸文献46号抄本,希伯来书被列在保罗书信的罗马书后面。亚历山大的阿塔那修(Athanasius,又译作“亚他拿修”)(公元298~373)用“正典性”一词来描述公元367年发布的一份书卷名单,恰巧与我们的新约27卷书一致,其中包括完全被承认的希伯来书。[9]北非的奥古斯丁[10](Augustine,也称“希波的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和哲罗姆(Jerome,又译作“耶柔米”)(公元346~420)都承认希伯来书是正典[11]。
第三次迦太基大公会议(公元397年)第一次给出了官方确定的正典名单,当然它只是接受了主流观点。这份名单与我们新约的27卷书相同。它提到“使徒保罗的13封书信”,然后又加上了“由同一位作者写给希伯来人的信”[12]。希波大公会议(公元419年,也称为第六次迦太基大公会议)列出相同的27卷书,但只说“保罗的14封书信”[13]。
总而言之,希伯来书的正典性从一开始就被承认,虽然有些人,特别是西方教会,质疑它是由保罗所著。[14]亚历山大传统,至少早在潘代努斯和克莱门时期就接受希伯来书是正典,并且假定它是由保罗所著。[15]在希腊和叙利亚的教会,希伯来书至少从公元3世纪就被接受为保罗所写的正典。[16]到了公元4世纪,西方教会也同意与大家保持一致,这一点从奥古斯丁和哲罗姆等领袖的言论和做法中可以看出。
作者
对希伯来书作者的寻找已经持续了数百年,至今没有什么进展。候选的人不少,但每一个都缺少结论性的证据,不论提议哪一个,都存在问题。虽然这封信是写给一个特定的读者群体的,但信中没有附加作者的名字,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问候任何一位收信人。最可能的几个提议如下。
保罗
使徒保罗绝对是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在古代,东方教会正是因为相信保罗是这封信的作者,才很早就接受它为正典。到了现代,司可福串珠圣经的编辑们给希伯来书所加的标题是“使徒保罗写给希伯来人的信”[17],其他英文圣经也加了类似的标题。
最早提到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公元185~253)的作品中。优西比乌论到他这样说:
他说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但是用希伯来文写给希伯来人的。后来路加字斟句酌地将它翻译成希腊文,并向希腊人公开,正因为这样,这封信和使徒行传似乎具有相同的特点,但是没有加“使徒保罗”这一称谓。他说:“因为他在写信给对自己心存偏见和怀疑的希伯来人时,明智地略去了自己的名字,以免让他们一开始就感到不愉快。”[18]
亚历山大的奥利金(公元185~253)也了解针对希伯来书作者的不同观点。他写道:
我们听说有人认为这封信是罗马主教克莱门写的,还有人认为是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写的。[19]
奥利金自己也意识到,希伯来书和其他被接受的保罗书信在文体上有不同之处,虽然他承认该信在内容上与保罗是完全一致的。他的评论是:
这封标题为“致希伯来人”的书信,其措辞上的特点与保罗粗糙的语言风格不一致,保罗自己也承认自己言语(即文风)粗糙,而这封信的遣词造句是比较好的希腊文,任何知道如何区分词法上不同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然而,这封信的思想是让人仰慕的,任何仔细阅读使徒们的作品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20]
他最后针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是:
我的观点是:这封信的思想是使徒的,但是措辞和行文另有其人,他回想使徒的教导,可能之前记录下使徒的教导。如果哪个教会认为这封书信就是保罗的,这是可嘉的,因为前辈们这样传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到底这封信的作者是谁,只有神知道……[21]
除了早期历史这种得不出什么结论的见证,还有一些关系到这封信作者问题的内部考证。书信典型的结尾(13:25;参帖后3:17、18)、与“兄弟提摩太”(13:23)的关系、整体上先是教义紧接着是劝勉的结构,以及信中明显出自保罗的概念,都支持这封信是由保罗所写。[22]信中提到意大利,可以理解为是从保罗的角度出发的(13:24)。彼得的一句话,一直以来被解释为保罗曾经给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写过一封信,这封信被竭力主张是希伯来书(彼后3:15、16;彼前1:1;彼后3:1)。但必须承认,这些事实虽然与保罗的作者身份一致,却不足以下结论说是保罗写的。[23]
针对传统认识也指出了一些问题。书信中没有给出名字,这个特点与保罗一贯的做法不符。作者承认自己所领受的基督福音是经由他人证实的,(2:3),而保罗常常坚持认为自己不是从人领受的福音(加1:12)。这个观点不是不可逾越的(见注释部分),对早期的教父似乎也并不重要,但是很多人认为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这封书信的写作风格以及作者对七十士译本的偏爱,也在某种程度上与保罗不同,保罗的写作更加直白,不加修饰,他也不像希伯来书中那样连续引用七十士译本。
巴拿巴
关于巴拿巴的提议是由迦太基的德尔图良(Tertullian of Carthage, “德尔图良”又译“特土良”)(公元150~222)第一个提出的[24],在近代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25]。支持这一提议的理由如下:(1)作为利未人,巴拿巴应该对犹太礼仪有深厚的兴趣,并且应该对这些程序也极为熟悉;(2)“劝勉的话”(13:22)可能暗指巴拿巴的另一个称呼“劝慰子”(徒4:36);(3)作为一位来自塞浦路斯的犹太人,他可能与亚历山大或至少是希利尼思想有密切的接触,这一点从书信的预表和某些哲学概念中可见一斑;(4)巴拿巴在五旬节后不久归信,他可能受了司提反教导的影响,这一点可能体现在这封书信中;(5)在使徒行传第9章,巴拿巴在犹太基督徒和保罗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也可以理解为他借着这封书信做了同样的事,将保罗的思想解释给犹太信徒。
然而,我们同样遇到一个难题:巴拿巴对得上号,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是唯一具备资格的人。希伯来书主要描述的是会幕礼仪,而不是圣殿礼仪。肯定也有其他基督徒持有司提反和保罗的观点,他们也能够写这封信。大名鼎鼎的巴拿巴,居然在一封实际上由他所写的书信中完全没有留下姓名(而一部伪经反而假称他的名字),这一事实使得人们反对将他看作这封书信的作者。
亚波罗
亚波罗一般被认为是路德最早提议的,从那以后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26]人们给出的理由通常如下:(1)亚波罗熟悉保罗,应该深谙保罗的理念;(2)他来自亚历山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书信中会有哲学的暗示,以及为什么偏爱七十士译本;(3)他精通旧约,希伯来书的作者显然也是如此;(4)他在哥林多的教会接触到提摩太;(5)他的口才可能反映在这封书信优美的文笔中。
这个假设最大的弱点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早期历史的证据。奇怪的是,亚历山大是当时最伟大的基督教学术中心,这里有潘代努斯、克莱门和奥利金,然而它没有任何线索暗示一个土生土长的亚历山大人写下了这封杰出的书信。
其他建议
还有许多其他提议,但大部分都不像上面提到的三位那样持续引起人们的兴趣。奥利金曾提议罗马的克莱门(Clement of Rome),但是克莱门自己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中却没有这样说过,实际上他还采用了一个与希伯来书的核心论点相反的观点。亚历山大的克莱门认为,路加是保罗最初用希伯来文所写的希伯来书的译者,与希腊文的希伯来书没有任何翻译痕迹的观点相左。还有人提议西拉,因为他在罗马为人所知(彼得前书5:13的“巴比伦”指的就是罗马),是保罗和提摩太的同伴,曾经在耶路撒冷教会,应该熟知圣殿的程序。近年来,这个假设被强烈支持,理由是希伯来书和彼得前书所谓的语法很相似(假设西拉是彼得的书记员)[27]。除此之外,还提到很多人,包括腓利、百基拉个人或与亚居拉共同执笔、约翰·马可以及阿里斯提昂(Aristion),这表明目前学术界还不能真正达成一致。奥利金一语中的:“究竟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只有神知道。”唉!我们是不得而知了。
收信人
就像作者的身份一样,原始读者的身份也完全丢失了。对于他们是哪个民族的以及是哪个地方的人,学者们都不能达成一致。书信的名称“达希伯来人”[28](To the Hebrews)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但是书信本身并没有说读者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结果很多学者否认第一读者有任何犹太渊源。费恩-贝姆-库梅尔(Feine-Behm-Kümmel)说道:
这不太可能是为犹太基督徒写的。书信中关于不要“把永生神离弃了”的警告(3:12)更像是针对外邦基督徒,而不是犹太基督徒读者。希伯来书没有体现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对比,甚至都没有Ioudaios和ethnē这样的词。作者就是写给所有基督徒的。[29]
然而,这个古代名称的重要性以及几个世纪以来的主流观点不能这样轻易地搁置一旁。另外,此书信的内容比持反对观点的人所说的更具有犹太人的特点。它没有提到外邦社会,其全部内容都是在犹太历史和宗教背景下解释的。书信中没有驳斥诺斯替派或异教的观点或行为。
威廉·曼森(William Manson)写道:
在希伯来书中,唯一受到批评的错误教导与饮食律有关,这一点与保罗的罗马书惊人地一致,那里说到罗马教会的一部分人被要求遵行同样或类似的教义,这成为使徒严厉责备他们的唯一问题。另外,希伯来书要求“不可停止聚会”(10:24-25),这与圣保罗命令罗马弟兄要“接纳”或“款待”构成关系紧密的反义平行。[30]
他还说道:
唯一看起来合理的解释是,犹太人关于饮食的教义给教会带来了危险(13:9),它们在犹太礼仪中被认可为依据而加以推广。
一旦假设读者群对古老的犹太教及其敬拜、许可、仪式、神圣特权和恩典的施予有好感和倾向,我们看到的所有这些特点就有了一个真正的解释和合理性。如果我们将这个群体放在外邦基督徒的背景下,就找不到同样的合理性和可被理解的地方了。[31]
大多数保守的人都会同意,希伯来书的犹太基督徒特征是不证自明的,尽管读者是哪个地方的人还有待确定。
那么这些犹太基督徒到底住在哪里?各种提议不胜枚举,包括耶路撒冷、凯撒利亚、撒玛利亚、安提阿、巴勒斯坦、吕吉斯谷(Lycus Valle,可能是歌罗西)、以弗所、加拉太、塞浦路斯、哥林多、比利亚、亚历山大和罗马。布鲁斯(F. F. Bruce)给出了极为详尽的概述。[32]选项如此众多,显然支持其中任何一个,其证据都不足以让所有人认可。但其中有两个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它们比其他提议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
尽管耶路撒冷作为希伯来书的受书地点很有吸引力,这种指认还是带有一些问题。难以理解如何将经文2:3应用在公元1世纪的耶路撒冷读者身上,因为它暗示他们没有亲自听到耶稣的讲论。另外,这些读者以他们的爱心著称(6:10,10:34),而耶路撒冷基督徒以他们的贫穷闻名(他们开始遭受迫害之前的早期时段除外)。还有,这些读者还没有经历殉道(12:4),而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失去了司提反(徒7:59、60)、约翰的兄弟雅各(徒12:2),可能还有主的兄弟雅各(他在希伯来书成书的时候可能已经离世),大概还有其他人(徒26:10)。最后,如果作者想的是耶路撒冷读者,他在讨论犹太礼仪的时候一次都没有提到圣殿(希伯来书只提到会幕),这更令人费解。
一个貌似更合理的受书地点是罗马。关于“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33],应该指的是那些远离家乡的罗马基督徒,和作者一起向家乡的教会致以问候。(但是短语“从意大利”也可以解释为表明作者和问候之人当时的位置。)最早对希伯来书的引用出现在罗马的克莱门所写的书信里(但是,他也引用了以弗所书和哥林多前书,这两卷书显然不是送往罗马的)。那场带来财产损失但还没有带来生命损失的迫害(10:32–34; 12:4),被解释为公元64年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或指公元49年克劳狄(Claudius,又译“革老丢”)颁布法令的结果。
伦斯基(Lenski)总结说,保罗到达罗马并与犹太领袖会面,使得一半的犹太首领都归信基督(徒28:17-24),这使他们的会堂顺势变成了一个基督教会,归信的人无需加入城市中已有的外邦基督徒群体。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之后,尼禄开始迫害教会,直接针对的是基督教会,而留在自己会堂中的犹太基督徒则逃过了最猛烈的一击。伦斯基总结说,希伯来书是在保罗死后不久,由亚波罗写给罗马犹太基督徒肢体的。他看到了这样的问题,即他们想要放弃基督教信仰,回归从前的犹太教。[34]
另外,威廉·曼森虽然同意罗马是收信人的最佳地点,但他解释说,这里所说的迫害指的是公元49年克劳狄颁布的法令。他认为,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所说的Chrestus,代表的是犹太群体中关于传播基督福音所引起的纷争,并总结说,所有的犹太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受到经济上的损失,但没有到殉道的地步(见徒18:2)。他认为,收信人当时的问题不太可能是回归犹太教,而是他们与犹太文化的连接过于紧密,无法看到基督教的普世性使命。[35]他们没有像司提反那样,抓住耶稣是救世主这一更广阔的视角。
尽管如此,认为罗马就是这封信的受书地点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格思里(Guthrie)提醒我们说,在罗马几乎没有人是通过亲眼见过主的人所传而接受福音的(2:3、4),除非我们假定他们大多都是从巴勒斯坦移民过去的。他还指出,希伯来书中的犹太教(显然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与罗马书中的犹太教明显不同。[36]但曼森反驳了这一点。[37]关于假设这封信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另一个质疑是,希伯来书丝毫没有提到外邦人。只有认为这封书信单单是写给罗马的犹太基督徒群体的,而不是写给罗马所有教会的,这个难点才能被解释。
对于本书作者来说,这封信的原始读者就是希伯来基督徒,这一点似乎很清楚,他们可能在罗马,也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虽然不太可能是在巴勒斯坦)。仔细研究信中的五个警告段落,可以看到他们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被引诱离开基督教,回到犹太教的安全港湾。他们这样做,既可以避免来自犹太同胞的迫害,也可以享受犹太信徒从政府而来的合法保护——这是当时的基督徒无法享有的福利。如果一个人认为,6:4-6、10:26-29和10:38-39等处的经文只是勉励读者从一些次要的犹太习俗中得自由,似乎就没有充分地理解它们。
写作日期
写作日期的确定取决于作者和收信人的身份。由于这两者都没有定论,希伯来书的写作日期只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些指导原则的。
由于罗马的克莱门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引用了这封信,所以希伯来书的写作日期不可能晚于公元96年。书信的内证也给出了一些亮光。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提摩太还活着(13:23)。假设公元50年保罗拣选提摩太的时候(徒16:1-3),他20岁左右,根据这一点,这封信的写作日期可能是公元1世纪的后半叶的任何时候。然而,我们也不可将这封信的日期定得太早,因为读者已经归信了一段时间。他们显然是第二代基督徒(2:3),归信的时间足以让他们在灵里成熟起来,但不幸的是,在某些方面并非如此(5:12)。他们归信的时间已经足够长,可以回顾曾经遭受的迫害(10:32-34,12:4)。如果说这迫害与公元49年克劳狄颁布的法令有关,那么成书日期可能在公元60年代(但可能在公元64年尼禄执政之前,因为那时的确有人为信仰流血[38]),关于这一点有足够的内证。另外,他们一些初期的领袖已经离世了(13:7)。
信中还表明,犹太人的献祭体系仍在运行,这说明它的成书日期应该在公元70年之前。我们注意到以下经文:
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7:8)
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8:4)
……总不能藉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10:1、2)
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10:8)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10:11)
有人争论说,上述经文中的一般现在时只不过是文学性或历史性的现在时陈述。他们参考的是公元70年后也用一般现在时来描述犹太礼仪的其他作者。[39]况且,这里描述的是会幕礼仪,而不是希律的宫殿,这一事实使得任何关于时态的讨论都显得多余。[40]然而,基于希伯来书作者的主旨,这个争论并不能这样轻易地被驳回。当然,必须要理解的是,在犹太人的敬拜中,会幕和圣殿从本质上是一个(虽然后者当然是前者在历史上的延续)。另外,如果当时的事实真的是圣殿被毁、献祭停止,作者还可能这样描述献祭吗?这难道不会影响他在10:2的措辞吗?作者的主要观点之一,便是坚持摩西之约是暂时的,它最终会被取代。为了表明这一点,作者引用了耶利米书的一个陈述,暗示摩西之约是“旧的”,并且他辩称,这也是在暗示它已过时,最终会被取代(8:13)。如果他指出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而这审判使献祭体系彻底终结,并以此支持他的观点,那么他不这样做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鉴于以上种种,这里的一般现在时态的确为解决这封信的写作日期问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因此,将写作日期定在公元60年代与现有的数据契合。
[1] 尽管仍旧有充分的理由,尤其是根据彼得前书的情况来看,可以相信彼得书信的收信人是犹太人,但今天人们不再像以前那么普遍认为,它们是写给犹太基督徒的书信。
[2]“The First Epistle of Clement to the Corinthians,” in The Apostolic Fathers, I. 71, trans. A. Kirsopp Lake.
[3]“Polycarp to the Philippians” (chap. 12), in The Apostolic Fathers, p. 299.
[4] Saint Justin Martyr “First Apology” (chaps. 12, 63), in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VI.
[5] Alexander Roberts and James Donaldson (eds.), The Ante-Nicene Fathers, II, 107.
[6] 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6. 14, trans. Roy J. Deferrari, p. 26.
[7] Eusebius 6. 25, p. 50.
[8] Eusebius 6. 25, p. 50.
[9] Archibald Robertson (ed.), “Select Writings and Letters of Athanasius,” in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IV, 552.
[10] Philip Schaff (ed.), “St. Augustine’s Christian Doctrine,” in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II, 538, 539.
[11] W. H. Fremantle (ed.), “The Principal Works of Jerome,” in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VI, 101, 102. 关于希伯来书的不确定态度是由于该书的作者问题,并非其正典性。
[12] Charles Joseph Hefele, A History of the Councils of the Church, II, 36. 这些正典书卷实际上是早在393年召开的希波大公会议上通过的,但这些记录已经失传了。它们在397年的迦太基会议上被重新确认。
[13] B. F. Westcott,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p. 437, fn. 9.
[14] Roy J. Deferrari, 优西比乌《教会史》的罗马天主教译本的译者,他得出这样的观察结论:“这封书信的正典性从未受到质疑,但其作者的身份从早期的教父时代一直到今天都有争议”。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Eusebius Pamphili, Ecclesiastical History, Books 1-5, p. 140, fn.
[15] Eusebius 6. 14.
[16] Paul Feine, Johannes Behm, and Werner G. Kümmel,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trans. A. J. Mattill, Jr., p. 275.
[17] The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ed. C. I. Scofield, p. 1291. 把作者归结为保罗的说明在《新司可福串珠圣经》中已经被删除了,p. 1311.
[18] Eusebius 6. 14.
[19] Eusebius 6. 25.
[20] Eusebius 6. 25.
[21] Eusebius 6. 25.
[22] 例如,希伯来书5:12-14“吃奶”的说法有些贬低的语气,这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2中的用法相似,但与彼得前书2:2的用法不同。
[23] 尽管现代趋势显然否认保罗是本书的作者,但一些当代作家还是偏向认为保罗是作者,其中包括William Leonard, The Authorship of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Herman A. Hoyt,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Arthur W. Pink, An Exposition of Hebrews.
[24] Tertullian “On Modesty” (chap. 20), Alexander Roberts and James Donaldson, eds., IV, 97.
[25] J. Vernon Bartlet, “Barnabas and His Genuine Epistle,” in The Expositor, ed. W. Robertson Nicoll, Sixth series V, 421–427.
[26] Theodor Zah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II, 356; R. C. H. Lenski, Interpretation of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p. 22; C. Spicq. L’Epȋtre aux Hebreux, I, 209–219.
[27] E. G. Selwyn, The First Epistle of St. Peter, pp. 463–466.
[28] 希腊文是 Pros Hebraious,潘代努斯最早使用,如优西比乌的《教会史》6.14所记载的。
[29] Feine, Behm, Kümmel, Introduction to the NT, p. 280.
[30] William Manson,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p. 13.
[31] Manson, p. 158.
[32] F. F. Bruce,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pp. xxxi–xxxv; 亦见 Donald Guthri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Hebrews to Revelation, pp. 37–41.
[33] Greek: aspazontai humas hoi apo tēs Italias (13:24).
[34] Lenski, Interpretation of Hebrews, pp. 14–21, 22, 23.
[35] Manson, Epistle to the Hebrews, pp. 40, 41, 71, 163, 24.
[36] Guthrie, Hebrews to Revelation, p. 40.
[37] Manson, Epistle to the Hebrews, p. 13.
[38] 然而Lenski争论道,这封信是寄给在罗马的一群希伯来基督徒,尼禄的逼迫主要针对外邦基督徒,这些希伯来基督徒也被迫逃离。因此,他认为写信的日期是公元68或69年,Interpretation of Hebrews, pp. 21, 22。
[39] 见 Guthrie, Hebrews to Revelation, p. 42。
[40] Feine, Behm, and Kümmel, Introduction to the NT, p. 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