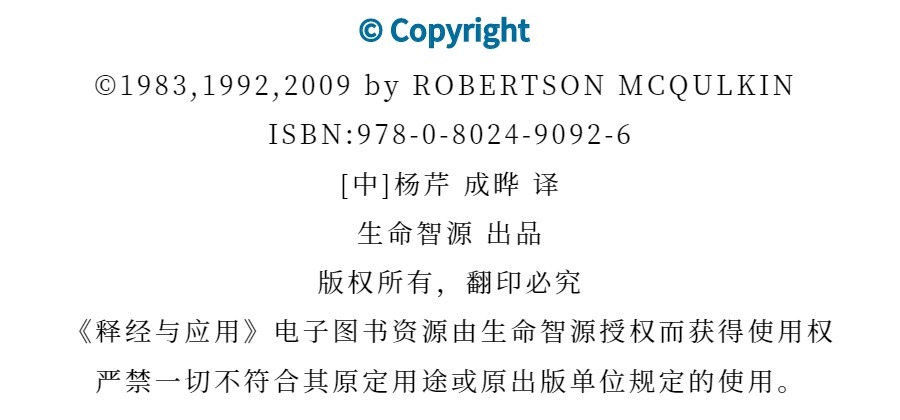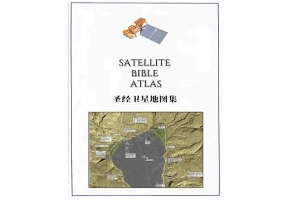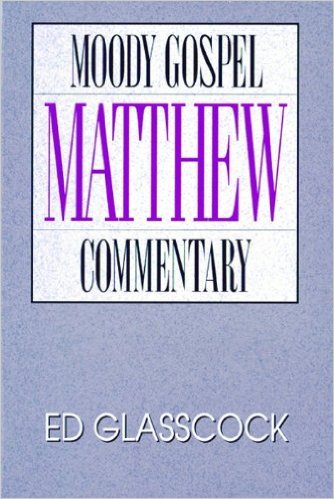普遍原则
普遍原则是指可以应用于一种以上情况的规范或标准。然而,对这种原则的回应当与对具体指导的回应相同:信心和顺服。因为普遍原则不总是一目了然的,所以给我们的信心和顺服增添了色彩,需要我们勤奋、开放以及有勇气。也就是说,我们要勤于探究、愿意改变和勇于挑战传统的解释。
圣经的普遍原则是从哪里来的?基本上说,圣经普遍原则的来源有四点。让我们逐一详尽地查考。
直接陈明的原则
从某种意义上说,“要爱人如己”(利 19:18)是一个直接的指示,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普遍原则。圣经在其他地方具体阐述了爱应当如何表达。但是,我们必须发掘出该命令对当代生活的全部意义,因为圣经并没有将它的相关原则应用到所有的当代问题中。例如,这一原则如何体现在雇佣关系或跨国公司的政策中?我们一生都当对该原则的应用孜孜以求。
从直接宣告中提出的普遍原则
总结出普遍原则可以从一个或一组直接教导中推理出来。例如,圣经中有一系列关于性纯洁的直接指示。“不可奸淫”(出 20:14)、“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在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太 5:28)。这类诫命背后的原则与性纯洁有关,这条原则背后还有一条原则,就是忠贞,而忠贞背后又有一条原则,就是爱。
一条有关圣洁的普遍原则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能让圣经在当代人的生活中成为切实的权柄。例如,看色情图片或窥阴癖行为在圣经中没有被直接定罪,因此,一些福音派心理咨询师就用色情图片来医治有问题的婚姻。但如果从圣经一系列的诫命中得出一条非常明确的原则并加以应用,上述事情就不可能发生。身心上的纯洁是从很多教导中总结出来的原则,这些教导涉及的主题包括性、罪的本质(意识上的和肉体上的)、忠贞、爱,等等。
从历史事件中提出的普遍原则
一个历史事件总会有它的意义,否则,历史事件也就不会被写进圣经了,而且它们的意义往往不只一个,这些意义无非是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这一类事件可以被当作例子来阐明一些重要真理。但我们若想从历史事件中提出一个普遍原则,必须要根据圣经对该事件的解释,而不能擅自提出教义或原则。
圣经只是对所记录的部分事件做出了评判—要么是称赞,要么是谴责,有时还会进一步解释称赞或谴责的理由。这一类经过解释的事件有助于我们从中提取普遍原则。例如,既然亚伯拉罕因献以撒而被称为信心的典范,那么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行为是应当称赞的,即使我们本来可能不会这么想。既然圣经赞许埃及接生婆说谎,谴责亚伯拉罕和撒拉说谎,那我们在将这些例子应用于当前行为之前,必须先找出圣经赞许或谴责背后的原则。可是,如果圣经并没有说该事件是否应当受称赞,我们就不可从中提取原则或将它应用在自认为相似的情境中,我们不能以圣经记录的情景为权柄树立一个标准。
我们要远避恶人的错误,并从对他们的惩罚中得到警诫(林前 10:11);我们要以义人为榜样,特别是他们的行为被用作例证来阐明神旨意的时候。保罗反复告诉我们要效法他,因为他效法基督。然而,保罗分裂犹太会堂建立教会的模式是我们当效仿的榜样吗?诸如此类的历史事件必须借助圣经直接、明确的教导加以解释。只有这样,它们才能作为某个原则的释例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如果圣经没有表明神是否赞同该行为,我们就不能擅自带着权柄加以应用,或将它作为榜样要求别人效仿。
思考约伯的故事。如果我们从中得出所有试探都来自魔鬼的原则,是不合理的。某一历史事件(例如约伯的经历)只能够得出这样的原则:某些试探是出自魔鬼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某一具体的试探可能是撒旦的作为,但若说所有试探都直接来自撒旦,则需从其他地方找到证据。
保罗对腓立比的狱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 这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记录,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说,这句话也可用于其他人。但狱卒问保罗的话是“我该怎样做”,而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该怎样做”。保罗根据他的问题,具体告诉他该如何行。我们不能从保罗针对狱卒的回答得出一个关于如何得救的教义。这教义必须从其他地方证明。
彼得回答一个类似问题时说“你们各人要悔改…… 受洗”,基督回答一个类似问题时说“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 来跟从我”。我们不能凭自己的喜好从这些教导中挑选,而必须研究所有圣经数据,并以圣经教导为依据建立一个在任何特定历史背景下都有效的普世标准。
圣经中非历史性书卷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也可用来提取可应用于今天的普遍原则。例如,在《罗马书》15、16 章中,保罗记录了很多关于他个人的细节,并向当时居住在罗马的人给出了具体吩咐,还包括许多问安。这段经文主要针对历史上特定的群体和事件,其中大部分教导都不能被直接应用于我们。但是,这其中也掺杂着一些普世性的教导。保罗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在福音已经传到的地方传福音(罗 15:20)。这并不是所有基督徒甚至宣教士都必须效仿的原则,而只是保罗特定的“工作说明”。但是,当保罗说到外邦教会在属灵上受过耶路撒冷基督徒的恩惠,因此有责任在物质上资助那些基督徒时(罗 15:26-27),他似乎暗示了一条普遍原则。为什么?不仅因为这一教导在圣经其他地方明确给出过,还因为保罗在同一段经文中给出了该责任的原因。这原因是作为一个基本原则给出的:他们应该给予,因为他们在属灵上得了好处。
我们还可以从祷告和诗歌中引申出普遍原则。如果它们反映了敬虔之人对神敬虔的回应,那我们应该可以放心地这样祷告、吟唱。但是,只有当这些祷告和诗歌是出自被圣灵默示的圣经作者时(例如大卫或保罗),才具有无误真理的权柄。即便如此,应用时仍要小心。例如,所有基督的祷告并非都适合我们效仿。牧师或许可以用基督为门徒的祷告为会众祈祷:“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约17:8、15)。他甚至可以继续这样祷告:“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18节)。但是,他不能这样祷告:“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24节)。虽然有的牧师这样做,但它并不恰当!
总而言之,历史性经文在引申出普遍原则时的权威性分为三个层次:
1. 如果圣经本身对某一事件进行了评价,并给出了评价的原因,这一历史事件具有提出普遍原则的最高权威。
2. 如果圣经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褒贬进行了评价,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原因,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一事件与圣经明确的教导一起用于提出一个原则。但按这种方法提出的原则不具有同等确定的权威。
3. 应用性最低的是圣经未做任何评论的历史事件。虽然这些经文或许可以用做圣经其他地方明确教导的真理释例,但它们不能单独被用于建立规范性的基督教教义或行为。
从不能被直接应用到当代生活的经文中提出的普遍原则
如前所见,圣经中很多诫命或教导是:(1)被上下文限定了受众或应用环境的;(2)被后续启示修正的;或者(3)看似与圣经中更明确、更强调和持久的教导相抵触的。
然而,因为它们出自神,这些教导在某方面反映了神的旨意。因此,神虽然无意要每个人都遵守这一具体的教导,但它们背后一定有某些与神的品格相合的普世真理。既然它们是局限于当时或者后来被修正的,怎么会有任何价值呢?
如果圣经给出了某个诫命或教训的目的,即使教训本身不是普世性的,它也具备普遍应用的原则。在从历史性经文中提出原则时,可运用同样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圣经给出了目的,那目的就成为一个不变原则的基础。例如,神命令约书亚赶走迦南人,使之成为以色列人的居住地,这难道意味着神想要教会向占据同一个地方的穆斯林发动圣战吗?当然不是。但神为什么要那么做?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爱以色列人,而这个原因是神所有行为背后的一个不变的原则。
但是,如果圣经没有明确揭示诫命的目的,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从不适用于当代人的教导中推导出潜在的普遍原则吗?与历史性经文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它与普世教导的明显对应关系,那么运用这个有限的教训作为神旨意的解释或许是恰当的,但是,这种解释与对经文的任何其他当代应用一样,不具备启示真理的权柄。
思考圣经中(尤其是旧约中)直接且明确地表明了教导的目的,但是被后来的启示修正过的经文。
例如,神在旧约中会直接地、明确地命令征战。在教会历史中,很多人都认为这一点支持正义的、攻击性的战争。然而,耶稣基督教导基督徒不要抵抗,而且明确说他的国不在这世上,不应该用武力保卫或扩张他的国。但是,不论基督的教导对人际关系或国际关系有什么意义,我们都不能说所有战争都是违反神旨意的。哪怕神仅命令发动过一次战争,也表明神并非完全不能接受战争。既然有些战争是正当的,有些是不正当的,那我们就不得不寻求这些命令背后的原则,来解决这些教导表面上存在的冲突。因此,我们或许可以从一段不能被直接应用到当代生活的经文中提取这样一条普遍原则,即战争并不总是错误的。
我们已经考察了从圣经中提出原则的四种方法。当这些原则明确是神的旨意时,它们就与那些明确的教义或指示拥有同等权柄,需要我们以信心和顺服回应。神的启示中充满了各种原则。
马歇尔博士(I. Howard Marshall)如此强调说:
我们应当从某一特定境况的圣经教导中挖掘潜在的圣经原则,并将这些原则应用于我们当前的境况和问题上,而不是直接将某一圣经境况应用于现代,无视两者的差别,错用经文佐证。[1]
麦克森(A. Berkeley Mickelsen)提出了相似观点:
“经文的应用包括从这段经文中发掘出一个适用于所有神子民的原则或者适用于相似处境下的每一个人的原则。”[2]
如果这些见解不会导致反对圣经直接宣告的应用,还是很有价值的。不论是圣经的直接宣告还是以正确方式提出来的普遍原则,神都期待我们用信心和顺服去回应。
请注意有关普遍原则的另一个事项。虽然圣经明确启示的原则具有神旨意的全部权威性,但信徒或教会对这个原则的应用则不具备同样的无误性。我们在运用时可能会犯错。但无论如何,我们有责任不断地以我们对这些原则及含义最清楚的理解来加以应用。
[1] I. Howard Marshall, “Is the Bible Our Supreme Authority?” His, March 1978, 12.
[2] A. Berkeley Mickelsen, Interpreting the Bibl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3), 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