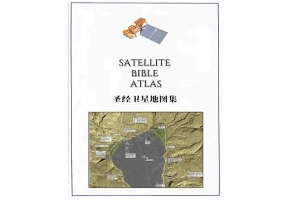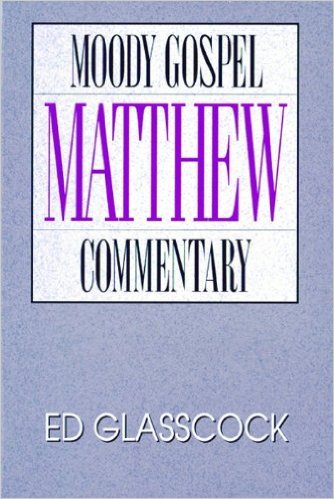序
约翰·本格尔(John Albert Bengel)曾在1742年说:“圣经是教会的根基,教会是圣经的监护者。教会刚强时,圣经的信息就光辉万丈;教会生病软弱时,圣经就因被忽略而遭腐蚀。因此,圣经的外在形式和教会的外在形式,不是同时健康强壮,就是一起生病软弱。人们对待圣经的态度,正反映出教会的健康状况,这已经是不变的定律。”[i]两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能证实本格尔的警言是正确的。教会和圣经真是兴衰与共,教会因着放胆传讲圣经经文而得到滋养和坚固;否则教会的健康将受到严重损害。
众所周知,世界上多处地方教会状况不佳。她一直在渐渐衰弱,因为她被“垃圾食品”喂饱了。她吃了各种的人工防腐剂和添加物。结果,为确保健康而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致癌物或有害物破坏身体的这一代,却为神学知识和圣经学知识的营养不良所困。普世的属灵饥荒,实在是由于缺乏神话语真正的供应(摩8:11),这种情形仍旧持续肆虐于在无形教会的几乎每个实体。
本书并不能指出所有的原因,也不能提供所有的解决之道。但笔者既然受教会元首的委托,为整个基督教会装备牧者,我深感欠了教会一笔特别的债,需要我偿还。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意识到,在准备讲章的事上有一条鸿沟,也就是说,在硏究经文(包括运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等圣经原文)和实际向神的百姓传递信息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很少有圣经和讲道训练机构会花时间或精力向学生展示如何由分析经文过渡到组织讲章,使他们的讲章能直接取自经文且符合对该经文的分析。
即使在这个选定的范围内,本书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必须坦率地说,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这方面并没有完整的指导文献可资参考。根据我所能发现的,在欧美人士中没有人尝试过撰写“解经神学”(exegetical theology)的著作。这一发现本身就令人吃惊。“解经神学”是神学教育的核心。简而言之,它是既是“论证”,也是整个过程的最后一笔。讲台事工一旦失职,其他辅助性事工,如基督教教育、辅导、社区参与,甚至传福音和社会活动,都会随着萎缩,甚至垮掉。在这个方面,本格尔说得最准确,也非常切中要害。
因此,我们必须有所行动。这里所做的一切反映了我个人试图改变这一困境的尝试。几十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解经和讲道的“句法—神学方法”(Syntactical-theological Method)。然而,我很清楚,本书只能被视为探索性的和暂时性的初步成果。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解经神学探讨》(Toward an Exegetical Theology)这本书的一个积极影响是,将催生出许多类似的“解经神学”——这是何等美善的事啊!
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该领域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到需要这样一个工具。许多人准备接受挑战,撰写类似的著作。我相信这本书可以鞭策他们完成他们的计划,因为全球事工都有这个需要。也许当我读完所有这些佳作之后,我可以把书名的“探讨”二字除掉,写一本增订的《解经神学》(主若许可)。
我写作时尽可能顾及到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显然,由于每个人的能力和背景不同,各人从书中所领受的也就不一样。读者最好先读那些他比较容易吸收的部分。本书有一两点谈得比较深入,因为我不但愿意与注重实践的同工进行对话,也愿与那些专精的学者进行对话,以及那些可能不认同我们的神学信念却正在积极寻求解决同一问题的人进行对话。
依我个人之见,一个希望完全准备好的人,若还不能直译希腊文或希伯来文,他就不该冒然解经。然而,我也知道许多神所选召的牧者、圣经教师、宣教士,以及第三世界的传道人与教师,他们还受着环境和教育机会的限制,那么神用来衡量他们的尺度(也许连同他们所服侍的对象),将不同于那些有优厚条件却不使用的人。为此,我已经表明,即使一个人只能读到圣经译本,本书所介绍的方法也是有益的。当然,这些人可能还需要再买一本不必太贵的教科书,以便复习他们自己的语法、用语和句法结构,其实,这是全民义务教育(更不用说高中、大学了)的全部内容。从前人们刚殖民美洲时,每个人都学习读书写字,主要不是为了找一份好的工作,改善经济状况,而是为了能自己读神的话,增长灵命。同样地,如果将本书的建议付诸实践,就意味着复习诸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等定义的基本知识,那也是值得的。让我们重新学习语法、句法的定义与基本规则吧!这关系到人的生命!
我必须向主献上感谢,是他赐下帮助和能力,我才能在极其繁重的讲道、授课负担之余完成本书。我相信,无论是身经百战的牧师,殷勤带领查经班的同工,渴慕自己深入挖掘神话语的弟兄姊妹,还是刚刚开始讲台服侍的神学生,都会从其中得到莫大的助益。但我依然祈求,更重要的是,读者都能感受到笔者委身于神的话语之下的意愿和回应,从而清楚认识到此书涉及的不仅仅是学术研究。
本书的完成得力于许多同工的忠心参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贝克书房(Baker Book House)的兹尔斯特拉(Zylstra)先生,他从1973年以来就不断地督促、鼓励我完成本书;还有我的妻子玛格丽特,以及格拉姆斯和埃尔文两位先生;还要提到我的秘书阿姆斯特朗,她细心地为我录入手稿。最后,要提到我的研究助理阿丁顿,他在我写作过程中多次帮我校对。
[i] John Albert Bengel, Gnom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rew R. Fausset编,共五册(Edinburgh: Clark 1857~1858),1:7。英文译本曾修改其中一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