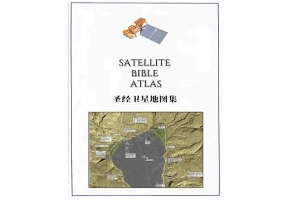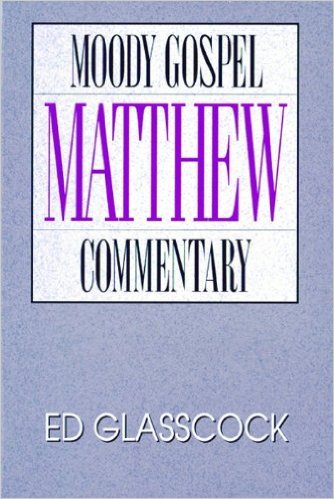第二章 解经学的定义与历史
虽然我们这一代人随手可及各种圣经手册、词典和期刊专文,我们还是很难为圣经的解经(Biblical exegesis)下个可行的定义。由于这方面的学习是整个神学课程的基础,我们指望至少能有一两章的详细内容,来专门定义解经的含义和任务——尤其因为目前没有一本工具书能为初学解经者详细列出解经的方法,对资深的解释者就更没有了。
1963年,奥托·凯泽(Otto Kaiser)和沃纳·格奥尔格·屈梅尔(Werner Georg Kümmel)应德国福音派神学学生协会的要求,撰写了一本小册子。[1]这本小册子虽然在列出许多高等批判学和低等批判学的各类书籍上出色,[2]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我们认为,这本小册子除了在主要论述中简短插入对罗马书5:1-11和马太福音12:22-37的注释外,更着重于向解经者介绍经文批判(Textual Criticism)、文体批判(Literary Criticism)、希伯来诗歌节奏分析、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传统批判(Tradition Criticism),以及主题、概念和内容的解析等各类参考资料。[3]
问题是,因为几乎所有敢于尝试叙述解经的本质和任务的人,都随着这个大纲和方向来发挥。例如,1973年维克托·傅尼斯(Victor Paul Furnish)在《珀金斯学派神学期刊》(Perkins School of Theology Journal)上发表文章就是用这个大纲:(a)经文分析;(b)文体分析;(c)历史分析;(d)神学分析。他在结论中提到翻译的问题和五个解经规则。然而,在这篇颇长的文章中,最后一页才说到“解释经文本身”这件事。[4]
在我们看来,他的最后一页才是整个事情的核心,至少要占解经工作的75%。解经教师常常太热衷于史学、词义、文句平行、考古、碑铭材料等领域的最新发展,这些占据了他们解经的整体工作和使命的大部分时间,以至于解经最主要的目的濒于灭绝。这种情形如果继续下去,解经就成了“圣经序说”的同义词,沦为对圣经不同程度的导论而已。
我们当然需要找出所查经文的正确语境,但也要平衡,不可偏废。我们认为,背景研究是绝对基本和重要的,必须在深入研究特定段落之前进行。这就是奥托·凯泽和屈梅尔的论点中特别注重的。但不能强调得太过,以致取代了对经文本身的直接硏究。
即使在傅尼斯转而给出我们能借以研究原文对象的七个步骤时,他的建议仍旧偏重主题或专题的研究,而不注重对具体文法或句法的直接分析。他给解经者的建议有如下几点。
(1)列出经文要点(但依照什么原则或程序而得呢?傅尼斯只是建议:“照你所观察的。”);
(2)记下经文中的难点所在,或者比较不同的译文,看看彼此是否有重大的差异(但解经是否只限于有难题的部分呢?);
(3)确认关键词或主要概念(但如何确认?);
(4)列出经文中其他所有历史、文学和神学问题(这似乎又回溯到背景研究了);
(5)初步拟定符合整体上下文的经文大纲(宁可叫大纲与段落本身的发展联系更密切);
(6)参考其他与这段经文思想相近的经文或“相关文学”(但是,解经者必须优先考虑更早期的经文);
(7)记下经文可能有的“任何更广泛的意义”。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这份清单很满意。很少有其他的解经者试图在这种程度上指引学生。但是,从我对这些建议的编辑评论看出,这份清单并没有教人如何从现有的短语、从句、句子和段落中推导出教导或讲道的大纲。这正是需要完成的工作。因此,我们还是必须尝试对解经的工作加以定义,并说明解经的任务是什么。
一、解经学的定义
英文的“解经”(Exegesis)一词是由希腊文的ἐξήγησις音译而来,原意是“叙述”或“解释”(它的这个名词形式并未在新约出现,只在七十士译本之梵蒂冈抄本,即旧约的希腊译本的士师记7:15出现过一次)。希腊动词形式是ἐξηγέομαι,直译作“领出”(注意前缀ἐξ)。七十士译本中的ἐξηγέομαι主要译自希伯来文的סָפַר,这个词的加强式意为“叙述、告诉或宣称”。新约中这个动词只在约翰福音出现过一次,并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共出现五次。[5]其中约翰福音1:18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父〕表明出来。”路加福音记载主在以马忤斯路上显现之后,当晚革流巴和他的同伴将这些事向其他人“述说”,即“讲解”或只是“叙述”(路24:35)。同样地,哥尼流向其他人“述说”他所看的异象(徒10:8);保罗和巴拿巴“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神迹奇事的意思(徒15:12);彼得“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徒15:14);保罗也“一一述说”神借着他向外邦人宣教所成就的事(徒21:19)。
从新约这有限的几处用法中,我们就可以清楚看见“解经”(Exegesis)跟“释经”(Hermeneutics)——解释的科学——有密切的关系。ἑρμηνεύω一词及其相关词汇在新约中大约出现了20次,有一半是“翻译”的意思,因此马太福音1:23说到希伯来文的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而马可福音5:41将亚兰文的“大利大古米”就“翻出来”作“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但相关的词汇διερμηνεύω的意思是“说明”或“解释”,常用于对与原先不同之听众讲述旧约经文的时候;例如,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将所有关于自己身份、工作的事都“讲解明白”了(路24:27)。所以传统上,解经和释经都专注于经文本身,志在断定经文原始目的中的内容和意思。然而很不幸的是,并不是教会历史的所有时期都强调这一点。
在宗教改革的强烈冲击下,人们重新强调,如果解释者要忠于他的使命,就只能在一处经文中取得“一个概念”或“一个意思”。解释者唯一的目标就是查验并尽量清楚地解释出作者写这段经文时的意思,解释的工作就是“重现经文”,而不是表达解释者的成见、感觉、判断或顾虑,因为任意表达就是在“解入”,是在“读入”个人希望经文有的意思。宗教改革者采取的立场支持早期的安提阿(Antiochian)学派,与奥利金(Origen)在亚历山大所倡导的学派相对立。
正是在这一点上,事情对现代解释者来说变得复杂了。虽然大家对“解入”都有某种程度的嫌弃,把它看作解经的低劣替代,但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解经能够用这样客观的术语来定义。对于许多现代人来说,意思已经变成“多重的”——他们认为意思有不同的层次。[6]
维恩·波伊思雷斯(Vern S. Poythress)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难道经文的意思真的只有一个吗?”[7]直到最近十年,这个问题的答案仍是:“是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文文本的意思。”
波伊思雷斯对这个回答十分不满,他没有把自己受限于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有人不理智地称为“故意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也没有从听众的反应中获得的意思(笔者认为应当称之为“情感谬误”〔Affective Fallacy〕),[8]波伊思雷斯主张讲论的意义同样存在,是由那些具有足够的语言学和历史背景知识的称职的法官来确定。[9]然而,即使我们同意只有“称职的法官”才被允许确定讲论的意思(这种奇怪的观点同时辩说还有说话者的意思和听者的意思),波伊思雷斯的结论还是令人失望,他说:“因此,区分不同类型的意思是有其用的,但它本身不会告诉我们哪一个或哪一些意思才是‘经文原义’。”[10]这正是建立多重意思的真正问题所在:在这些不同的意思之间,谁来为我们作出裁决呢?
这种多层次的系统势必要诉诸“元沟通”(Metacommunicative)的维度,它要使我们不按照句法和语义结构来理解经文,而按照经文在我们头脑中“实现”的各种方式来理解。
简单地说,这种看法教导我们不但要读圣经,也要读自己。如此,对于大部分现代人来说,所有寻找“真实或单一意思”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这样一来,经文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意思结构。正如苏珊·威蒂格(Susan W. Wittig)所说,这些意思结构可能是荣格型(Jungian)、佛洛伊德型(Freudian)、结构专家型(Structuralist)或深层结构型(deep-structure),等等,不一而足。[11]
另一个近代学者主张,确实有“不同层次的意思”,可以分成两类:“本体意思”(Ontological Meaning,真正的、有权柄的意思)和“美学意思”(Aesthetic Meaning,超越经文字面意思的意思或意义)。[12]根据这种看法,阐释工作是循环的,[13]而不是传统的从解释到默想再到应用的线性过程。
所有这些不但为解释圣经带来难题,也给解释近年来所有关于释经学的文章带来困难。那些作者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时间试图传达一个关键观点,即存在着被锁定在一个解释循环中的多重意思?看来,这些现代的作者是想暂借单一意思理论和传统的线性过程解释法(linear-movement hermeneutic),直到建立他们自己的论点,然后他们希望在解释其他文件(如“圣经”)时进一步使用单一意思的解经方式作废,因为他们认为应用单一意思解释法是一种过时的解释方法。
单一意思解释法(single-meaning hermeneutic)最强的根据,可以从一般的谈话或著作中看出。如果意思不是单一的,“沟通”本身即便可能,也会困难重重。如果说话者或作者本人不能掌握自己的用词,如果意思不能表现他们用词的原意,那么我们就会处在最艰难的境地:大家都在沟通,但没有哪个人能特别接收到(或知道有没有接收到)信息。
这不是说解释者能把说话者或作者所有想表达的细枝末节都捕捉到,而只是说,有足够的交集,使得有可能对传达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有足够的了解。事实上,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会认为,会众或解释者所得到的是对传达者思想的“全盘”理解(包括所有细枝末节),更不用说对整个主题的全盘理解了。
因此,释经学(Hermeneutics)力图说明有助于硏究经文的一般或特别的原理和原则,而解经学(Exegesis)则力图确认个别短语、从句、句子中的单一真理意向,因为这些元素构成了段落、章节,最终构成了整卷书的思想。如此,释经学可以说是指引解经学的“理论”,解经在本书中可以理解为找出作者想表达意思的“实践”或“步骤”。
二、解经学的实践
牧师、神学生和认真的圣经解经者都震惊地发现,实质上没有人为解经者指明一条实际路线,引导他们进入解经实践。相反地,初出茅庐的解经者所学到的,只是这条路的两头已经充分检验过的两个方面:(a)对所传讲的经文本意的来源作预备性的研究;(b)对解经者到达讲道的场合时讲道的最终形式作详细处理。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工作如何做呢?很不幸,我们都只能靠自己尽力而为。我们在接下来的各章中希望探讨的,正是这项任务。
首先,我们要提出一个堪称首要的原则:预备讲道,必须从经文开始,并且必须以传讲神的话语为目标;这样,就可以在丝毫不损经文原有规范的情况下,尖锐而恰当地针对现今状况传讲神的道。
然而,即使我们提出这个原则,可能看起来经文只在解经的开头是重要的。其实,一旦存在挑战经文地位和重要性的其他事物,解经的过程就己经偏离了正轨。解经者还可能犯很多其他的错误,但这个错误是最具破坏力的方法论错误。
经文文本既然是解经的中心,那么掌握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就是基本的要求。但是,掌握圣经语言的目标必须恰当,这项公认的艰难研究,要做的工作一定有很多,绝不只是烦琐的语言翻译,以及正确地分析动词形式。这些方面的硏究一旦成了解经的主干,解经的结果就会少之又少,致使解经不合情理。
如果神学生在语言方面学到的专业知识仅止于此,那还不如开一个讲座,教导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动词结构的基本性质,再教他们使用词汇分析工具书,以便按字母排列顺序找出动词的分析,这种方式能很快分析出每个动词。还可以再开一个讲座,指点各种译本的使用方法(也许包含一些类似杨氏直译本圣经〔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或逐字对照圣经等材料),以及“经文汇编”的使用(汇编后面应该列出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音译表),这样就已经达到最低要求了。
我确实见过所有这些工具被介绍给门外汉,他们能够写出足以叫人接受的解经论文——如果这就是解经学的要求的话。毕竟动词已经被分析,许多字形的范围也已经被指出,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日期、作者、文体和形式等方面的注释,也只不过是鹦鹉学舌。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学原文的最大作用是了解短语、从句以及句子中的句法和文法。其实,各个单词或词组之间的连接要素,才是语言学习所有汗水和泪水的所在。如果我们不以此为语言学习的目标,那么我们也应该转向前面概述的简化方法,尽管这种方法严重依赖于前述方法,其结果是间接推导出来的。
然而,我们坚持认为严肃的解经者应当学习掌握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文法、句法的基本原则;否则一个人大部分的解经亮光都必然倚靠那些自称对这些语言有高深造诣之人的叙述了。当然,没有多少神学生、神学教授或成熟的牧师,能把每一个文法、句法细节牢记在心,但手边有标注清楚的语法书会带来巨大的帮助。很明显,我们在翻译方面的经验越丰富,我们就越能巧妙地处理较为晦涩的难题。
熟悉文法和句法结构需要的不只是死记硬背,甚至也不止是有能力辨认一处经文归属于文法书的哪一项。爱德华·哈勒(Edward Haller)曾论到“鉴别能力”(Faculty of Discernment),[14]指的是一种使人能用心细读每一个句子的能力,直到我们能够辨别出句子的风格、结构、美感和作者心中意思的细微差别等。哈勒警告说,匆忙、肤浅和固守成见的心灵是正确解经的大敌。缺乏语言能力已经够糟糕了,这几项对正确的解经更有害!
哈勒又鼓励那些渴慕能解经的人要有持久的耐力,要有训练有素的思维和方法,要有源于个人信仰的信心,也要有渴慕的心,期望亲身体验从经文中发现的真理对生命转变的影响。只有持之已久的努力工作而得收获的那份喜乐支撑着我们,探索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哈勒告诫,整个过程必须通过祷告和痛苦的经历来磨炼。解经的路并不容易,需要付出大量的工作,但最终它的回报就像它最初的要求一样令人敬畏。
为了避免有人说我们主张放弃一切介绍性的研究,我们要特别强调:解释者完成对圣经书卷的作者、年代、文化和历史背景的透彻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些重要资料,要理解该书在特定时空下的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圣经各卷书的作者、文化、时代、文体、组织原则等进行背景研究非常有用,也非常有必要,这算是为硏究经文做恰当的“预备工作”。但我们终究必须回到经文本身,它必须占用我们大部分的精力和注意力。我们必须对经文的短语、从句、句子、段落或诗段进行最详细的调查和硏究分析。
我们若有不正确的观念,就必导致解经学的不当教导。比如,若以为解经学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功能是探究Sitz im Leben(生活的环境或状况——大多学者会注意重复的模式,而比较疏忽独特的历史事件)和Sitz im Buch(圣经的环境或状况——取决于对史前文学单元的研究),便会如此。尽管这些方面的硏究有许多是正确的,但是一旦它们变成解经者唯一注意的焦点,那么这门学科就成了跟班跑腿的,沦为给“圣经序说”(isagogics,即圣经导论,包括高等批判〔亦即年代、作者、时代、受书者、文体〕和低等批判〔亦即经文和原典〕)当跑腿的了。我们要再说,“圣经序说”十分必要,也真的会对解释者有帮助,但它仅是预备性的。
另一个预备工作将是最有用的:解经者要准备所研究经文的译文。下面的方法会很有帮助。
你自己译完经文,并确定你已经理解所有的单词及其在句子中的功能之后,接着要很快看一下另外五种版本的译文,如果这些译文之间有任何显著的差异,就记下每个版本中有问题的短语、从句(列在不同的行中以便研究)。然后写下你自己的翻译,并简单地说明你为什么选择这种翻译(见图2.1,译者注:我们可采用一些中文译本,如和合本、吕振中译本、现代译本、文理本、官话本、思高本等)。
RSV:
NEB:
NAB:
NASB:
NIV:
自己的:
理由:
图2.1 译文比较表
三、解经学的历史
研究各种不同的解经理论和解经历史的变化历程有其特别的价值,最明显的益处就是解经者可避免某些解经传统中的过度行为。同样地,这样的研究也能够引导人们了解那些已经证明其价值并经过事实和时间考验的方法。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可把基督教解经的历史分成五个阶段:使徒时期、教父时期、中世纪时期、宗教改革时期和宗教改革后的时期。
1. 使徒时期
所谓使徒时期,我们通常指的是基督教纪元的第1世纪。这时期给人的印象,基本上就是新约作者对旧约的引用。然而,也有必要谈谈一些教派的解经,如库姆兰社团(Qumran community)的爱色尼派(Essenes)的解经,以及广义上的拉比解经(Rabbinic exegesis,包括早于使徒时代的材料,以及后来的他勒目作品〔Talmudic〕和中古犹太〔medieval Jewish〕的解经文献)。我们这样分类固然稍嫌体系化,却便于讨论。
当传统的犹太人着手进行解经时,他俨然面对两部妥拉(Torah,律法)法典:旧约的成文律法和如《塔木德》(Talmud)中保存的口传律法。对犹太人来说,两者具有同等的地位,因为口传律法包含过去的阐述和解释,这些注解据说也是从摩西那里接收的,所以也源于西奈山!
口传律法的一个主要类别可以定义为“解释律法的规则”。借着这些规则(或称“米多”〔Middot〕)的运用,旧约圣经文本被扩展、限制、给出类比、推论,并加以澄清和解释。
释经学(Hermeneutics)的三个主要体系是由拉比文献(Rabbinic literature)中发展出来的,包括:希列(Hillel,约公元前30-公元9年)七条著名的基本规则;拉比以实马利(Rabbi Ishmael,约公元60-121年)的十三条规则,它们是发展“哈拉卡经文解释”(Halachic texts,即宗教和民事律法)的“米大示法”(Midrashic method)的主要工具;以及拉比以利以谢(Rabbi Eliezer,公元2世纪)的三十二条规则,它们用来解释“哈加达经文(Haggadic Text,即著名的讲章)。[15]
“米大示解经法”起源于公众的演讲或讲道。讲道者先读一段经文,以此提出他所要讲的主题,然后用比喻来说明这个真理,再用当时人们所熟悉的谚语来加强。这个规则写在“米大示”的雅歌注释(1.a)中。
为了使这些讲道在美学上更吸引人,给听众带来愉快的体验,讲者经常在讲道中穿插相关语,用精简的文字使论点更清晰,并且在相关的人和数字之间寻找某种方式的类比。这种点缀容易变成神秘的或含有寓意的意思,一般称之为“奥秘解经”(Sod),意即“秘密”。这种形式的解释在犹太人著名的讲章、轶事、传奇的集录“哈加达”(Haggadah)中尤为常见。
比较合乎理性、平易、简单的解经方法叫作“释义解经”(Peshat),其形式在“哈拉卡”(Halachah)中比较常见(“哈拉卡”的希伯来文动词形式是“去”,是指传统律法或作法)。希列的七个规则是这个方法的最佳代表,在此对其进行简述。
(1)Qol wehomer,קֹל וְחֹמֶר(轻与重)。这个规则是以经解经(希列的七个规则都是如此),从比较不严格、不重要的部分,转入更有“哈拉卡”价值、更重要、更严格的部分。使用这规则和逻辑的一个例证,在耶利米书12:5:“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另见创44:8;出6:12;申31:27)
(2)Gezerah shawah,גְזִירָה שָׁוָה(表达的等值〔或类比〕)。根据相似的短语或单词,甚至是单词的词根,在两段不同的经文文本之间进行类比。例如,主耶和华的使者告诉参孙的母亲,不可剃刀“剃”参孙的头,因为他要作拿细耳人(士13:5);又如,由哈拿的起誓也可以推测,不会有“剃刀”会碰到撒母耳的头(撒上1:11),他也是拿细耳人。
(3)Binyan ab mikathub ’eḥad,בִנְיָן אַב מִכָּתוּב אֶחַד(以单一经文为基准的建构)。以一处明确的经文作为根据、起点,由此推出一个适合所有类似经文的准则(ab意为“父亲”)。这很接近后来新教徒所称的“首次提及法则”(Law of First Reference)。例如,因为神从荆棘中第一次呼叫摩西时称呼说“摩西,摩西”(出3:4),所以得出结论:神每次对摩西说话时都这样称呼他。
(4)Binyan ab mishene kethubim,בִּנְיָן אַב מִשְׁנֵי כְתוּבִים(以两处经文为基准的建构)。这个其实是上一个规则的延伸,是以两处经文或一处经文的两点作为一个普遍结论的根据。例如,在出埃及记21:26-27中虽然只讲到身体的两个部分(眼和牙),但所指的是身体的每个部分。因此,人若致残了奴仆身体的任何部分,都要使他得自由。
(5)Kelal upherat,כְּלָל וּףְרָט(一般与特殊)。一般性叙述先被提出,然后接连着一个将一般原则具体化的陈述。例如,创世记1:27说到人类一般的创造,即“造男造女”;但创世记2:7和2:21说到神所用的材料,以及女人如何被造。后面的两段经文不是另一个创造的历史记录,也不与创世记1:27冲突,只是把前面一般性叙述具体化而已。
(6)Kayoṣē’ bo’ mimeqom ’aḥer,כַיוֹצֵא בוֹ מִמְקוֹם אַחֵר(其他经文旁证的类比)。可以用第三段经文解释另外两段。例如,据记载,耶和华呼叫摩西是“从会幕中”(利1:1),又是“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出25:22);这两个表面上的矛盾可以用民数记7:89解释,说到摩西必须进会幕去听神在“二基路伯中间”所说的话。同样,将撒母耳记下24:9、历代志上21:5与历代志上27:1比较,最后提到的经文被用来解释前两处表面上的数字差异。
(7)Dabar hilmad me’anino,דִּבָר הִלְמַד מְעַנִינוֹ(从上下文而得的阐释)。正确的解经一定要考虑整个上下文,不能断章取义。例如,对于出埃及记16:29“第七天各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这句话,不应理解得那么绝对,而只限于在安息日不许人出到旷野拾取吗哪。
以上的拉比解经体系,对教会是个忧喜参半的祝福。它在许多规则(米多〔Middot〕)中介绍了“释义解经”(平易、简单或字面的方法),但它的趣味性,以及对更深层次、更奇异意义的探索(即“应用解经”Derash),往往与严肃、字面的解经方法背道而驰,最后“奥秘解经”(Sod)胜过了对“释义解经”(Peshat)的关注。
库姆兰社团的爱色尼派是一个末世论派别,他们认为自己是活在最后的日子里,也确信先前的预言可以(并应该)直接应用在他们的时代和他们教派的历史中。
他们的解经方法只是引用1到3节经文的简短段落,作为“话”,然后将这句话加上“别沙”(Pesher〔解释〕)。他们倾向于把他们当时的人物、活动和状况,“直接”与经文中的人物、活动和状况相提并论。为此,哈巴谷书1:4的“义人”变成他们教派的创始人,即“公义的导师”;“恶人围困义人”中的“恶人”则是逼迫(甚至可能杀了)他们创始人的“邪恶的祭司”、“说谎的人”。哈巴谷书1:6的“迦勒底人”变成罗马人,为这个教派所痛恨,盼望他们赶快退出巴勒斯坦。
使徒时期解经法则的另外一大来源,就是新约作者对旧约的引用。许多现代学者争论最为激烈的是,新约作者主要采用了一些宽松的规则,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这些规则已经在犹太社团里实施。[16]
然而,这个结论极不可能成立。如果新约作者想要说服多少带有敌意的听众,使他们相信旧约已经详细预言了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许多特点,那么他们必然会用“释义解经”,而不用“米大示”、“别沙”或“奥秘解经”。为了使旧约适应新约的情境,任何形式的新约对旧约的临时现代化,其真相都会被轻易认出来。
例如,有人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9-10和加拉太书4:21-23使用了“别沙”解经法的一种,其实这个结论是由于错误地理解保罗对申命记25:4和创世记16、21章的用法。[17]又有人说,保罗在罗马书10:5-10、[18]哥林多前书10:1-6、哥林多后书3:12-18、[19]加拉太书3:16和以弗所书4:8[20]用“米大示”法或“别沙”法,对此我们绝对不能苟同。相反,我们认为新约作者引用旧约经文以建立某一事实或教导的所有段落中,他们所领会的是经文自然、直接的意思。这不是说他们没有引用旧约作其他的目的。例如,他们有时借用旧约的文字,却不采用其论点,而不过是用作例证,取其描述的画面而已。但是新约作者进行严肃的解经时,其要点建基于以下事实时,他就不会用这种方式:旧约预见的某个特点已经在新约明确实现;或者旧约是新约所倡导的原则或教导的基础。
2. 教父时期
早期教会的解经历史,基本上是亚历山大(Alexandria)学派与安提阿(Antioch)学派相争的历史。[21]但早在这一僵局出现之前,早期教父明显表现出寓意化解经的倾向。
例如,波利卡普(Polycarp,又译“坡旅甲”)的学生爱任纽(Irenaeus,使徒约翰的门徒)在公元185年所写的作品《反异端》(Against Heresies)中,提到旧约所说洁净与不洁净的牲畜是预表人类的等级。旧约律法把分蹄倒嚼的牲畜定为洁净的(利11:3),爱任纽认为分蹄预表那些向父和子而行的人,倒嚼则预表昼夜默想律法的人;不分蹄不倒嚼的牲畜代表外邦人,倒嚼而不分蹄的牲畜则代表犹太人。“巴拿巴书”(Epistle of Barnabas,约成书于公元130年)中有更多这种令人恼火的解经例子。
然而实际上,在公元2世纪末和3世纪初,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克莱门”又译“革利免”)和奥利金(Origen,又译“俄立根”)把这种“寓意法”制度化。奥利金在其作品《首要原则》(De Principiis)中解释了他的方法,他主张每一处经文都有潜在的三重意思(他后来甚至又推想到四重意思的可能性)。这些寓意法学者深受斐洛(Philo)的影响,每当在下列情况下,就诉诸解经的这一方便之策:(a)经文中出现了他们以为不配与神的属性有关的事物;(b)经文中出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c)面对一段似乎没有意义或互相矛盾的描述。
虽然亚历山大学派的多重意思理论那么盛行,但并没有阻止安提阿学派的学者提出,虽然旧约作者自己可能通过神赐予他的异象预见到他的预言在未来的应验,但该预言在本质上仍与先知那一代所理解的历史意思一致。[22]因着强调经文的单一意思,安提阿学派树立了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并在过分执着于字面意思的伊便尼派(Ebionite)与私自寓意化的希腊哲学、诺斯底派(Gnostics)和亚历山大学派之间走了一条微妙的道路引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3. 中世纪时期
公元600-1500年间漫长的时期中,解经的主要人物是来自巴黎圣维克多修道院(Abbey of St. Victor)的维克多派(Victorines)。[23]圣维克托的休格(Hugh of St. Victor,1096?-1141)仍然使用三重寓意原则解释圣经。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也因强调字面意思而与众不同。休格认为,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经文文本的意思,因此,他为杰出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铺平了道路。
到了公元12世纪,休格的学生,圣维克托的安得烈(Andrew of St. Victor)进一步强调字面意思,不过他对有争议的经文还是用二重解经法——他一面用武加大译本(Vulgate)给出基督徒的解释,一面又本着希伯来经文给出犹太人的解释。这样,如以赛亚书7:14,就既有犹太人的解释,又有基督徒的解释。
这段时期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是坎特伯雷的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斯蒂芬·兰顿(Stephen Langton,1150-1228)。他最为我们熟悉的成就,就是把圣经分成现有的章节。另有一点也值得注意,他强调所有的解释都要符合基督教信仰的必要性。只是很可惜,他虽然认为灵意解释应该基于经文的字面文本,但还是像许多早期教父一样,倾向于自由地使用这一原则。
这时期真正的代表是托马斯·阿奎那。他对两方面作了明确的区分:虽然紧紧相关,但价值不同。[24]他主张,圣灵在一些经文中清楚地对我们说话,因为圣灵的信息很容易从自然的或字面的意思上看出来。通过按字面意思解释这些话语,神学家确立了他的结论和神学。
但是圣经也有象征的意思,其原因有二:一是,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象征意思,天上的事物是不能以地上的词汇解释的;二是,以色列的历史是由那位掌管历史的主宰者所安排的,神能够将一些与新约有关的事物放在其中。这样看来,阿奎那虽然已经开始痛饮新的水流,也就是说,经文文本的字面意思是一切坚实教导的根基,但他显然还难以摆脱旧式的“相称教义”(doctrine of correspondences)。
吕拉的尼古拉(Nicholas of Lyra,1270-1340?)是同时期的一位犹太信徒,他开始把字面意思推举为唯一合理的解经根基。他在解经史中的角色之重要,可以从这句名言看出:“如果吕拉没有吹笛,路德就不会跳舞。”
4. 宗教改革时期
在强调要回到圣经原文的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约翰·罗伊希林(Johann Reuchlin)的希伯来文文法与字典和伊拉斯谟(Erasmus)的希腊文新约第一修订版(公元1516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为路德和加尔文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伊拉斯谟受到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1467-1519)的影响,将新的人文主义对历史和语言学方法的重视应用于圣经。当科利特从意大利回到英国讲授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时,他充满了这个新观念,并完全拒绝了经院派寓意、奥秘的解经方式。公元1498年,伊拉斯谟参加了他的讲座,以后的事就都成了历史。
路德曾明确地(他的思想是否有所隐藏?)肯定经文的单一意思是解经的唯一正确基础,这标志着解经的又一个新的推动力。他对寓意法的评论既清晰又有力,他以特有的口吻说:“奥利金的寓意法一文不值!”因为“寓意法只是空想……是圣经的渣滓。”“寓意法真是笨拙、荒唐、无稽、老旧、胡闹。”他认为这种方法“不过流于猴戏”。“寓意法好比一个美丽的妓女,对懒惰的人特别能显出诱惑力。”[25]对路德而言,“圣灵是天上地下最单纯的作者,圣灵的话不会多于一个最简单的意思,这就是我们所说圣经的或字面的意思”。[26]
加尔文对寓意法的意见同样毫不留情,他在加拉太书4:21-26的注释中曾指责每一个将寓意解释或多重意思加给经文的作法为“撒但的诡计”。他又在“罗马书注释”中列入他写给朋友的一封献词信,说道:“既然他〔解释者〕唯一的工作就是表达他所解释之作者的思想,那么他一旦带领读者偏离了作者的意思,他就是失职,至少是偏离……无所顾忌地改换经义的意思,像是在玩游戏一般,这是一种僭越、亵渎的行为。而许多学者竟都曾做过这事。”[27]
从基督纪元前开始,支持和反对寓意化的潮流就一直此起彼落,而加尔文和路德则比其他人更有力地扭转了解经的趋势。这并不是说他们自己在实践自己的原则时总是成功,而是说他们为教会制定了一条路线,这条路线为后来的解经指明了方向。
5. 宗教改革后
在解经史上,公元17世纪有两个很重要的运动:敬虔主义(Pietism)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
敬虔主义本身就是对缺乏个人信仰经历的制度主义和教义教条主义的一种抗议,它最推崇的是个人悔改的经历和各种实际的敬虔行动。虽然我们可以列出像斯彭内尔(Philipp Jacob Spener,又译“施本尔”)和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又译“富朗开”)这样的领袖,但从我们的解经学角度来看,最有价值的贡献者是约翰·本格尔(1687-1752),他是第一个把新约希腊文抄本依照各种相似点加以分类的人。他著名的注释书《新约之晷》(Gnomon of the New Testament,1742)汇集了历史字根、修辞格解释(附录中收集了大约一百个修辞格和相关词汇解释表)和实际应用的建议,堪称典范。[28]
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发源于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而神学上的理性主义可以更直接地追溯到三位杰出的源头:克里斯蒂安·冯·沃尔夫(Christian von Wolff,1679-1754)、赫尔曼·塞缪尔·赖马鲁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1694-1768)和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沃尔夫试图将圣经启示与自然启示联系起来。接下来,赖马鲁斯则是想把自然启示当作基督信仰的全部来源;由于他无法协调信仰和理性,因此就拒绝接受特别启示的观念。莱辛则认为历史上偶有的事实,不能用来证明理性所要求的真理。[29]这些人也可以算是后来自由神学内容的根源,包括19世纪极具破坏性的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
到了18世纪,这两个运动仍然持续着;其中敬虔主义的影响较为明显,主要通过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的一生和讲道。卫斯理的复兴呼召人回转归向神,归回到对神话语的个人研习和集体硏究。
但潜在的抗议浪潮再次爆发,这次体现在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施莱尔马赫的著作中。康德试图在他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思想中——即他认为“你应该”存在于每个人的灵魂中——建立关于神的证据和认识神的方法;施莱尔马赫则强调Gefühl(人类的情感)是人对神意识的所在。宗教的来源不是一本书、理性或任何其他外在的东西;它主要的来源是这种对自身以外某位存在的终极依赖感。罪只算是这种依赖神之感觉的破坏,并不是对神在书中所启示的旨意和律法的反叛!
阿尔布雷希特·立敕尔(Albrecht Ritschl,1822-1889)同意施莱尔马赫的看法,他不赞成个人信仰是由一个历史事件或一本书启示而来的。立敕尔声称,基督教的根基在于一个价值观,因此他只肯定基督教的道德和伦理价值。
这一条路线到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达到顶峰。他主张回到耶稣的信仰,但不是信仰耶稣,结果他排除了福音书中所有他自认为不恰当地附加其间的希腊化成分。
18世纪和19世纪的基本神学关注,对解经的方法和途径问题并没有帮助。教内教外的学者反而花费更多的时间、心力研究另一个问题:圣经在某一程度上能否成为教会和基督徒的可靠根据和权威。
甚至到了20世纪,仍无法逃脱这可恶可厌的危言耸听式的陷阱,它以更高深的姿态出现,实质上依旧贫乏无果。
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过去25年来圣经评判学的冗杂历史,不过读者至少要了解一点笔者的立场,因为这关乎解经这个主题。
高等批判学(Higher Criticism)的任务不是可有可无的任务,福音派人士不能简单地将其排除在考虑之外,就像非福音派人士不能声称这是他们的特权:删除圣经中他们看似不合口味的教训。事实是,如果我们要作忠实的解经者,并“要充分证明我们的事工”,我们就必须硏究日期、形式、作者、受书者、对应文本和作品来源等问题。
一个好的解经者不应该接受任何形式的未经证实的“假设说法”,这些“说法”先用一文献演绎而“鉴定”,再用同一文献归纳而“证明”,形成了一个最恶性的循环论证,论据和结论都是一样的。但同时“真正的”来源仍旧存在,是必须加以研究的;例如,历代志中明明列出的六七十个文献便是。而且,这并不是高等批判学的全部工作,还有更多。
赫尔曼·贡克尔(Hermann Gunkel,1862-1932)开创了一个叫做“形式批判学”(Form Criticism)的新方法。他的关注点是确定圣经文献的类型和体裁,这些文献是由口传的前文学阶段(oral preliterary stage)和特别的Sitz im Leben(即生活状况,如礼仪、身份、团体等,往往以习俗或类似的模式重复,并呈现出特定的形态或相关样式)发展而来的。
贡克尔最初的观察被改进,并应用于诗篇的硏究(Sigmund Mowinckel,1921-1924)、旧约立约条款的硏究(George E. Mendenhall,1954)和新约的研究,尤其是福音书的研究(Karl Ludwig Schmidt、Martin Dibelius和Rudolf Bultmann)。
我们仍旧不能同意下面的基础假设:圣经的文学形式都有它更原始的形式,原始形式是口传的,与旧约时代以色列或公元1世纪的特殊Sitz有关,这形式不但对文学有影响,而且可以说“控制了它的要义和内容”。这说法真是太缺乏根据了,但是当真实证据存在时(就如公元前一两千年的附庸条约〔Vassal Treaties〕所用的Gatt-tung形式,正与圣经中几个盟约甚至申命记的整个结构相似),我们务必要把它包括在我们的解经中,并据此调整我们的方法。[30]
最后,我们要说到传统批判学(Tradition Criticism)和校勘批判学(Redaction Critism)的新发展。前者着重追溯圣经中口头和书面资料的形成、修改及新综合的历史。这派学者有伊万·恩内尔(Ivan Engnell,1906-1964)、马丁·诺特(1902-1968)和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Albrecht Alt,1883-1956)。校勘批判学则更注重神学原因,研究经文如何取舍、如何安排,以及其材料取用什么样式;其目的在于说明新约作者们的神学重点是如何互不相同的。与校勘批判学有关的主要学者有金特·博恩卡姆(Günther Bornkamm)、汉斯·康策尔曼(Hans Conzelmann)和维利·马克森(Willi Marxsen)。
虽然以上两个学派提供了了解圣经的一些见地,但也都有负面后果,因为他们都倾向于不按照经文自身的内容和主张来解读经文。因此,如果作者(或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编者或校订者)声称自己的立场具有启示性,然而这些学者就先发制人地说他是一位搜集剪辑者,或是摘录风俗轶事的速记员,必然会有某些方面需要作出调整。经文本身的内证必须在这取舍中占主导地位,直到出现独立的或外在的反证。
我们的确相信,有些修正过的校勘批判理论形式可以、也应该用在研经上。因为任何知识,若能根据神学原则帮助我们明白作者对历史材料的取材与布局(当然,如同圣经作者所称,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下),显然能帮助我们根据这些经文讲道。依我们看来,有些神学差异(例如,福音书作者之间的差异)与其说是矛盾的,不如说是互补的;虽然彼此的神学目的可能不同,却因此把圣经结合成一个更完整、更统一的整体。
所以,解经必须尽可能运用所有正当的工具,但需要保持经文的自主性,并假定它的真实性(除非发现反证)。然而,222年来对圣经批判的成果,还是不能取代在这些预备工作之后,遵循解经的严格要求,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回到教会近17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的主要问题上,虽然这问题曾经因为大多数圣经批判研究所引出导论性的争论而被搁置。
因为偏向各类批判硏究而被搁置的解经学(Exegesis),却在释经学(Hermeneutics)的名义下继续,我们也在第一章部分追溯了这个运动。我们接下来所要作的是呼吁恢复较古老的解经方法,包括更广泛地使用严谨的方法,以极其详尽的方式分析作者的文法和句法,为发现那话语中的神学和教导作准备,并为在我们这时代重新传讲它奠定基础。
[1] Otto Kaiser和Werner Georg Kümmel, Exegetical Method :A Student’s Handbook。
[2]低等批判学探讨圣经应当包含那些书卷(正典),原典之内容为何(经文批判学)等问题;高等批判学则探讨著作年代、作者、读者、特殊风格,及文章形式等。
[3]以上各项即凯泽之文章的大纲,而屈梅尔的部分则较为简略。
[4] Victor Paul Furnish, “Some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New Testament Exegesis.”
[5] Anthony C. Thiselton, “Explain, Interpret, Tell, Narrative,”收录于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编者Colin Brown,共三册(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5~1978), 1: 573-584。
[6]例如,见Susan W. Wittig, “A Theory of Multiple Meanings,” Semeia 9 (1977): 75-103; Gerald Downing, “Meanings,” 收录于What About the New Testament? Essays in Honour of Christopher Evans,编者Morna Hooker和Colin Hickling(London: SCM, 1975)127-142页。
[7] Vern S. Poythress, “Analysing a Biblical Text: Some Important Linguistic Distinctions,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32(1979): 113。
[8] W. K. Wimsatt, Jr., The Verbal Icon: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oetry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1954),3-18,19-39页。
[9] Poythress, “Analysing a Biblical Text,” 126页。
[10]同上,137页。
[11] Wittig, “A Theory of Multiple Meanings,” 96-97页。
[12] John Sandys-Wunsch,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3(1977): 66-74。所引之词见67页。
[13] “释义圈”指经文与产生经文的人类心理以及解释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会使经文与解释结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见Richard N. Soulen, Handbook of Biblical Criticism (Atlanta: John Knox, 1976),75页。
[14] Edward Haller, “On the Interpretive Task.”此文原名“Ad Virtutes Exegendi”(“On the Virtues of Exegesis”)收录于Evan gelische Theologie 25 (1965) :388-395。
[15]参考下列佳作:Bernard Rosensweig, “The Hermeneutic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J. Weingreen, “The Rabbin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Brevard S. Childs, “Midrash and the Old Testament,”收录于Understanding the Sacred Text: Essays in Honor of Morton S. Enslin on the Hebrew Bible and Ckristian Beginnings,编者John Reumann (Valley Forge, Pa.: Judson, 1972),45-59页; Richard Longenecker, Biblical Exegesis in the Apostolie Perio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5),32-45页。
[16] E. Earle Ellis, “How the New Testament Uses the Old,”收录于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Essays on Principles and Methods,编者I. Howard Marshall,199-219页;以及D. Moody Smith, Jr., “The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New,”收录于The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New and Other Essays: Studies in Honor of William Franklin Stinespring,编者Jamps M. Efri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编者James M. Efird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1972) 3-65页。另参Frederic Gardiner,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in Their Multual Relations (New York: Pott, 1885),310-331页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17]关于此点更详细的讨论,见Walter C. Kaiser, Jr., “The Current Crisis in the Exegesis and the Apostolic Use of Deuteronomy 25:4 in 1 Corinthians 9:8-10,”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21 (1978) : 3-18。另见Robert J. Kepple, “An Analysis of Antiochene Exegesis of Galatians 4:24-26,”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39 (1976-77) : 239-249。
[18]见Walter C. Kaiser, Jr., “Leviticus 18:5 and Paul: ‘Do This and You Shall Live (Eternally ? ),’ ”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14 (1971) : 19-28。
[19]见Walter C. Kaiser, Jr., “The Weightier and Lighter Mattiers of the Law: Moses, Jesus, and Paul,” 收录于Current Issues in Biblical and Patristic Interpretation: Studies in Honor of Merrill C. Tenney Presented by His Former Students, 编者Gerald F. Hawthorn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5), 176-192页。
[20]见Gary V. Smith, “Paul’s Use of Psalm 68:18 in Ephesians 4:8,”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18 (1975) : 181-189。
[21]见James N. S. Alexand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in the Ante-Nicene Period: A Brief Conspectus,” Interpretation 12 (1958): 272-280; Allan E. Johnson, “The Methods and Presuppositions of Patristic Exegesis in the Formation of Christian Personality,” Dialog 16 (1977): 186-190。
[22]见A. Vaccari, “La Theoria Nella Scuola Esegetica di Antiochia,” Biblica 1 (1920) : 3-36。
[23]“论中世纪的解经学”(On exegesis in the Middle Ages),见Beryl Smalley, The Study of the Bible in the Middle Ages (Notre Dame, Ind.: Uni versity of Notre Dame, 1964); Ceslaus Spicq, Esquisse d’une Historic de L’exēgēse Latine au Moyen âge (Paris: Vrin, 1944); Robert E. McNally, The Bibl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Woodstock Papers: Occasional Essays for Theology, 4 (Westminster, Md.: Newman, 1959)。
[24]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l 1 a. 1.10; Quaestiones Quodlibetales 7. 14-16。
[25]见Martin Luther, Lectures on Genesis, 收录于Luther’s Works, 1-3册,编者Jaroslav Pelikan (St. Louis: Concordia, 1958-1961), Comments on Genesis 3, 15, 20。
[26]引用Frederic W. Farrar,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 Bampton Lectures, 1885 (Grand Rapids: Baker, 1961), 329页。
[27] John Calvin,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Paul to the Galatians and Ephesians, 译者William Pringle (Edinburgh: Calvin Translation Society, 1854), 135页;同作者,The Epistles of Paul the Apostle to the Roman and to the Thessalonians, 译者Ross Mackenzie, Calvin’s Commentaries, 编者David W. Torrance和Thomas F. Torranc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1), 1, 4页。
[28] John Albert Bengel, Gnomon of the New Testament, 译者Andrew R. Fausset, 共五册 (Edinburgh: Clark, 1857-1858)。
[29]有一个很好的分析,见Geoffrey W. Bromiley, “History and Truth: A Study of the Axiom of Lessing,” Evangelical Quarterly 18 (1946): 191-198。
[30]与研究旧约有关之数点讨论,见Walter C. Kaiser, Jr., “The Present State of Old Testament Studies,”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18 (1975): 78。此处采用了O. T. Allis, Meredith G. Kline, Kenneth Kitchen和Herbert W. Wolf形式批判研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