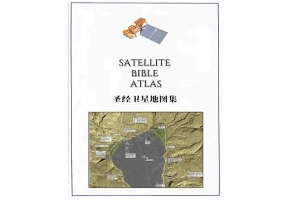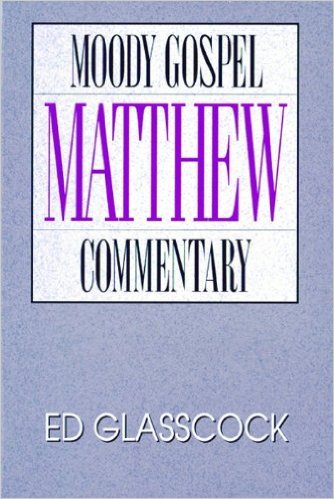第一章 解经神学在当前的危机
对于一代几乎每天穷于应付各样危机的人们来说,向他们宣布“解经神学”的危机,并不会让人感到震惊。我们已经被警告过关于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上的危机,以及对圣经内容无知等等的危机,[1]但我们不得不同意兰德斯(George M. Landes)教授的主张:“圣经硏究的最基本危机”[2]必然出在解经上。在很多方面,其他神学危机的根源都在这里。
一、解经神学的危机
大部分神学院或培训机构在解经课程中所列出的步骤,与大部分牧师每周实际准备讲章面临的实际困境之间,总是存在着鸿沟,这正是危机所在。神学课程中最令学生头痛和无助的是,(如何)将了解圣经的原意与,传讲切合时代需要的信息,使人们生发信心、生命和忠诚,这两方面联系起来。其实,这两方面在不同时期都有详细甚至全面的研究:一方面是对经文的历史、文法、文化和批判性分析;另一方面是实践神学、崇拜学、讲道学、教牧学(加上演说、组织、辩证等)运用在所有场合的讲道大纲合集。但是,谁能制定出沟通这两者的途径呢?[3]那些既忠于经文原意,又能喂养现代人灵命的书籍或专文,其数量非常少,也隐藏在多数人所不熟悉的期刊或语言中,因而对我们今天的需要几乎没有帮助。就我所知,在英语或任何现代欧洲语言的背景下,没有人写出我所谓的“解经学”论著,描绘出这条从经文的研习到经文的宣讲的最困难的路线。
显然,教会中“默想式”或“专题式”的讲道太多了,却又经常与经文的短语、从句、句子、经节等缺乏关联,或是根本不相配合。目前急需一些书籍或专属文章,能教导人们严格地按圣经目前正典形式的合法单元(例如,一段或一大段)分析经文,教导在职或未来的传道人如何从经文转化为讲章,同时,既不忽视经文原意又能满足现代人对生命之道的渴慕。
有些讲道虽然号称能够针对时代的问题、需要和诉求,却常常显出主观性的弱点。在许多讲员手中,圣经经文在澄清现代人的问题并提供解决之道方面都没有真正的帮助。听众往往不确定所宣讲的盼望之言是否就是圣经对现况的提示,因为圣经经文往往只不过是讲道信息里的标语或一再重复的话。这情况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事:讲章必须出于忠实的解经,并且必须紧贴着经文原意。这是所有希望讲道既合圣经又切合实际之人必须牢记在心的。
一再目睹这种错误方法,尤其在专题式讲道中看到,笔者对此深恶痛绝,因此笔者多年来一直叮嘱学生,每五年才能有一次专题讲道,讲完后还得立刻悔改,求神赦免。读者若对此感到不解,且听我慢慢道来。然而,这句戏言背后的严肃之意,乃在大声呼唤全然符合圣经的讲道:从出发点,到预备,再到传讲,都让神的话语来指引。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同样很快承认,最能打击、摧残会众心灵的,莫过于枯燥沉闷地叙述显然与当下毫不相干的圣经章节。牧师传讲这样信息,正反映出他在神学院所上的解经课程,是把人带进历史、语言学和批评学的迷宫,使人迷惘失措,以至于经文在听众面前了无生机。这种信息是如此集中于细节的描述,以至于它基本上仍然是公元前或公元1世纪的用词,与20世纪人们的兴趣和需要毫无关联。
现在困难来了。一种方法的长处,往往正是另一种方法的短处,两种方法都暴露出严重的问题。悲剧在于,这种情形往往是造成当今神话语饥荒的主要原因;而现代的许多观察者认为,神的话语在神的子民中继续存在。大批美国信徒不断地涌到各处,参加硏讨会、圣经会议、教会或家庭的查经班,希望借此满足心灵的饥渴;然而他们的收获往往大同小异:重复安排信仰的基础真理,不断讲些受当地民众欢迎的高谈阔论,或讲些漫无边际的专题、诙谐机灵的信息,也许还点缀着讨喜的幽默轶事,以便迎合那些灵里懒惰、只想听故事和笑话以自娱之人的口味,如此而已。传道中的预言性信息何在?曾经与神话语相关的权柄和使命感何在?
谈到圣经讲道的衰退,对其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圣经的解经原则。当然,原则教学生学会了分析动词,断定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的文法形式,流畅地译出经文,根据高等批判学(Higher Criticism)和低等批判学(Lower Criticism)的合理标准,从历史和批判的角度分析相应的经文。但这就是它的全部工作吗?
我们认为,解经的原则本应该指出由分析经文到传讲经文的路线,但传统太严格地限制了它的范围。结果,“解经神学”成了牧师在讲台事工中最先抛弃的一门课程,因为他们发觉这门课程(正是大多数神学课程所教的)太死板、枯燥、与现代的需要无关,因而是多余的。当然,我们不是以实用与否来断定真理,但这说明“解经神学”在神学课程中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它所强加的狭窄和限制,没能够服侍教会的需要。
为此,我们不得不强烈认同兰德斯对这问题的分析。他认为“神学院的圣经教师若只根据历史背景来解释圣经,那就真是全然辜负了圣经文献。虽然他必须从历史入门,但如果他没有进一步阐明其中的神学,及其持续至今的神学意义,他不仅忽视了神保留经文的一个重要用意,也忽视了经文的角色和功能……”[4]
斯马特(James D. Smart)教授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1970年出版的《圣经在教会中出奇的沉默》(The Strange Silence of the Bible in the Church)一书中说:“传道人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神学院中圣经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的脱节所造成的。”[5]他还说,“虽然神学院中的圣经课程正确地教导了学生如何仔细辨认经文初写时的原意,但往往又假定学生在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教导、协助或延伸的方法论下,就能毫无困难地从原意过渡到现代含义。”[6]
讲道集和讲道大纲等书籍,仅仅指出最后的结果,并没有指出讲章自开始解经到完成的路线。许多人感到这些步骤是缺失的要素,然而谁该标示出这条路线呢?是圣经系的解经神学,还是讲道系的实践神学和教牧学?
其实,这两个系都有责任去填补这种脱节,但若确定预备讲道用的经文是谁的基本和首要责任,那么我们相信圣经系的解经神学必须主动发展解经方法的延伸,使解释者能安全自信地从圣经作者的原意过渡到该文本对现代听众的现代意义上,其实这就是解经的延续和扩展。在讲道中,研经的所有基本准备工作——包括具体说明经文的中心或焦点,经文的神学依据,经文的历史、文化、神学的背景,以及经文的应用等——都要以最简明扼要的形式呈现出来。此外,讲道不只要反映出解经的成果,也要根据它要解析的经文,评定它所宣讲的内容和重点是否正确。只有解经技巧和讲道的艺术是不够的。实际上,宣讲者本人必须集解经神学教授和实践神学讲道家于一身。是否曾经或在将来会在课堂上塑造这样的人,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现在要加紧做的。
因此,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已经在牧会的人和那些每周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但我们主要的对象必须是就读于神学院和圣经学院的学生。正是为这些学生和他们的教授,我们才敢于开拓新视野,踏足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特别意识到在尝试(建立)解经神学时的不完整性和内在陷阱。
然而,愿本书终能成为初熟果子的奉献,献给全地教会。笔者由衷地希望更多人能借此与笔者对话,叫我们能同心协力地完成圣经和神学教育的一个中心目标。我们容忍平庸的讲道和解经已经太久了,现在要么就开始用好的解经神学来纠正这种情况,并相应地宣布从解经到讲道的一系列有效步骤;要么去除我们圣经和神学系的所有专业假冒,只提供以研究为导向的学位,从而填充学术界的教学和写作职位。目前有一种运动已经在暗中发起,我称之为“家庭神学院”(House seminary,由几个当地教会提供2到3年的学习和实习机会,一次招收2到20个学生,由各教会的全职同工负责教导)。这些“家庭神学院”之所以产生,常常是因为不满于神学院对这些课程缺乏专业的整合。他们也很少反对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要求,相反,他们几乎总是要求至少要学希腊文,往往两样都要学;但他们大部分的心力是,将语言研究与发展通常被称为“准确解经式”或“经文式”的讲道联系起来。可惜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现有的神学院一样,也在努力解开这纠缠在一起的结。因着我们在基督里与许多“家庭神学院”的情感和交通,我们也把这成果交给他们检验和指教。
二、解经原则的危机
讽刺的是,正当我们这一代开始面对解经与讲道的脱节时,一般解释原则(hermeneutics,释经学)的整个范畴也突然出现巨大的震荡,以至于老教条已经不能再被轻易地视为理所当然。然而,仔细考察后就不难发现,就连这场危机也与上文所提解经神学(Exegetical Theology)的根本危机不无关系,因为争议的核心仍是解释者如何连接“经文在历史背景下的意思”和“该经文对我的意思”。如此看来,这无疑是所有解经者都要面对的问题,而并不仅仅是圣经解释者的问题。
1. 经文单一的意思
坦白地说,问题就在这里:经文的意思是单指圣经作者使用字句时所赋予的“字面”意思,还是也应考虑经文对读者和解释者的“现在”意思?这是现代的一大难题,也是决定圣经权威的关键所在。以下略述各学者的看法。
(1)威廉·艾姆斯的观点
讨论释经学最好也从威廉•艾姆斯(William Ames,1576-1633)开始,因为哈佛大学自从17世纪创校以来,就以他的书为标准课本。在艾姆斯时代,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清楚明了的。他说:“……圣经的每一处经文只有一个意思,否则该经文的意思不仅含糊、混乱,而且根本就没有意思,因为任何经文若不是单指着一个意思,就肯定没有任何意思。”[7]
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了结,这个单一的意思是否也包括经文对同时代人的应用,或者将该含义引申到其部分介绍的主题?近代人对此的争论,在18世纪约翰·埃内斯蒂(Johann August Ernesti,1707-1781)与约翰·塞姆勒(Johann Salomo Semler,1725-1791)的争论中已经反映出来。汉斯·弗莱(Hans W. Frei)[8]巧妙地总结为:埃内斯蒂认为,解经(当然是用来判断经文意思的)包括:(a)发掘字词的用法;(b)发掘支配此用法的历史背景;(c)发掘严格受其用词制约的作者意图。
(2)约翰·埃内斯蒂的观点
对埃内斯蒂而言,解经的范围只限于作者的用词,并且与作者使用的词完全相同;而神学解释和经文应用,则只能严格依赖于经文预先决定的意思。[9]
埃内斯蒂的主要论点可以归纳如下所述。
A. 解释的行动:暗指两方面,即正确地理解词的意思,合理地解释该意思。[10]
B. 解释的艺术:教授他人语言意思的艺术或能力,使我们能够将原作者的语言以同样的意思赋予另一种语言。[11]
C. 解释的技巧:这是通过表达作者的意思来体现的,包括用比作者更易懂的同一语言的文字,或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并通过论证说明来解释。[12]
D. 释经学的定义:释经学是一门科学,为要教导我们以正确、周密的态度寻得作者的意思,并合理地向人解释。[13]
E. 单一意思理论:虽然一个词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意思,但同一个词因着用法不同就逐渐衍生出多种意思……要得知每一个情况下的意思,方法是:(a)一般说法,即常用法;(b)临近的字词或上下文。[14]
F. 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将一个词赋予多种意思的错误:这种看法应当加以否定,虽然它沿习已久,奥古斯丁(Augustine,见《忏悔录》〔Confess〕Ⅻ.30, 31)即持此见。但这种性质的解经必然会给解经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没有比这危害更大的。[15]
G.主张圣经的每一处字词都具有它所有可能的意思之错误:这个偏差起源于拉比学派(Rabbinical schools),并在教会早期从他们传给了基督徒……[16]
H.文法含义(Grammatical Sense)是唯一正确的意思:那些把一种意思理解为文法意思,另一种理解为逻辑意思(Logical Sense)的人,并不理解文法意思的全部含义。因此,我们不该求得那在本质或意思上可能随着学科、对象而改变的意思,因为如果真有这种词意,字词就会因诸多对象而有许多意思了。[17]
I.所有非语言学的解释都不可靠:不仅如此,从事物中收集词语的意思,这种方法纯属错误。因为我们认知事物的方法是适切地解释词语的意思。只有靠着圣灵的话,我们才能明白当如何思考事物。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lipp Melanchthon)说得好:除非先从文法上理解圣经,否则无法从神学上理解圣经。路德也曾断言,对经文意思的明确认识,完全取决于对文字的认识。[18]
J.主题、教义、应用和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绝不能操纵解释:根据文法原则,圣经中的每一个词都应该被赋予意义,因此不能基于事物的缘由或先入为主的观点就拒绝该意义。因为一旦如此,解经就变得不确定了。[19]
(3)约翰·塞姆勒的观点
塞姆勒却着重于考虑经文字词所要表达的一般主题。后来他赢得了胜利,因为大多数人都随从了他。塞姆勒的看法是:“简单地说,释经学最重要的技巧取决于:(a)能准确、正确地认识圣经对语言的使用,能区分和表达圣经经文的历史环境;(b)在时过境迁的今天,能以我们同代人可接受的方式讲述这些事物。……释经学的其他方面都可以归结为这两件事。”[20]
除了塞姆勒先发制人的负面历史批评外——他断定公元1世纪历史中的超然因素是不可能的(单从他的方法论来看,笔者就不予接受)——显然,他早在1760年就在上述的步骤(b)中将填补现代解经者面对的脱节的任务加给了释经学(hermeneutics)。然而,他没有将这一步与作者的词语和真正用意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我们当赞同埃内斯蒂,他说:“只有靠着圣灵的‘话’(Words),我们才能明白当如何思考事物。”[21]当然,塞姆勒也表示需要了解文法和经文。但就如弗莱所说,文法和经文“只是年代和步骤上的问题”[22]。实际上,字词在塞姆勒看来某种程度上是死板枯燥的,人们只有掌握了该字词所表达的主题,才能以此为基础理解该字词。
(4)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的观点
埃内斯蒂和艾姆斯可算是早期学者的代表,他们都确信经文可以直接领受。埃内斯蒂认为,解经包括两部分:一是,理解的技巧,即理解的正确性;二是,解释的技巧,即解释的准确性。用现代的话说,埃内斯蒂主张,使用文法分析来获得(a)“作者所用字词的单一意思”的释经步骤,不应该脱离(b)“应用该意思或指明其意义”的过程。[23]
但是,在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1768-1834)的思想中,这两部分被分开了。“释经学”(Hermeneutics)专指前一个部分,只涉及文法和句子结构。埃内斯蒂主张,每个词只有一个“涵义”(Sinn,sensus),但可以在不同的“意义”(Bedeu-tungen,significationes)中展开;施莱尔马赫则以为,在文法上领会作者的用词(即,理解的技巧),必须与“心理的”或“技术的”(Technical)解释区别开来。[24]他向我们确认,文法解释只关注解释的客观层面,而“技术的”解释则应对主观层面。因此,文法解释永远不可能成为所有人、所有时代的普遍原则与意义的根源。它有一个纯粹的“负面作用”,那就是它只“划定界限”;[25]至于“技术的和心理的”解释(即埃内斯蒂所谓“解释的技巧”),则还需要额外的步骤,那就是,通过确定或尝试重构作者的“心理过程”,来亲自融会贯通该主题——但这根本不可能办到)。
简而言之,施莱尔马赫对语言的整体概念,与埃内斯蒂正好相反。这一差别是最关键的。埃内斯蒂主张作者的用词只有一个意思,虽然可以有不同的意义或应用,却仍须反映出这个单一的意思;施莱尔马赫则认为,每个词都有一个一般范围的意思,这个一般范围意思不是根据其本身的意思,而是出自于经文原典的语言对经文的影响,及作者和读者对它共同的认知。[26]
(5)汉斯·伽达默尔的观点
许多人觉得,施莱尔马赫在晚年亦逐渐强调“技术和心理的”解释。其后,接续这思想的有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和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汉斯•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1900-2002)继而将这一传统思路加以扩展,编纂成了现今神学界一般所称的“新释经学”(New Hermeneutic)。[27]
在伽达默尔那里,艾姆斯和埃内斯蒂的释经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伽达默尔思想最完整的表述出现在1960年。[28]在他看来,我们不仅不可能了解作者的意思,也不能把经文现在的意思与其曾经对作者的意思联系起来;相反,经文的意思在于其主题,即经文所阐释的事,与作者和读者都没有关系,又可以说都有关系。所以,经文的意思“总会”超越作者的原意,它真正的意思并无止境,可任由无数释义者讲解。因此,一旦有两位解经者在同一时间得出彼此冲突的解释,并不存在衡量孰是孰非的标准,在这种可悲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确认对它的解释,无论是作者及其用词,还是至经文过去的意思,都不能确认。
为了摆脱这一完全不可接受的状况,伽达默尔沿用传统观念,提出一个方法,将一段经文过去各种不同的解释融合为一体。但这个传统作法并没有任何可以诉诸的东西,因为它没有任何规范律例,也没有能力验证。怎么办呢?正如小艾瑞克·唐纳德·赫希(Eric Donald Hirsch,Jr.)的尖刻批评,伽达默尔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反而把自己陷在一些关于文本中的书面标记的自相矛盾中,这些存在的书面标记既可重复,又不可重复。[29]分析到最后,“解释”仍旧是经文原有看法与解释者个人意见的融合体,伽达默尔称之为“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
对于我们的圣经文本研究来说,伽达默尔和新释经学派,以及与这学派有相当关系的人,他们的一个有意思的方面在于,作为解经过程中一个重要步骤的应用(应用的技巧),终于获得了应有的重视,但是,作者用词的原意(应用的根基)却被忽略了,结果解经的过程被宣告为循环论证(释经循环,hermeneutical circle),而非线性。虽然我们确信这种循环不是恶性的,但通常的观点是解释者的文化、信念(本体论)和硏究方法对经文的影响,跟经文对他的影响是一样大的。
(6)埃米利奥·贝蒂(Emilio Betti)和小赫希的观点
如果伽达默尔算是释经学界海德格尔派(Heideggerian version)后期最杰出的代表,那么埃米利奥·贝蒂(Emilio Betti)和小赫希几乎是唯一一批致力于将释经学和解经回归到更客观的解释方式的人。的确,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更不必说布尔特曼[30]和他的两个学生格哈德·艾伯林〔Gerhard Ebeling〕和恩斯特·富克斯〔Ernst Fuchs〕)先是否定客观历史知识的可能性,结果是把过去知识的完整性推到相对主义(Relativism)和主观主义(Subjectivism)的大海中(这派学者本身也经常抱怨这点,却从未完全脱离,而仍不断尝试搜集更多的证据支持他们所声称的)。
贝蒂是意大利的一位法律史专家,他担心“现代德国(对我们而言是西方世界)忘记”他称为“古老庄严式的释经”,就大胆地提倡恢复。他写作论著,以抵制多数德国学者对“意义赋予(Sinngebung)的偏执(解释者将“意义赋予”所解释的内容),以及把这种意义看作原著的解释的错误观念,[31]区分“解释”(Auslegung)和“意义赋予”是至关重要的。
这正是维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英文教授小赫希在1967年所提出的看法。[32]我们必须指出“意思”(Meaning)和“意义”(Significance)的重要区别:“意思”是指文本、文法和作者的真实用意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意义”则只表示该意思与其他人物、时间、状况或概念“之间”的关系(“意思”与这些密不可分)。依据小赫希的意见(笔者的看法亦同),一旦圣经作者选用了一个词,它的“意思”就不会改变;“意义”则不但会改变,而且必须改变,因为人的兴趣、问题和解释者生存的时代都不断改变。但是,作者原有意思是“不能”改变的,连作者本人也不能改变它!如果作者后来修改了他的观点或者完全改变了他的观点,他必须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即否定、摒弃他以前的观点,否则这些就正是他现在意思的反证。[33]
贝蒂也承认,在解释的过程中,解释者确实涉及到他的主观看法,但如果这个主观看法没有渗入意思之中(这主观看法与解释者的风格、观念、用词和疑问有别,并无关联),解释者就成功了,他顶多是在他以为是该解释的经文中提出个人的意见和喜好(主观部分)罢了。贝蒂的意见并不认可布尔特曼的看法,因为贝蒂不断抨击所有存在主义者,称他们否认了获得任何关于过去的真实、客观知识的可能性。
伽达默尔曾坚持认为所有解释都包含了当下的应用。贝蒂则认为,此话运用于法律上属实(我们也可以说适用于圣经解经),但可惜他认为这不适用于历史。此外,由于贝蒂和小赫希将他们的“意义赋予”(Sinngebung)或“意义”建立在经文已知的文法意思上,即使对关于应用的必要性似乎达成了一致,实际上并没有达成一致。
小赫希的看法受到一些学者的反驳和尖锐的批评,试图推翻他的主要论点——经文的意思正是作者借他的用词所要表达的意思。通常,这些批评的本质是经文意思独立于作者的意思之外。这些批评包括:(a)小赫希未能建立并给出一套检验经文正确性的可能性依据和标准内容;[34](b)他对意思所下的定义前后不一致;[35](c)他不加批评地采用亚里斯多德(Aristotelian)的定义,这种定义并不是如他希想的那样机械地区分意思和意义,而是用一种变相的批判,在理解经文之后才区分(经文意思和意义的区别)。[36]
我们认为,小赫希确实给出了一个检验经文意思有效性的标准: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经文的意思。当然,巴里·威尔逊(Barrie A. Wilson)和大多数现代学者都不接受这种说法。有一点在此值得一提:我们有必要对小赫希的观点加以完善。小赫希坚持不在经文中找意思,然而我们应当谨慎地提出,经文既然表达了作者的真实意图,经文对他就仍是重要的。为此,小赫希确实把意思和经文联系起来,只不过认为经文的意思是次要的,而作者的意图是主要的而已。但小赫希不愿把“意思”和作者的“经文”完全联系起来,这使他很容易受到使用“偏向准则”(Preferential criteria)的指控。
我们曾在别处试图发展另一论点,建基于神把他自己的形像赐给人,使人有交通的能力和理解交通的能力。[37]解释的一般法则似乎不是正式学到的,也不是人凭空发明或发现的;相反,这些法则表现出按神的形像所造之人天性的一部分。自从神在伊甸园中与亚当交谈起,说话和理解的艺术至今仍一直使用着,所以当幼儿牙牙学语时,无论是否正式知道解释法则(显然不知道!),就都已经在立即进行解释了。
我们觉得,小赫希思想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没有深入探讨经文在现代的应用和意义的难题。我们不同意理查德·帕尔默(Richard E. Palmer)对他的批评,以为小赫希对意思和意义的划分,既无正当理由,也只是解释工作完成后的虚假的回顾性批判。若小赫希有什么错,乃是错在他与施莱尔马赫一样,实际上已经把解释局限于知性的“理解行为”。然而,不断改变的意义(大概是实用性)只有在它们参与了由文法、句法所得之作者意图的不变且可证的单一意思时,才能被接纳在解释中。
那么,解释者从这些经文中所得的“意义赋予”(Sinngebung,贝蒂)或“意义”(significance,小赫希)的权威地位是什么?就我所知,这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这当然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许多解释者开始摸索时都会问的:作为解释者,我们能否比作者更了解他自己?
2. 解释者所谓的多重“意思”
解决这难题的一个办法,就是依靠这样一句说法:“解释者常常能比作者自己更了解作者。”[38]此说法所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思想中有一种层次,狄尔泰(Dilthey)称之为“作品的内在形式”,在创作过程中超越了作者的意识,但如今留给解释者去发现。
但是,我们说到“更了解作者”,这是指什么呢?最好按照奥托·弗里德里希·博尔诺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的意见,不要包括作者的心理体验,而单指对他文字的认识。如此,以上说法中的“作者”一词,应当被理解为他们的“作品”。
博尔诺夫首先巧妙地问,我们是否能“跟作者一样”了解他本人?然后才问“对作品的了解能否超过作者”。如果“了解”仅指能说明各事件自然而固有的逻辑,[39]那么它就可以比喻成我们掌握一个数学公式内在连贯性的方法。博尔诺夫找到了另一个同样过程的例证,即从人类行为、工具或机器的工作部件推断出手段与目的拟合关系。我们若把“了解”看成这样的一个内在逻辑,就可以说“了解”包含“完整性”(Completeness)和“结论性”(Conclusiveness),不容许在“了解”本身的内容以外还有概略或进深的情形。[40]这里的“结论性”是指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完成、定型,所有要表达的事物都有了完备的定义。“了解”是可能得到确定知识的条件。因此,当作者用简洁、明显的方法表达自己后,经文就有可能被了解。一旦满足了这些条件,博尔诺夫说:“就可能像作者一样地了解经文了。”
但是,说到比作者“更了解”他的作品,又是如何呢?博尔诺夫承认,即使有“全然总结性”(Total Conclusiveness)或我们所说“全盘了解”,也是很少的。我们只把这特权留给神。所以我们可以说,由于我们具有这样两种潜力,即能完成未完的主题[41],并且能澄清不证自明的背景、假设、基本概念和指引性信念,因此我们可以说“更了解”是可能的。[42]但是,限度还是有的。博尔诺夫认为,“更了解”的观念不能延伸到产生新的意思,[43]只能说进一步充实同一主题,找出隐含的预设、基本概念和指引性信念,或者(这一点博尔诺夫未提及)能指出作品对另一时期或文化中的人们所具有的意义。
如此,这种“更了解”就与作者的意思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若要用这个“了解”来改良或评断作者的作品,就需要先了解作者所说的,而后区分出那不影响意思的“更了解”。这样,我们就很难说“了解”是决定经文的现代适用范围、应用和意义的方法了。
解释的行为反倒必须依照小赫希的路线。“意义”必须是次要而主观的判断,只有在已经正确判断作者在经文中的单一意思之后,才具有合理性;在这意思的基础上,解释者和读者可以提出他们的问题、批评或现代的类似建议。
三、讲道学的危机
在提出我们的一些解决方案以先,我们还要面对一个危机:讲台的危机。大部分基督教会中都存在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圣经讲解在现代讲道中已经成为失落的艺术,其中最被忽略的是旧约部分,而旧约却拥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属天启示!
这情形部分要归咎于马西昂(Marcion,又译“马吉安”)、尤里乌斯·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及其他众多的人。然而,忽略旧约的所有理由(收集起来必定是一大串),我们只看一件事:旧约历史的独特性。旧约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话语,都是在特定时间、状况中,对特定文化下的特定听众说的,这才是真正的难处。不但旧约,连新约的对象和时间也是特定的,基督徒解经者如何去面对这些篇章?难题似乎无法避免。
我们同时代的一位学者,劳伦斯·图姆斯(Lawrence E. Toombs),一直尽力尝试越过这个困难,他致力于让每个人都能理解圣经,尤其有益于现代牧师的讲道。他为了使旧约与我们这时代相关,强调在两约的历史事件中,神所接近的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也邀请我们参与其中。[44]图姆斯所指的关键点是我们相同的人性,因此传道人有责任问会众:在这段旧约经文中,有什么人性状况是对我说的?有什么与它类似的现代例子?既然我知道我和那些人一样,又面临相似的处境,那么我能否将那些古代的旧约话语放在上下文的语境中,加以改变并重现于现代事物上?我能将这句话变成一种新形式,成为我今天真正的信息吗?
然而,如伊丽莎白·阿赫特迈耶(Elizabeth Achtemeier)所指出的,图姆斯的建议的困难在于,他没有意识到旧约历史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是多么的具体。毕竟这些话不是对一般人讲的,而是对一群与神有特殊关系、肩负着特殊使命的特殊民众讲的,因而在此产生了对圣经的“冒犯”。[45]
要回答旧约与现代讲道学的相关性问题,需要先解决阿赫特迈耶所提的一个卓越问题:教会与以色列人有何关系?教会在哪些方面与以色列人所得的祝福和审判有份?这问题问得很恰当,要求我们深入研究解经神学和圣经神学,比起图姆斯的类比法,这个问题更有可能给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布尔特曼也试图解决同样的问题,但他的答案与图姆斯不同,他的结论是:神与以色列的交往已经终止,因此具有特定历史的旧约已经不再是神对我们的启示。[46]旧约唯一与我们有关的是一般的道德要求,不是植根于神的启示,而是植根于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冒犯旧约的独特性,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旧约。在布尔特曼手中,旧约变成“非历史性的”,其价值只在于作教导工具,使每一个完全听到的人在生活中“重新实现”(Reactualized),它跟对以色列人所说的毫无关系。结果,它给出了今日的史实和今日的陈述,但这与过去以色列历史事件所说的全然无关。
布尔特曼也承认旧约历史的独特性,并在这个过程中顺服于它对教会规范权柄。旧约只是为福音作准备,而福音也已经转变成一个存在主义的、末世的、非历史的、个人主义的体系。
1952年,学者们在解决圣经特殊性问题上又作了新的尝试。马丁·诺特(Martin Noth)根据以色列人在三个重大节期中将过去带入当时的时代,敦促教会也应当传讲旧约历史,作为教会中的“重新呈现”(Vergegenwärtigung)。借着述说逾越节、除酵节和住棚节,神在过去施恩的作为(如,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奈山颁布律法、在旷野的救助等)每年都会被呈现为现代事件,使人对以色列的神能用爱和服侍来回应。[47]
这一点极为有用。不仅节期被视为仍然适切,同时注意申命记29:10-15也强调“今日”:“今日你们……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作他的子民,他作你的神。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48]
这是圣经中把过去事件应用在当时的时代的一个生动例证,正像教会在分领主餐时所做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
圣经中另有一个将早期历史事件直接应用到后代的例子,就是在引述这些事件时常用“我们”和“你们”等词。申命记6:20-21教导后代,当人问起神所吩咐的律例的意义时,应当这样回答:“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再看申命记26:6-7的告白:“埃及人恶待我们……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
虽然“重新呈现”的方法有这许多确实的好处,但讲道学的危机仍然存在。科内利斯·特里姆(Cornelis Trimp)曾指出,诺特这种“教导性”的应用圣经的方法有些缺点:讲台信息变得有一种特质,也就是说,使历史事件——无论有没有发生(遗憾的是,这派人士常认为没有)——再一次现实化了,这就像天主教徒把基督所献上的身体再实化一般。[49]这样就失去了“唯独圣经”的原则,反而有了一个对圣经的“重新解释”(Re-interpretation)的新传统,它等同于(甚至超过)圣经的书面形式。这种“重新呈现”含有自由的倾向,使信息不受现有文字经文的约束。这样,神所默示的就不再是圣经,而是解释和传讲之人所说的话。
特里姆在继续批评诺特和图姆斯等人看法的同时,又提出另一种看法:“原始听道者和后代之间的历史间隔被神信实的大能所填补。无论是从一段具有时间性的经文中抽取理性或道德上的永恒真理,还是组织起原著所述状况的类比,都是不可能的……主不容许他所启示之话语的意思只局限在最先说话者或最先听话者狭窄的意识范围中;相反的,神在借着以往的工作和话语启示时已经考虑到我们这些末后世代的人。”[50]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如果一个解经者要得出任何有意义的应用,或想具有现代的意义,他也必须面对讲道学的实际问题。
[1]各为:Tom F. Driver, “Review of Langdon Gilkey的Naming the Whirlwind: The Renewal of God Language,” Union Seminary Ouarterly Review 23(1970):361;Brevard S. Childs,Biblical Theology in Crisi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0 ); James D. Smart, The Strange Silence of the Bible in the Church: A Study in Hermeneutic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0),10页。
[2] George M. Landes, “Biblical Exegesis in Crisis: What is the Exegetical Task in a Theological Context ?”274页。(若一本书或文章出现于本书后面的参考书目,则该文章有关的参考资料不会详尽地记录在附注中。)
[3]有关这方面,在Manfred Mezger, “Preparation for Preaching: The Route from Exegesis to Proclamation,” 159-179页中有很好的说明。
[4] Landes, “Biblical Exegesis in Crisis,”275页。我们在下一章的讨论,也要在他的神学观点上发展。
[5] Smart, Strange Silence,29页。
[6]同上,34页。
[7] William Ames, The Marrow of Theology, 译者John D. Eusden (Boston: Pilgrim, 1968),188页。本教科书(拉丁文本为Medulla Theology)继续广泛地受人阅读,17世纪时极受美国清教徒的重视。非常感激我的学生威廉·格拉斯(William Glass)向我提供这个参考。
[8] Hans W. Frei, The Eclip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A Study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Hermeneutic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1974), 245-260页。
[9]同上,248页。
[10] J. A. Ernesti, Elements of Interpretation,第二版,编译者Moses Stuart (Andover: Flagg and Gould, 1824),§4,2页。该译本虽然是有些不完整,却是最好的Institutio interpretis Novi Testamenti,拉丁文第五版,编者C. F. Ammon (Leipzig,1809)翻译本。另外有一本完整的译本为Charles H. Terrot所著,书名是Principles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共两册(Edinburgh: Clark,1832-1833)。见弗莱关于该语句稍微进步的译法。Eclipse,330页注1。斜体字是Stuart在这部分内容中之简要注意点。
[11]同上,§3。
[12]同上,§9。
[13]同上,§10。
[14]同上,§§18-19。
[15]同上,§22。
[16]同上,§23。摩西·斯图尔特(Moses Stuart)进一步评论道:“拉比的格言是:在经文的每一点,把意思悬疑的地方搁置一边。《他勒目》说:神把律法给了摩西,使人能有49种方法分辨一个物件洁净与否。大部分教父和一群后代的评论家均受这些原则影响。一个多世纪以前,著名的莱顿的科克由(Cocceius of Leyden)维持这种观点,即经文中一个词之所有可能的含义都应该是一致的。在他的博学和影响下,新教教会中兴起了一个有力的团体拥护这种原则。但它产生的不良影响则未曾停止。”我们要再说:就算我们进入21世纪这么晚的日子,这不良影响也不会停止。
[17]同上,§30。
[18]同上,§33。在§34和§37中,埃内斯蒂继续否认信仰类比或教义类比是经文解释的指南。参阅他的§142。我对使用信仰类比作为释经工具的迟疑已经在拙著Toward an old Testament theolog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8),16,18-19页;以及拙著“The Single Intent of Scripture,”139-140页中说明。另阅拙著:“Meanings From God's Message: Matters for Interpretation,”Christianity Today, 5 October 1979,30-33页。
[19] Ernesti, Element,§36。斜体的标题是我自己加上的。
[20] J. S. Semler, Vorbereitung zur theologischen Hermeneutik, zu weiterer Beforderung des Fleisses angehender Gottesgelehrten,共二册。(Magdeburg: Hammerde, 1761),1:160f. 弗莱将此译在Eclipse中,247页。
[21]见埃内斯蒂上列的第〔9〕点。
[22] Frei,Eclipse,248页。
[23] Ernesti,Eclipse,§4;见上列注10。Subtilitas指容量或能力。理查德·帕尔默指出J. J. Rambach对这三种能力的分别,1723年出版:Subtilitas Intelligendi(悟力),Subtilitas Explicandi(说明),及Subtilitas Applicandi(应用)。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 Dilthey,Heideger and Gadamer,187页。埃内斯蒂像是把后两种能力融合在Subtilitas Explicandi一词中。
[24]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Hermeneutics:7'ke Handwritten Manuscripts,编者:Heinz Kimmerle,译者:James Duke和H. Jackson Forstman,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Text and Translations Series,1 (M issoula, Mont.: Scholars, 1977),页41。自“The Aphorisms of 1805和1809-1810。”
[25]同上,42页。
[26]同上,76-77页。
[27] James M. Robinson, “Hermeneutic Since Barth,”在The New Hermeneutic,编者: James M. Robinson和John B. Cobb, Jr., New Frontiers in Theology, 2 (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1-77页。
[28] Hajis 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Tubingen :M o hr, 1960)。就这评估,大致上我依从E. D. Hirsch, Jr.,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254-264页。
[29] Hirsch, Validity,251-252页。
[30]尽管鲁道夫·布尔特曼的名声始于1941年他所出版的“Jesus Christ and Mythology”,但直至1955年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的下半场,他才回答这问题:我们如何了解传统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这些演讲以英文出版为History and Eschatolog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1957)。他宣称,所有的解释都是被解释者的“先见之明”所引导(113页),以及“历史意思的问题已是无意义”。因为意思只出自解释者与不可知之未来的关系(120页)。
[31] Emilio Betti, Die Hermeneutik als allgemeine Methodik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Tübingen:Mohr, 1962),1页。帕尔默将此译在Hermeneutice中,55页。见帕尔默对贝蒂思想最好的描述,54-60页。
[32] Hirsch, Validity, Xi, 8.
[33]同上,9页。
[34] Barrie A. Wilson, “Hirsch’s Hermeneutics: A Critical Examination,”特别是27-28页。
[35] William E. Cain, “Authority, ‘Cognitive Atheism,’和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 The Literary Theory of E.D. Hirsch,” 339页。他也指出Susan Suleiman, “Interpreting Ironies,” Diacritics 6 (1976): 15-21。Hirsch在E. D. Hirsch,Jr., 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7),79-80页中错误地把“含义”的定义延伸为“单纯为解释者的含义”是实在的。
[36] Palmer, Hermeneutics, 63-65页。在帕尔默的观点中,小赫希已经把释经学从“了解的理论”转到“实证的逻辑”。
[37] Walter C. Kaiser, Jr., Inerrancy的“Legitimate Hermeneutics,”编者:Norman L. Geisler (Grand Rapids:Zondervan, 1979),117-147页。
[38]这名言的历史可以在Otto Friedrich Bollnow, “What Does It Mean to Understand a Writer Better Than He Understood Himself ? ” 17-19页中找到。博尔诺夫通过Immanuel Kant, Johann G. Fichte,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August Böckh,和威廉·狄尔泰探溯出这名言。另见Hirsch,Validity,19-23页和注16;以及Frei,Eclipse,299页。弗莱算出在施莱尔马赫里这名言只出现4次,通常在心理学技术上及文法方面的诠释中平衡使用。
[39]这主张基于Friedrich von Gottl-Ottlilienfeld的Die Grenzen der Geschichte [The Limilts Hestory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1904)。另考虑约翰·费希特(Johann G. Fichte)的意见:“已经被完全透彻地思想过的事物,是可以了解的。”
[40]这实在是个大胆的步骤。即使博尔诺夫不能定规通向知识步骤的过程,他也相信这确是打破了古典文学中的“诠释循环”。这些部分的繁复性可以组成单一的整体,比如在对拉丁文句子的认识上。
[41] Bollnow, “What Do’s It Mean ?” 22-23页。
[42]同上,23-25页。
[43]同上,27页。
[44]见Lawrence E. Toombs的作品:The Old Testament in Christian Preaching.,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Christian Pulpit,” Hartford Quarterly 8 (1968): 7-14;及“The Problematic of Preaching From the Old Testament,” 302-14页。
[45] Elizabeth Achtemeier, “The Relevance of the Old Testament for Christian Preaching,” 在A Light unto My Path:Old Testament Studies in Honor of Jacob Myers中,编者:Howard N. Bream等,Gettysburg Theological Studies, 4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1974), 5~6页。这部分我采用阿赫特迈耶常用的进路。
[46] Rudolf Bultman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ld Testament for Christian Faith,” 在The Old Testament and Christian Faith: A theological Dissussion中,编者:Bernard W. Ander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8-35页。
[47] Martin No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Proclamation,”译者:James Luther Mays,在Essays on Old Testament Hermeneutics中,编者:Claus Westermann和James Luther Mays (Richmond:John Knox, 1963),76-88页(第四章)。
[48]强调为作者所加。
[49] C. Trimp, “The Relevance of Preaching (in the Light of the Reformation’s ‘Sola Scriptura’ Principle),”8页。
[50]同上,2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