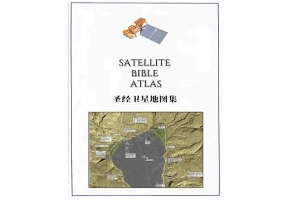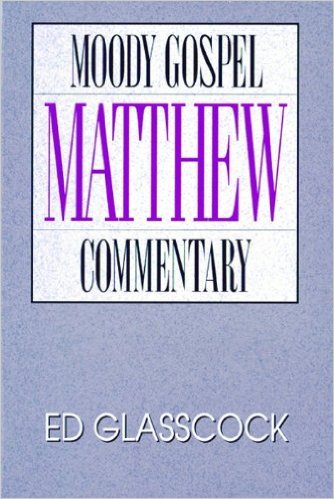我们采访了一位名叫玛拉的女士,她患了多年的严重抑郁症。大卫·鲍力生是她的辅导员之一。下面是这次采访的记录:
鲍: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给我们讲述你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故事。虽然这些事非常阴暗和艰难,但最终有了一些奇妙的转变。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你的抑郁症是如何开始的?
玛:我记得自己第一次说“我感到抑郁”是在二十年前,那时我十五岁。我不能确定在那以前我是否患了抑郁症,因为我从不记得自己曾经快乐过。但那是我第一次清楚地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接下来十七年的经历差不多可以用“我很抑郁”来形容。
鲍:什么样的经历使你说出这句话?
玛:对我来说,患上抑郁症最困难的地方之一就是,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经历。语言永远不能真正透彻地描述抑郁的感觉。十五岁时,我感到极度的悲伤、无望和孤独。1988年,我刚二十出头,便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感觉自己好像要死去一般,被一些自己无法辩明的感觉笼罩着。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应付它们。我感到恐惧,不知道该做什么。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自杀,只有这条路才能消除我的痛苦。神只留给我这一个选择。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时的感觉。我真的彻底绝望了。我知道答案在神那里,但他看起来是那么遥不可及。尽管我对神越来越疑惑,越来越生气,但仍然不能完全真正地离开他。如果真的能离开,我早就死了。我的内心里面,有太多的错误,太多的不敬虔和丑陋。一个人岂能如此不堪?我不知道那一周我该如何过下去。我知道每个人都想尽办法,努力帮助我。如果我只靠自己,肯定完了。我的感觉糟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所适从。我又痛苦,又无助,真是快要疯了。我试着让自己相信,在神那里有答案,但我完全看不到任何的曙光。现在,我感到自己就好像在一个漆黑的黑洞里。我知道在某个地方有光亮,但却看不到。我在这个黑洞里陷得越来越深。
我记得当时感到自己的身体在下沉。早晨醒来,我想要起床,一睁开眼睛,但抑郁症就在那里,它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使我感到喘不过气来,使我的胳膊和双腿更加沉重,做什么都没有力气。我知道这些身体上的感觉并不是真的,但我的感觉就是那样。同时,我还有强烈的罪疚感。
鲍:模糊的罪疚感,还是具体的罪疚感?
玛:在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从来就是一个不够好的孩子,从不能让父母满意,每件事都是我的错。这就是为什么我有许多的罪疚感。
鲍:你刚才说到了自己的感觉,孤独,内疚和不快乐,也谈到一些认知性的东西,觉得“我不如人”,还提到在一些情况下,父母对你有很高的期望,但这些期望是你不可能达到的。你是不是还有行为方面的问题呢?你的人际关系受到过什么样的影响?
玛:在青少年时期,抑郁症让我封闭自己,与朋友们疏离。青少年并不擅长处理像抑郁症这样问题,其实,成年人在这方面也不擅长。我认为主要的影响在于我的朋友圈非常狭窄,这是因为我太关注自己及自己的病,关注自己在抑郁中如何存活,以及尝试着摆脱抑郁。我不仅在整个青少年时期是这样,甚至在整个患抑郁症期间都是这样。这就是抑郁症的问题之一——使人非常以自我为中心。
鲍:你能否更详细地讲述这方面的经历?
玛:对我来说,患上抑郁症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绝望。我没有出路,感觉就像行走在一片永远无法消散的乌云中。它使我封闭自己,使一切事物都扭曲了。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我活在抑郁的阴影下,没有人能了解我所走过的路。当我说自己得了抑郁症,我感到人们虽然对抑郁症有一个概念,但不能真正地理解我所处的景况。抑郁症扭曲了我对周围世界的理解方式。我好像在透过一层云雾观看,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扭曲了,其中包括我跟他人之间的关系,我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
鲍:可以举个这方面的例子吗?
玛:就拿我对他人的看法为例吧,抑郁症使我对人产生恐惧,比如他们会如何回应我,如何看我等。我不知道究竟哪个因素在先,是惧怕人导致了抑郁症,还是抑郁症加深了我对人的恐惧。
鲍:你在怕什么?
玛:我害怕别人的拒绝、指责和不理解。同时,我又总是希望别人可以救我。
鲍:他们如何能救你?
玛:我知道我不能救自己。很多时候,我觉得神不会将我从抑郁症中救出来。我认为神有这个能力,但不相信他会救我,神是在瞒我。我也不知道人们会如何救我,只是觉得他们能救我。我觉得他们可以填补我内心中缺失的东西。
鲍:这算是惧怕人的另一面吗?
玛:我觉得别人可以使我感到有价值。如果他们给我足够的关注和时间,我就会感到自己是被爱的、完整的和有价值的。如果他们将足够的精力花在我身上,就能消除我的不足,拿走我的内疚、孤独和抑郁。
鲍:但惧怕人从来都没有使抑郁症好转吧?
玛:没有。我在日记里曾经写了以下这些话:“我从来都不认为神关心我或是关心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事,也从不认为他能保护我。我一直认为,只有自己才能保护自己。我在与整个世界为敌。如果我能够早一些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就不会感到那么孤单,也不会对每件事那么快地做出反击了。我或许会更好地面对他人的批评,更冷静地应对他人的攻击。我知道自己是如何尽心地照看自己的孩子,如何想要去保护他们,如果我相信神也同样以这种方式看顾我,一切就会完全不同。我会感到更安全。我明确地认为,神的爱是良好的、超然的,却又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鲍:你是如何看待神的?请简单介绍一下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他话语的认识、你的教会和神学观点。
玛:我在一所很好的教会里长大,后来就读基督教学校。十五岁时,我就成了一名基督徒。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说自己感到抑郁。信仰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塑造了我的行为。我努力孝敬父母,不去参加任何派对。我在教会里非常活跃,这就像我的生命线。另外,我对神的认识非常律法主义,这是家庭和学校共同造成的。我知道耶稣为了我的罪而受死,也知道圣经说神已经赦免了我、爱我,但仍然非常想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取他的爱。我在心里并没有真正地相信,圣经上所说的那些事是真实的。一方面,我总是带着一种不合标准的罪疚感;另一方面,我又非常骄傲,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如果自己听从命令、完成了足够的任务,就有资格赚取他的爱,我就合格了。
鲍:什么样的命令?
玛:凡事都要做得足够好。在我生命不同的阶段里,这个定义是不同的,譬如说,做一位好母亲、好妻子、好女儿和好学生,保持好的身材,每天都进行灵修等,我就可以了。这个定义会不断改变,我认为我也不断有新的命令需要去执行。这是一种骄傲。因为在内心深处,我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做一些事来赚取神的爱、饶恕和接纳。我试图在耶稣为我成就的事上另外添加一些东西。
鲍:在这些年里,你为了治疗抑郁症,都尝试过哪些方式?
玛:在医学和精神病学方面,我该做的尝试都做了。实际上,医院里的抗抑郁药我都差不多吃遍了,但我从未将所有的希望放在药物上。我住过几次院,还去做过两次电休克疗法。
鲍:目前,你如何评价药物的作用?
玛:对我来说,药物实际上能提供的帮助是微乎其微的。电休克疗法的确帮助我暂时感觉好了些。但在某些方面,我认为这些药物实际上使我感到更抑郁,更没有盼望,我不论尝试哪一种药物,似乎都不能得到什么帮助。虽然医生说“药物就是答案”、“总有一种药会对你有帮助”,但那不过是一种尝试,什么都没能真正帮到我。我认为,如果人们可以把药物视为一种工具,在抑郁过程中能使人得到帮助,但永远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药物上。其实,人们极其容易把希望寄托在药物上。
鲍:来谈谈现在的情况。你现在对这些事是如何看待的?
玛:这几年认识我的人对我的了解还是有限的。他们对我的经历知道得很少。我现在的生活不一样了,神在我身上动工,使我改变了许多。
鲍:你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在人生中看重的是什么?
玛:我的人生改变了很多。在过去的几年里,我重新回到学校去学习,拿到了本科文凭,现正在上圣经辅导的研究生,其实,我也在辅导别人。这种感觉非常好,给了我很多喜乐。我对此非常感恩,但这并不是我最重大的改变。抑郁症虽困扰我多年,但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我目前的情况和以前大不相同,我完全摆脱了抑郁,但这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主要的改变。我最重大的改变就是,我第一次真正与神和好了,这并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赚取的,而是我知道我在基督里的身份,相信神就是圣经中所说的那位神。
鲍:你以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是的,我知道神会爱人,但他只爱别人,他不可能真的爱我,他恨我。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几分钟前,你说自己曾经惧怕人,怕被拒绝,希望别人使你感到被爱。如今,你已经不再过分关注自己的表现和他人的赞许了。如果我们可以仔细思考自己的改变、如何改变的以及得到了哪些帮助,并加以明确的解释,就能看到最重要的事情。威廉·斯泰隆在《黑暗笼罩》(Darkness Visible)一书中刻画了抑郁症如何让人感到幽暗,但他并未给出任何的答案。他只是有一天醒来,发现生活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软弱无力,什么都做不了。你是如何改变的?你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力量。
玛:神曾藉着一些事改变了我。但这种改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不是说我一觉醒来就觉得自己完全好了。
鲍:当然不可能!根据我的观察,关键的时间段是几个月,或是几年,对吗?
玛:应该是两三年。
鲍:你如何描述这段时间?
玛:在人生的某一时刻,我感到极其压抑,整天都想着自杀。我对神非常生气。我认为,如果他想要将抑郁症从我身上除去,是可以做到的,但他却没有做。我不想以这种方式度过余生。我非常生神的气。自从成为基督徒以来,这是我信仰上最大的危机。
鲍:那天你说:“我试过了,基督教不管用。神并没有遵守他的约定。《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的经文是空洞的。这就是我自己的体会,我不想再忍受抑郁了,我要摆脱它。”
玛:这是在我陷入淫乱关系的几个月之后说的。然而出乎意料的,当时我正在选修圣经辅导课程。那或许是我最悖逆的时刻,我遇到了信仰中的最大危机,但神还是引领我学习圣经辅导课程。我记得自己坐在教室里,听到人们在谈论我此前的观点——受辅导者只是将神当作自动售货机,你将钱放进去,而他应该给你想要的东西;否则就会说基督教不管用。他们所说的“那些罪人”就是我,他们讨论的问题全部是我心里想的,那些“明显的罪”是我的罪。我在好几门课上如坐针毡,很难坚持听完。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逃离羊群的羊,拼命地朝着悬崖边上跑去,而悬崖下就是死亡和毁灭。这就是我对自己的想象。与此同时,这也是神开始在我生命中动工的时刻。
鲍:什么东西在你心里具体化了?这种新的认知为何影响了你?是什么使你得到了改变?
玛:我在悖逆中,做出了一些毁灭性的选择。我就像一只小羊跑向悬崖一样,不只是跑向自我毁灭,而且是跑进罪恶的深渊里。我开始深深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人若是认识不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就认识不到恩典的意义。
鲍:记得我们曾经谈到,你一方面认为自己是一个可恶的人,另一方面却不认为自己真的是个罪人,真的需要恩典。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而已。你得了抑郁症,你的情绪非常糟糕,而上帝却没有拿走你的坏情绪,使你成为一个愤愤不平的受害者。你的罪疚感和“我基本上是好的”的感受掺杂到了一起。
玛:那时,我虽然有罪疚感,但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女孩。现在我以敬畏的心认识到,自己的罪是多么地严重,对自己和他人造成的伤害有多大,然而神却动工来改变我。我以前常说自己对一些小事都会心存愧疚,更别说严重的罪了。然而,我却做了一些连自己都万万没想到的事,那种罪疚使我无法承受。但是,这件事也真正地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使我能够明白神的恩典以及基督为我成就的大事。
鲍:你是如何明白的?
玛:尽管我行走在一条灭亡之路上,但神还是将我放在某个位置上,让我可以学习他真理的话语,让我知道他是谁。
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没有完全理解恩典,认识到恩典是稍后的事。后来,我经历了一个破碎和谦卑的过程。我不再与神争论他是谁和他对我人生的旨意等问题。到了这一步,我彻底被破碎了。即使他让我的余生在抑郁中度过,我也得顺服。我是谁,竟敢跟神顶嘴呢?有几件事帮助我认识到了这一点。第一件事是,我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这使我谦卑下来。第二件事就是,我在一次课上读了《天路历程》。这本书非常有意义。当班扬谈到疑虑城堡和绝望巨人时,我的心深深地被抓住了。这位朝圣者只要运用一样东西就能走出城堡——信心。神通过这本书向我说话。另外,我当时虽然没有认真地读经,但听了许多的基督教歌曲,其中包括麦克尔·卡德(Michael Card)的《约伯组曲》(The Job Suite)。这首歌讲的是约伯的一生。我一遍遍地听,在这首诗歌的结尾处,约伯说:“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在心里说:“主啊,我将对这件事闭口不言。”我甚至觉得对神说“好的,如果抑郁是你对我的旨意,那么就这样吧”,都显得太狂傲。他是神!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向神重复着约伯说的话。我说这些话的同时丝毫没有想过,如果我这样做,他就会将我从抑郁症中释放出来,我一点也没有那样想。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是:“神啊,我愿意降服在你的旨意下。”
鲍:我以前经常看到你向神发怒。我很想知道你现在是否也是这样看的。以前,你的人生绕着一根轴在转——你的抑郁是神造成的,神令你失望,他没有改变这种感觉,没有使你感到被爱;他说他是天父,但你并没有感受到父亲般的爱。他快要让你疯了。现在看来,你绕着转的那根轴不一样发了。以前抑郁症是这根轴的中心,但现在发自内心的懊悔和对恩典的需要占据了主要地位。是这样的吗?
玛:是的。我不知道当时是否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对神发怒,但在那时候我是知道的。当我认识到这一点,并说“神啊,如果这就是你对我人生的旨意,我愿意降服在你的旨意下”,我的关注点和方向随即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想着如何将自己从抑郁症中解脱出来,虽说这是成年后我主要的关注点。我来到神面前说:“好的,如果你定意让我活在抑郁中,我愿意顺服。”这样的认识释放了我,改变了我的关注点,改变了我找寻的目标。同时,随着我对神的主权、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的确信,再加上我决定不再与他争辩,使我相信神是良善的。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当我决定,不管抑郁症对我意味着什么,都愿意降服在神对我人生的旨意下后,我就更加明白神的良善了。我逐渐相信,有关神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是良善的;他对我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爱我、赦免了我的罪,不论我自己的感觉和经历如何。与此同时,我还是非常抑郁,也没有远离淫乱的罪。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然而,我已经确信,我需要相信神是良善的,不是恶的。
那时,另一件事成为一个转折点。再回到前面那幅关于羊的画面,我当时仍然觉得自己一意孤行,冲出围栏,跑向那个会让我摔得粉身碎骨的悬崖。我虽然当时深陷罪中,但仍然不断地向神祷告:“神啊,不要放弃我!”在人生的那一段日子里,我强烈地感觉到神的同在,是成为基督徒以来最强烈的感受。这帮助我明白神的良善,使我可以说:“神啊,你是良善的!”不论我的感觉或是经历如何,神都是良善的。“你是良善的,因为你说你是良善的”。
我还能清楚记得当时所做的决定。但我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神面前,重新将自己委身于神。争战还没有结束。我清楚地记得一次又一次地作决定。但对我来说,这些决定无疑是我的转折点并且促使我不断向前。
鲍:让我们转换一个话题。我们想听听你对抑郁症的诱因的看法。关于这个问题,众说不一。有些人说,抑郁症是由怒气和失望而产生的;有些人则说,由于心里的苦毒没有得到清理,以至于针对自己;还有一些人认为是由于人们的悖逆、想逃避责任引起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听到两种最常见的世俗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一个人得抑郁症是因为成长环境恶劣,屡受伤害。第二种理论(现在最能得到世人的认同)认为抑郁症的诱因是人体的生物基因。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都有身体,有人生的经历,有各自的行为,也会变得苦毒,但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抑郁呢?
玛:抑郁症完全是一种恶性循环,很多因素掺杂在一起,很难找出单一的原因。它可能是由某一件事引发,但随后别的事会添加进来,混合在一起,不断地将你推向抑郁情绪的最深处。我的原生家庭的确对我产生了影响,或许在我早几年的抑郁中,扮演了部分的角色。我的父亲总是不在家,即使偶尔在家,也非常严肃。他跟我关系疏远,对我要求很高。我母亲十分苛求,对我的期望也很高,具有非常强的控制欲和操控欲。我的确受到了伤害,但这只是引发抑郁症的部分原因。除此之外,我追求的目标、抑郁的根源以及导致抑郁的因素都是源于我内心的问题,而不是过去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事。我虽然受到伤害,但也以同样有罪的方式做出了回应。这使我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鲍:你曾经说,导致你得抑郁症的东西就是促使你犯罪的东西,其中包括内心的偶像、想要被人接纳的愿望,做到完美等。这句话有道理。一个人外在的状况和内心是紧密相连的。
玛:这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我人生目标之一就是寻求爱。我在寻找爱和关心,寻找别人对我真正的理解。我在寻找一个父亲般的人物,他能够真正地关心我的感受,能够使我的感觉好些。这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不是说“因为我没有得到这个,所以会得抑郁症”。我的抑郁是一种悲伤和绝望的情绪,因为我没有得到自认为需要的东西。
抑郁症甚至能暂时帮助我,让我暂时品尝到自己寻找的东西。我学会了利用自己的抑郁来达到目的。我会向比我大十到十五岁的男性辅导员寻求辅导,其中包括高中的辅导员,牧师,基督徒辅导员。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真正的关爱和关心,但这永远都不够。我还记得,有时我因为抑郁而去向他们寻求帮助,只是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毫无疑问,我在用抑郁症去操控他人,努力去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我感觉很绝望。虽然我不觉得自己是在操控别人,但事实上的确是。情欲是个永远填不满的洞。
同样的渴望促使我犯了淫乱罪。我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生都在寻找的东西。他比我大,一个父亲般的人物。他理解我,体会我的感受。
鲍:他正好在你抑郁时走进了你的生活,与你的情感产生共鸣。
玛:他勾起了我的偶像。我一直将淫乱看作是“大罪”,但我逐渐认识到,我自己的内心不仅驱使我陷入淫乱,还陷入抑郁。
为了结束淫乱,我要治死最初燃起这段感情的东西。我感觉自己像死了一般。但当我向着自己死的时候,反而开始找到新生——我的抑郁症也开始发生转变了。
两件非常细小的事进入到了我的内心,改变了我。第一,我有了盼望,一开始非常微小,这个盼望就是神可以用我的经历去帮助他人。自从上高中以来,这种想法就藏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如果我有一天走出了这样的患难,神就能使用我的患难去帮助他人。不管一切有多混乱,这是神的恩赐,并且在我里面开花成长。这件事是使我现在去辅导别人的动力之一。第二件事是关于《约珥书》2章25节的经文,关于那些年蝗虫所吃的神要补还他们。我觉得自己人生中的许多年,包括整个成年生活都被抑郁症吞食了。虽说我结婚了,也有了孩子,但在我自己大半的人生里,我并没有真正地活着。我得到了盼望,知道神能够挽回一切。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将患抑郁症的那些年当作是浪费的光阴。我认为它们对我来说非常宝贵。
鲍:你得到了什么,使你能够给予别人?
玛:毫无疑问,我的经历使我更能理解别人的真实处境,而不会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不会让辅导停留在肤浅的层面。每当我辅导别人时,特别是那些与我有同样挣扎的人时,就会想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哪些事情对我有帮助,哪些没有,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我非常感激那些曾经对我付出耐心的人!在人生中,神给了我多年来都很忠实的朋友。他们对我非常耐心,当我不见起色时,他们仍然表现出恒久的忍耐。我当然也从中学到了耐心。我可以对受辅导的人说:“你是有盼望的,因为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如果说世上存在一个没有盼望的人,那便是我。我人生中的很多年都在抑郁中度过。我尝试了各种方法:服用各种抗抑郁药,进行过电击疗法,住过几次医院。我试图自杀过,自杀的念头缠绕了我好多年。”不管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不可能像我以前那样的绝望,也不可能像我那样糟糕。如果他们当时抓不住任何可以依靠的,那么我至少可以提供给他们盼望——神在做工,但他有自己的时间表。
鲍:你刚才谈到的盼望是很具体的。多年的经历使得你所说的话与属世的同情非常不同。人们说“我已经经历过了,我也受过苦,所以我可以与你同行”,这样的同情并没有太大的帮助,而你其实是在向人们传递真正的盼望,正如你所得到的一样。
玛:盼望并不是因为我或我所做的事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由于神在真实的环境中真正动工。
鲍:当你描述自己跟他人交谈时,你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坦诚,总是实话实说。你不是一个“同情小姐”,而是考量事情,实事求是地做辅导。
玛:我认为同情不能拯救或改变任何人。同情是有帮助的,却不能将人从他们所处的各种捆绑和奴役中解救出来。
鲍:如果一个人是为了被爱、接纳和理解而活,那么同情的部分含义便是给予爱、接纳和理解。这样做的危险之处是,这会勾起和强化对方内心的偶像,使对方对你产生依赖。他们并不会认识到,自己寻找的其实是错误的东西。
玛:说实话,我认为自己在对他人的辅导中更能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我自己深有体会。我不想强化人们内心的偶像,这偶像是需要拆毁和离弃的。然而,与此同时,我想要向人们彰显出神的恩典(不论这有多模糊),而且在我与他们建立关系时,想要向他们表明神的爱。对我来说,这在我的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我接受辅导的过程中。
鲍:在交谈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了完美主义,包括对外表,房子,钢琴演奏水平,学历,考试分数以及亲子教育等方面过高的要求。人们常常通过使自己达到完美,来得到别人的爱和接纳。完美主义起到了什么作用?
玛:我患抑郁症的确和完美主义有密切的关系。正如我此前所说的,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常想通过良好的表现来换取上帝的爱、父母的赞许或他人的接纳。我给自己定的标准非常高,几近完美,而我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地达到这个标准。有时,这导致我直接放弃或是根本不想去尝试。根本不去尝试比失败接受起来得更容易。我已经被失败吓破胆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生活中没有目标的部分原因。如果有谁说“你失败了”,或是有谁谴责、批评我的话,我就会大受打击。这种心态真正的原因是不明白恩典以及没有真正地信靠神。
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很失败,另一方面又狂妄自大,觉得自己不需要基督,可以靠自己,这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我也不需要恩典。我觉得自己只要做得足够好,就会得到神的爱和接纳。这种想法慢慢变得根深蒂固。然而,当我在那段悖逆期里,径直陷入罪中时,这样的想法才开始破裂。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都由一条主线连接在一起,并且每个部分都是紧密相联——完美主义是跟自以为义和靠行为称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你真正认识到罪和恩典时,这种想法对你来说都变得毫无意义。
我是不是又重了两斤?我的头发是否漂亮?厨房的地板是否干净?虽然这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困扰着我,但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逐渐让自己不再在意这些东西了。神做了许多工作,但我还不能说我已经做到了,已经完全了。
鲍:谈谈有关目标的问题吧。我记得你从不制定任何目标。
玛:我以前从未制定过目标。我高中毕业后,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父母帮我选了一所大学,我上是上了,但根本不想要也不在乎那个文凭。后来,我认识了我的丈夫。神是如此奇妙和慈爱,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丈夫,让他以令人惊奇的方式来爱我并支持我。我从未想过这件事,他就像从天而降来到我面前的,这一切都是神安排的。一生中,我从未有过任何目标,这可以说是绝望、毫无盼望和完美主义结合而造成的结果。我如果不能把一件事做到完美,根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甚至连尝试一下都不愿意。我常想:“定立目标有什么意义呢?”我记得跟你谈到过,从青少年时起,我就认定自己的结局不是自杀就是进精神病院。这些想法吞噬了我人生的目标。为什么要庸人自扰呢?回首往事,我无法想象那些想法对我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
在过去的三四年间,我生命中发生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改变就是,我第一次去追求有关学业和事业上的目标。我开始相信,靠着神的恩典,我是有未来的。我认为,抑郁症的好转、生活有了目标等,许多外在的改变都是伟大奇妙的事,但这些并不是最有意义或最重要的改变,而只是神在我内心所作的改变之外,外加的祝福。我认识到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并且真正与神和好了。我不必再像以前那样,一直在自己与他的关系上劳心费力了。当然,这并不是说过去的事情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我终于能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并藉着基督得到神的爱。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说我有多好。我从此不必再为与神的关系挣扎了。我认识到他在圣经中所说的一切事都是真实的,并且我可以倚靠他的话语。我认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中,最重要的就是,我终于认识到,圣经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实的。正因为这样,我才成为了一个不一样的人。我有了信心,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虽然有时还会陷入抑郁中,但基本上已经好转了,有时即便处于抑郁中,我仍然有信心。我重新回到学校上学,给他人做辅导,并且经历着生命中的许多其他的祝福。这些美好的祝福使我感到快乐,但我并不把它们放在首位。
鲍:你说得太对了,我深有同感。你说到自己开始认识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另外,你可以说一下你的家人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吗?
玛:我非常感谢并且敬重自己的丈夫。我真的可以这么说,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他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我之所以这样来评价我的丈夫,不是因为他一直做得很完美或是从未出过错,而是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一条艰辛的路。结婚十四年来,他从来没有因为我的抑郁症,对我红过脸。我们婚姻的前十年就是在我的抑郁中走过的!他有时回到家,即使我们还没有孩子,家里也是乱七八糟的——床铺没有整理,碗盘在水槽里,而我却缩在厨房的角落里发呆或是哭泣。有的时候,他到家后发现我正在车库,坐在发动的汽车里,想着如何自杀。但他从未因为这些而生过我的气或是抱怨过——一次都没有!只有几次,他因为厌倦了我的做法,离我远一点,但他从未埋怨过我或是对我生过气。对我来说,这真是太大的祝福。
当一个人在抑郁症中挣扎时,人们常常认为家人理所当然要跟他一同承受。我知道自己不可能了解,当我有时一时冲动想要自杀时,丈夫会感到多么恐惧。人们常常忘记这对家人或配偶来说是多么沉重的负担。我的丈夫虽不完美,但对我特别忠实。在我走出抑郁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的很大的变化,我们也因此做了一些调整。这对我们来说不容易,我自从摆脱了抑郁后,仿佛换了一个人。
鲍:具体有哪些调整?你是如何改变的?你们现在的状况如何?
玛:当我摆脱了抑郁的束缚之后,改变了很多。丈夫担心我会对他感到厌倦,对他失去兴趣,担心他不能满足我。对于这些,我并不担心。我所关注的是,我突然觉得不认识自己了,甚至有些难为情。我以前觉得自己被抑郁症包裹着、压迫着,仿佛我就是抑郁症的代名词,抑郁症就是我的身份。当我走出抑郁后,我个性中新的一面开始呈现出来,让我很不适应。我经常感到难为情,不知道自己是谁,将要成为什么人。我又开始弹钢琴了,在艺术方面的才华逐渐展露出来。我变得能勇敢而冷静地面对事情,变得更加直接、坦率,能更多地与人互动,对周围的世界和人们更加感兴趣。我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夫妻之间的关系当然需要调整了。
鲍:一直以来,你都是一个有才智而且善于表达的人。虽然你经常处在抑郁的阴云之下,但仍不时闪过一丝智慧的火花。但你现在变得更有活力,善于与人沟通、善于表达。你变得有想法,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按理说,你以前很少和人交流,现在变得非常活跃,这是你在个性方面有很大的转变,但你并没有改变成另外一个人,人们还是能够认得你,只是你的个性完全被释放了。
玛:对于我丈夫来说,难以面对不是我个性上的改变,而是我们角色的转变。他曾经一直在照顾我,而我总是依赖他,需要他。现在,我逐渐开始脱离对他的依赖,变得更加独立了。这是好的。我开始对他做一些不一样的期望。这对他来说是一项挑战,因为这些领域是他的弱项或是被我的抑郁症所扼杀了。但我们一天天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已经走完了过渡时期,适应了现在的生活。关于抑郁症,我还想说的一点是,虽然对他来说非常艰难(我知道自己不能完全了解对他来说到底有多艰难),但它的确让我们的关系更近,因为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它使我们紧密联合在一起,增加了我们关系的深度。若是我们没有一起经历抑郁症,或许我们的感情不会这么深厚。
鲍:你曾经提到,神使用抑郁症使你远离自我毁灭。
玛:我们很多亲戚的家庭仍然处于一片混乱中。他们现在所过的生活跟他们二十年前的一模一样,唯一的变化是,他们的问题已经升级恶化了。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在二十年前所走的灭亡之路和犯的习惯性的罪都已经像毒瘤一样滋生扩散了。在我的周围,人们的生活和婚姻都在土崩瓦解。我确实相信,由于抑郁症,我被迫去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被迫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自己,被迫去面对自己,最终得到改变。我如果还按照以前那种生活方式的话,根本活不下来。这是上帝使用抑郁症来拯救我的一种方式。我感谢抑郁症,这话是我在以前怎么都不能说出口的。我不是说还想要再经历一次,而是说我感谢神,应允抑郁症发生在我的人生中。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年的经历。从某些方面来讲,抑郁症就像是另一种生活,谈论它时,我仿佛身临其境。
鲍:你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特别是在自杀方面,似乎神使用了你的孩子,作为阻止你轻生的强大力量。
玛:是的,他们的确是神使用的方法之一,使我有动力继续活下去。有了孩子以后,我就要变得更加勤快些。当孩子需要照顾时,我没有一天不在照顾他们,尽管我可能会有许多的意外情况。我知道神用我对他们的爱以及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爱来教导我有关他的爱,让我知道他的爱是主动的,时时保护和看顾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