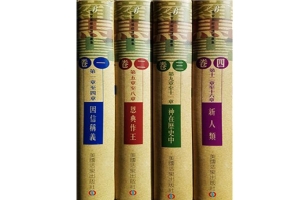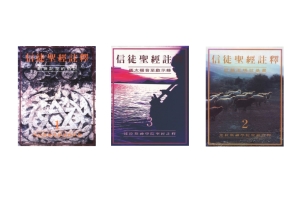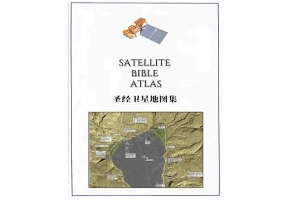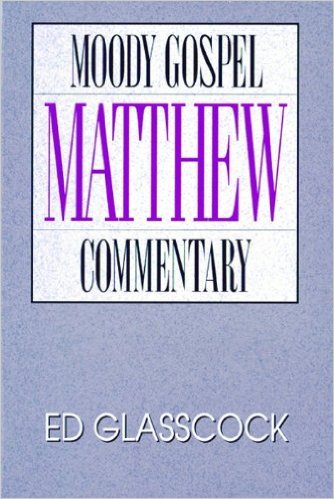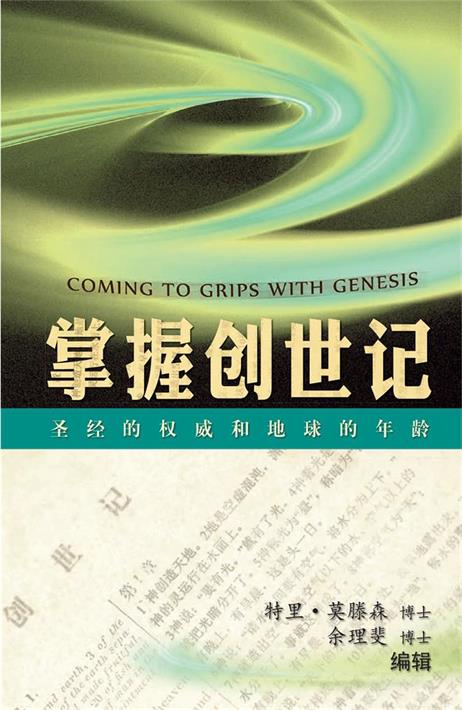
第十三章:死亡从哪里来?关于死亡与自然之恶的圣经神学
詹姆斯·斯坦博(James Stambaugh)
每天看新闻报导,就知道肉身死亡是现今世界的一个悲哀现实。我们听到有人死于疾病、风暴、火山、地震、车祸、罪案和战争。而且人的死亡与其年龄、国籍、财富或宗教毫无关联。幸存的人饱受痛苦,且可能是强烈的痛苦。
然而,人类并非是死亡的唯一受害者,动物也受制于死亡。有时为了减轻我们所爱的宠物的痛苦,会让它们安乐死;有些动物被撞死在公路上,也有些动物成为其它动物的食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地球的岩石中找到更多的死亡证据,沉积于地层中数十亿化石样本,为动物在地球历史中经历的疾病、死亡和灭绝,提供了清晰的证据。
人们常问:“为什么会有这一切的死亡?”一般人假定死亡被编织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如果上帝真的关心他的受造物,他本该有所作为。但可惜的是,当我们问为什么会有死亡时,天堂总是沉默以对。正如我们的经验显明,所有受造物都必承受死亡这个结局,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体和情感上的痛苦。
我们常常不用神学的眼光去思考生命和死亡。我们倾向于忘记(或更糟糕的是,拒绝)一些分水岭事件,圣经说这些事件塑造了地球,并对植物、动物和人类产生了重大影响。您是否曾在《国家地理》的一个特别节目看见一只母狮追逐羚羊并最终吃掉了它?这只羚羊正在逃命,眼中充满了恐惧。当我们从一些关于自然灾害的新闻中了解到许多人死亡或遭遇痛苦的时候,我们在身体和情绪上都会自然地产生负面的反应。这里似乎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假定,即被造物命该如此。这样的假定引发了许多人对上帝真实性的质疑。例如:“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和死亡?他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个充满痛苦和死亡的世界?究其原因,要么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问题,要么是他根本就不在意。” 这个问题在神学上被称为“邪恶问题” ;而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则称为“神义论” 。[1] 这个问题引发了对上帝品格和能力的怀疑,把受造界的状况归咎于创造者身上。
如今,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似乎在暗示,世界上出现的各样状况,都不应该归咎于人,而应该归咎于上帝。休·罗斯(Ross)指出:
“一方面,因人的罪使我们对衰败、劳作、死亡、痛苦和灾难自然地做出消极的反应;另一方面,这些最终都与上帝永久性地战胜罪的计划相关联。圣经中没有经文迫使我们认定在亚当第一次忤逆上帝的行为之前,这些现象统统不存在。另一方面,上帝透过自然界大量的证据向我们表明,在上帝创造亚当之前所有这些确实都存在了很长的时间。”[2]
休·罗斯相信,我们目前所观察到的正在运行的世界体系是上帝所造的,在人类犯罪以前就是这个样子。但这种观点正确吗? 这和圣经的教导一致吗? 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死亡、疼痛和灾难的始作俑者,那么对提出“邪恶问题”的怀疑论者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按照圣经去认识痛苦和死亡的起源及其属性。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前后一致的神义论和神学立场,以及有效的见证。
1. 什么是肉身死亡?
我们首先需要研究圣经中描述“死亡”的词汇。考察圣经中关于死亡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词汇,和根据对英语词汇的考量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
韦氏英语词典中为 “death(死亡)”提供了9个不同层面的定义。[3] 第一个定义对我们的研究最为相关:“死亡是一种行为或事实,指人或动植物生命的永久停止,一切生命功能的永远丧失。”英语 “death”一词清楚地表示植物会死亡,就像动物和人会死亡一样。
但是,当我们看圣经对“活”与“死”的定义时,我们看到一张不同的图画。再查验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这副图画就得到印证。我们看到,圣经所描述的有生命的物体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第一,它必须要有意识。反映意识的希伯来词是ֶנֶפש(nephesh),希腊词是ψʋχή(psuche),这两个词都经常被译成“灵魂”。所以一个活物必须对自己和环境有意识。第二个要素,根据圣经的定义,活物必须会呼吸,就是利用某些身体器官进行气体交换。圣经用“生命的气息”来描述人和动物,但不包括植物。[4] 最后一个存在于活物中的要素是血液。《利未记》17:11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人和动物都有这三个生命的特质,但植物缺少其中的两个,有些植物有血液这个要素,比如有些豆科植物用血红蛋白在根部固氮,但其“血液”不像动物和人的血液那样遍布全身。可见,英文中的“活”字更宽泛,包括人、动物和植物,但圣经却没有授予植物像人和动物那样的“活物”地位。[5] 然而,有些基督徒提出植物也会“死”的话题,我们在后面会探讨这一点。
旧约希伯来语的“死亡”一词,是מּות(mût)。[6] 它作名词(161次),也作动词(630次,以最基本的Qal词干形式)。《旧约希伯来文与亚兰文字汇》(The Hebrew and Aramaic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简称HALOT)[7]为其动词Qal词干提供了四重定义[8],为名词提供了六重定义[9]。斯米克(Smick)指出:
“Mût可指自然死亡或暴力死亡,暴力死亡可能是刑罚或其它情况。尽管mût 这个词根主要用来指人类的死亡,但也不限于此。该字根通用于闪族语系中,泛指死亡和垂死。”[10]
旧约使用מּות或其同义词,普遍是指生命的离开。[11] 它主要是描述人类的死亡,尽管动物也会死。旧约唯一用מּות描述植物的死亡,是在约伯记14:8,这个我们后面会讨论。
新约主要用两个不同的希腊文词汇来表示“死亡”,即θάνατoς和 νɛκρός 这两个名词及其动词形式。比较而言,θάνατoς 的含义更为宽泛,可以表达身体死亡和灵魂死亡(永死)。[12] 圣经有一处记载了动物的死亡(启示录8:9),该处使用了θάνατoς 的动词形式 ἀπoθνῄσκω。第二个词νɛκρός ,则表达肉体死亡,或者比喻某物变为无用。[13] 戴维斯(Davids)指出,νɛκρός 在神学上常常表达两种概念: “在身体方面停止了生命的特征,或者是在灵魂上与上帝的分离。” [14] 与旧约一致,这两个希腊词也被用于人类。
读者可能会想到,在英文的旧约和新约的有些段落中提到了植物的“death(死)”。的确如此,但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被翻译成“death(死)”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词汇是什么?这些词是怎么用的?旧约中有一次用מּות这个词来指植物死亡,新约也有两节经文用ἀπoθνῄσκω来描述植物的死亡。没有任何形式的 νɛκρός 被用来描述植物,只有上述θάνατoς(thanatos)的变体被用于植物。现在我们来仔细分析这几节经文。
唯一用מּות来描述植物“死亡”的旧约经文是约伯记14:8。在查考这段经文时,为了更好地理解上下文,我们需要从第7节读到第12节:
7 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8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9及至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10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11海中的水绝尽,江河消散干涸。12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仍不得复醒,也不得从睡中唤醒 。
这里约伯希望人像树一样,树看起来好像死了,但给它浇水后,它便可以恢复生机。然而人死去,却没有新生的盼望。[15] 约伯想表达的是:树看上去已经死了,其实它没死。克莱恩(Cline)说得好: “人死后失去力量与树被砍后继续保持的生命力形成对比。” [16] 因此,虽然מּות用于描述植物的死亡,但这段经文彰示了植物死亡和人类死亡(我们也可以再加上动物死亡)的根本区别。植物的死亡,其含义不同于人类与动物的死亡,因为植物的“活着”,也不同于人类与动物的“活着”。
新约中有两段经文用“死亡”来讲述植物。第一处是约翰福音 12:24,其背景是12:20-33。经文如下:
20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21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22腓力去告诉安得烈,安得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23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24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25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 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26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27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甚麽才好呢?父阿,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28父阿,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29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30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31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32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33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
有人会争辩说,耶稣非常明确地说种子“死”了,所以植物都会死。从表面看,这似乎颇有说服力。然而,仔细考察这段经文,很明显,耶稣使用的是表象语言(language of appearance)。
耶稣透过这种表象语言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来:第一,从上下文来看,麦子的死,指耶稣借着自己的死得荣耀。因此,第24节被认为是比喻或象征耶稣将来的复活。[17] 第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这个短语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了25次,通常出现在耶稣讲解神的国,或指自己是那受膏之王(即弥赛亚)的时候。所以耶稣是这段经文的焦点,而不是麦子。第三,这段经文的重点不在于种子的“死亡” (像人一样),因为没有人认为种子本身是活着的。种子只有“生命”的潜质,它必须发芽才会有“生命”。耶稣用种子的比喻表明,种子必须被埋葬,才能生发果实。类似地,人子必须被埋葬,才能结出许多果子。果子就是相信他和他的复活的人。[18] 耶稣用埋葬种子的例子,形象地描述了他的死和复活。他的死和复活,生发了教会。这里耶稣并没有说植物或植物器官的死亡与人(或动物)的死亡具有相同的意义。
第二处经文是犹大书12节,犹大似乎在说一棵树可能会“死而又死”。经文如下:
11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12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或作:玷污 )。他们作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13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
犹大首先诅咒那些毒害基督徒读者的假教师(叛教者)。他举了两个旧约的例子和四个自然界的例子来描述他们的特征。每个例子,犹大都数点假教师与他们的相像之处。云彩表明这些人被吹来吹去飘忽不定;海浪的沫子表示他们行为上的羞耻;他们也像流荡的星,注定永远与上帝隔绝。
我们感兴趣的,是犹大将这些假教师比作树,他强调树“死而又死(ἀπoθανόντα ἐκριζωθέντα)”。[19] 犹大描述这些假教师在灵命上处于像死树一样的状态,而且还要经历第二次的死。在所有的释经者中,似乎只有梅耶(Mayor)认为“死而又死”既指树木,也指叛教者。[20] 其它的释经书大都遵循巴克汉姆(Bauckham)的观点,他说,“很难给‘死而又死’赋予植物学上的意义。”[21] 犹大似乎像约伯一样,用树比喻人的死亡。犹大强调的是树要受创两次才被毁,但假教师的罪已经定了。“死而又死”,似乎旨在表达“第二次的死”。因为假教师将面临现在的和将来的双重审判,所以犹大如此强烈地谴责他们。不能说树木会死两次,因为只有人类才会这样。新约经文在谈到植物“死亡”时,重点描述的是一个画面,而不是关于植物死亡的命题陈述。这两段经文都不能用来证明植物像动物和人一样会“死亡”(不同于植物,动物和人是有生命的活物[חַיּה נֶפֶשׁ ] ,创世记1:2-21,1:30,2:7)。
因此,圣经中的死亡一词具有广泛的含义。如我们所见,旧约主要使用一个词,偶尔也使用其它词来描述人与动物的死亡。常用来描述植物消亡的词有更具体的含义,例如“枯萎”或“凋零”。从圣经的角度看,人类和动物的死与植物的死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人类和动物有相同意义上的身体的生死,而植物则没有这层意义上的生死。新约中描述“死亡”的词汇反映了旧约中的用法,即“死亡”仅用于人类和动物。值得注意的是,新旧约中共有三处经文在表面上提示植物能够死亡,但仔细考察发现圣经作者的意思,是要表达人与植物之间的某种基本的类比并显示其区别,而不是在说植物与人具有相同意义的死亡。这一切与地球年龄的关系将在下面讨论。
2. 最初的受造界会遭受肉体死亡吗?
这里需要考虑两个相关的问题:最初的被造物是否受制于死亡?换句话说,动物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会死吗?亚当和夏娃是否需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才可以不死?我们看到,关于这两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一个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会极大地影响其神学的整体一致性,以及他的神学与圣经经文的契合程度。
有人认为亚当被造的身体是会死的,他需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才能永生。[22] 大多数神学家认为上帝最初赋予亚当的肉身是不会死亡的,[23] 但斯特朗(Strong)是个突出的例外。他明确指出,亚当在被上帝创造的时候就被判死亡,[24] 但这很难解释上帝创造亚当时说“甚好”。此外,斯特朗的结论并非来自严谨的释经,而是让他的进化论信仰操控了他的释经。[25] 那些相信人类始祖被造时就会死的人,认为亚当和夏娃需要定期吃生命树的果子,才能不死。这意味着果子自身具有特殊的功效。同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自身也提供对邪恶的知识。但是,这种说法显然与上帝的属性相抵触。问题始于释经法,两种树必须一视同仁,我们不能将一棵树视为实物,而把另一棵视为象征。如果两棵树都是真实的树,如果两棵树的果实都自身具有赋予生命的能力或赋予知识的能力,那么这些能力一定是上帝赋予的。如果不是因为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如果仅仅是因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而认识了邪恶,那么,一定是上帝创造了邪恶!如果果子内含有某种东西,人吃它时会懂得道德之恶,那么,一定是上帝创造了果子里的道德之恶。这与上帝的属性背道而驰。有人用这一点暗示上帝有道德之恶的可能。这个悖论是无解的。但如果承认是吃善恶树果子这一违背上帝命令的行为带来了道德之恶,问题就解决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生命树,吃生命树的果子得永生,不在于果子本身,而在于上帝的应许。
有些人可能认为,动物和人类在亚当犯罪之前就死亡,正如我们现在从自然界所观察到的,受造物具有衰败的本性。[26] 这个衰变原理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或熵变定律,简单地说,就是系统用来做功的能量趋于减少。该论点认为,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衰变过程从创世之初就存在。因此,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动物甚至亚当和夏娃在被造之时,死亡过程必然已经开始了,因为这符合现在的物理学定律。例如,曼迪(Munday)分析说:“从创造周早期的情形就可以推断出某种广义的衰变过程的存在。当地与水分离,出现陆地和海洋的时侯,热交换一定就开始运行了。”[27] 另一个熵变的例子,是海水白天加热和夜晚冷却。事实上,今天几乎所有持年轻地球创造论的学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这种观点。当人或动物摄食并消化植物性食物时,或者当亚当犯罪前在伊甸园中工作时,熵变都会发生。亨利·莫里斯也承认:“在创世之初,即使我们称之为‘衰变’的过程诚然存在(例如消化、摩擦、水蚀、波浪的衰减等),这些过程也一定与该系统内别处所发生的‘增长’精确地平衡,使整个世界的熵值保持恒定。”[28] 因此,在创造周里,物理宇宙中就应该有熵的存在。但是,人类和动物的死亡与疾病,是否是犯罪之前熵变的一部分?是否是上帝“甚好”的创造的一部分?这却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应该指出的是,衰老的原因尚不明了。[29] 认为衰老是一种衰变过程,始于创造之初的说法,既无科学依据,也无圣经依据。因此,热力学第二定律肯定在人类犯罪之前就在运行,但这并不意味着犯罪之前的生物界(人类、海洋动物、陆栖动物及鸟类等有意识之物)存在衰败和躯体死亡。
3. 肉身死亡是从何时开始的?
现在来看圣经关于肉身死亡和自然之恶的起源的教导,并试图建立一个内在一致的神义论解释。保罗在罗马书8:19–21中指出,受造物被置于一个严厉的主管之下,称为“虚空”(ματαιότης)。不同版本的圣经把这个词翻译为“挫败”(NIV译作frustration)、“腐败”(NAS译作corruption)或“虚空”(KJV译作vanity)。当我们审视这个世界时,我们常常看到诸如蚊子传播的疾病、艾滋病毒、地震、海啸和飓风等许多事物,显明这世界不是一个值得久居的好地方。常常有人问:“上帝应该为此负责吗?” 根据圣经创世记1:31,上帝说他创造的一切都“甚好”,[30] 上帝在他的受造物上盖了验收的印章。然而,我们看见的大量证据,显明“恶”确实存在于自然界中。
把肉体死亡和自然之恶放在亚当犯罪之后的神义论与圣经文本及基督教神学相吻合。对于死亡和自然之恶起源的解释影响着我们对上帝的属性及其计划的认识。
首先牵涉到的是上帝的属性。假如上帝在创造之初植入了痛苦,那么上帝似乎乐于看到动物和人类遭受痛苦,并称其为“甚好”。如果这样,上帝就沦为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31]的原型,正好符合异教神明的属性。然而,圣经描述的上帝满有恩典、慈爱、怜悯,即便对动物也是如此。我们看见上帝对受造之物的关爱,始于他吩咐人治理全地(创世记1:26)。上帝设立安息日,使人养的动物可以歇息(出埃及记23:12)。他谴责虐待动物的人(箴12:10),即使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他也顾惜各样的生物(诗104:14-16和27-28)。在马太福音6:26-28中,耶稣也谈到了上帝对“田间百合花”和“空中飞鸟”的看顾。
这就是连贯一致且符合圣经的观点,当上帝在创世记1:31中说“甚好”时,他在描述一种田园诗般的状态。创世记1:29–30告诉我们,人、动物和鸟类当初都食素。圣经清楚地区分了被吃的植物,与吃植物的有生命的(30节用nephesh chayyah)受造物。人不吃动物,动物不相互残食。事实上,直到大洪水之后,人类才被允许食用动物(创世记9:3)。亚当犯罪之后,世界发生了巨变。现今的苦难,源于人的叛逆与上帝的审判,不是源自上帝创造的善工。自从罪玷污上帝的创造那一刻起,上帝就一直在寻找凭着信心归向他的人。这样的认识为护道者提供了向怀疑者介绍基督福音的机会。
第二是关乎上帝的计划。圣经中有很多经文讲述受造物将来会被更新。保罗在罗马书8:19-25中谈到了将来的更新。大多数释经者认为保罗指的是创世记第3章,[32] 因亚当的犯罪,自然界受到诅咒,其潜力因此被“削弱、束缚和限制”。[33] 保罗的意思是指:当基督完成他的救赎工作,使信徒身体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整个世界将会改变和更新。[34] 使徒行传3:21和歌罗西书1:15-20进一步说明了将来所有的受造物都要因基督的工作而更新。这两段经文都指出,由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万有都会得到“修复”与“和好”。并且,这种修复会发生在弥赛亚完全降临并在他的国中作王之时。“更新”一词表明受造物归于类似于以前的美好状态。
另一段关于将来世界更新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1:6-8。这里我们看到自然界的各种变化:1)现今的食肉动物将变为食草动物,与它们的掠物和平共处;[35] 2)现今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动物,将与人和谐相处。这是实实在在地回归到人类犯罪之前的景象。[36]
最后,启示录21-22讨论了新天新地里的更新。在第20章,上帝审判所有非信徒,罪从新世界中消除。在21章4节中提到:“不再有悲哀、哭号或痛苦,因为旧的事已经过去了。” 当今世界的哭泣和痛苦大多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如龙卷风、飓风、海啸、昆虫传播的疾病等,这些都会消失。启示录22:3 解释的原因是:不再有咒诅了。这里的观点很明确:这些不好的事情,源自于人的罪和上帝的诅咒。当不再有罪和诅咒时,田园诗般的美好世界便得以复原。
至于那些接受地球有亿万年历史之“科学”观点的人,以及哪些拒绝承认始祖犯罪并因此殃及所有受造物的人,他们必须把自然之恶(包括死亡、痛苦和灾难)归于创世记第一章,即上帝创造宇宙之时罪恶就存在。
但是,这种解释的各种版本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些将死亡、痛苦和灾难的根源归于创世记第一章的人,无法协调自然之恶和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关系。[37] 他们试图保留基督教神学的一些正统的立场,但他们却纳入了许多与他们所说的信仰相矛盾的教义。
最近有人尝试用进化论和东方神秘主义作为调和的构件。贝蒂(Betty)说,上帝创造的目的,是“创造与他自己迥然不同的人类,使他们能以独特的方式体验神圣的生活。”[38] 贝蒂这样描述上帝创造的过程:
“类似地,灵魂借着与身体(例如,原虫的身体)的结合而得到培育。当原虫死亡,与其身体结合的灵魂 ‘粒子’或‘波动’离开的时候,它就返回未分化的灵魂状态。但该粒子已经与之前不同了。它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单位的完整性,因为在这一早期阶段还有赖于与一个具体物质体的结合,但它比以前更接近于独立化。”[39]
实际上,这种神义论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给基督教神学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尽管它似乎自圆其说,但这种观点更多的是基于灵魂转世的观念,而不是基于圣经的教导。贝蒂试图提供走向“最大好处”的“最佳途径”,但她的观点与印度教或佛教的观点,似乎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40]
一些古老地球神义论试图将死亡、痛苦和灾难的存在解释为有益的,说它们也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它们未必会对人类造成不良影响。[41] 这似乎是基督徒协调神学与科学的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这里分析这种说法的几种形式。
伯纳德·拉姆(Bernard Ramm)是倡导这一观点的先驱之一。他指出:
“上帝没有说受造的世界是完美的,只是说它是好的。圣经中,天堂代表完美。地球是人类临时生存的地方,是好的,但不是天堂般的完美。受造系统必然地涉及一些在我们看来无目的[42]的特征(疾病、风暴、龙卷风等)……宇宙必须包含各种不同等次的良善。有一等良善是允许失败的良善。受造的完美宇宙必须具备可以败坏、可以在良善上失败的可能性。受造界并非在每个部分都是最好的,比如动物会死亡。但从整体上看,这依然是最好的创造。如果没有会朽坏之物或者邪恶之人,宇宙中就会缺少许多美好的事物。狮子之所以活着,是因为它可以捕食驴子。只有在不义存在的时候,复仇之义才值得赞扬。只有在不义的处境里,对痛苦的忍耐才被视为美德。”[43]
因此,根据拉姆的观点,一个好的创造不能没有动物的死亡,而人类只有在面对人的愤怒和仇恨时,才能看到并欣赏上帝的良善和慈爱。死亡、痛苦和灾难是上帝创造的自然秩序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有这样,人才能看到上帝的供应与自然之道不同。这样的做法是在论证之前就认定了结论是正确的。当一个人身患绝症时,你只需告诉他,振作起来吧,因为神造的世界原本如此,我们有什么资格质疑上帝呢?
在论及动物和人类在情感上的痛苦时,约翰·文翰(John Wenham)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动物所遭遇的最大痛苦是在与人类密切接触的时候。被囚禁的动物在见到残忍的主人时所感到的焦虑,在自然界中根本无法比拟,工业化养殖最糟糕的侧面和活体解剖也是自然界中所没有的。动物在其自然的栖息地也会经历恐惧,但那是健康的。我们自己也能明确地区分惊悚的体验和留下心理创伤的过度恐惧。一只健康的动物逃脱肉食者的猎捕,其兴奋感可能类似于一个胆大的年轻人从一次危险的恶作剧中逃离。”[44]
文翰说并非所有的恐惧或情感经历都应该被归类为“不良”,这并没有错。但是,根据最近的观察和实验,即使在其自然栖息地,动物也会经受巨大的情感痛苦。[45]
对于苦难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协调,还有一些其他的尝试。这些观点似乎提示,自然界存在的苦难在上帝整全的计划中有象征性的含意。他们提醒科学家或神学家,不要用对自然界的观察去直接解释上帝的属性。[46] 赖斯(Rice)阐述了象征性理解在自然界中的应用:
“我们通过科学方法获得有关自然界的事实资料。但是观察者经常不由自主地为自然界作出象征性的解释。这种解释之所以是象征性的,是因为它引导我们寻求一些例证来说明一些与被研究的自然系统之起源或运作没有真实关联的基督教主题。如果我们采用这种象征性的做法,那么我们能不能证明自然界有一个设计者,或者进化理论是否正确,便都无所谓了。良善的上帝与自然界的 ‘邪恶’之间表面上的矛盾也不存在了。大自然就像他的一部伟大的小说作品,小说家不需要赞同他书中人物的每一个举动,上帝也不需要认可他的故事里每一个参与者的全部行为。”[47]
这种方法似乎否定了圣经关于大自然反映出上帝荣耀和品格的清晰教导。如果我们使用这种护教学的思路,基督教就跟其它任何东方宗教一样了,因为我们必须否定(大自然中所展示的)客观物质现实与真理有任何关联。
赖斯还提出另外一种说法,即可以把受造界中的严酷现实当作逆境;即使在逆境中,上帝的祝福也存在。他说:
“然而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证明上帝在自然界中的创造机制,与人类经历中的创造机制是一样的。它们都可以理解为:逆境出祝福。当上帝运用自然法则时,自然界会出现诸如匮乏、疾病、伤害等各样逆境。但一般而言,个体生物或者整个种群,都能创造性地应对并胜过这些逆境。”[48]
虽然在始祖犯罪之后,上帝的确运用逆境来展示他的目的,但这引发了逆境起源的问题。赖斯和那些持相同观点的人,都必须把逆境当作上帝“甚好”的原始创造的一部分,这在神学上有问题。
加里·埃姆伯格(Gary Emberger)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神义论,他将天使的堕落视为邪恶的起因。
“天使的堕落带来了广泛的变化,如寄生虫、病原体、掠食动物、死亡等,扭曲了上帝的计划(可能是通过魔鬼引导的进化过程)。化石向我们展示,天使造成的混乱导致了众多的物种随时间而灭绝,甚至可能引发了恐龙的灭绝!基于以上所讨论的原因,上帝允许这些搅扰发生,而他又亲自做工,从邪恶中带出良善…… 在人类犯罪之后,死亡才被视为恶。因为这时人与上帝的关系破裂,死亡成了被弃绝之善。因此,所有的死亡,无论是过去(化石)、现在和将来,都被视为恶。”[49]
这种观点的某些观察,还是值得肯定的。首先,它的确提供了一种有内在一致性的神义论,因为它明确指出天使是自然之恶的道德起因,而不是上帝。其次,它能够对自然界的数据(如化石记录)做出相应的解释。但这个理论最大的障碍,是它远离了经文的陈述。圣经设立人作为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管理地球,并教导说是亚当的罪带来了自然之恶。圣经从来没有说天使的堕落给地和其余的受造界招来上帝的惩罚。这种观点也破坏了首先的亚当的罪与末后的亚当(即耶稣基督)的救赎之间紧凑的经文联系。因此,虽然将天使的堕落视为自然之恶根源的观点看似吸引人,但从圣经上讲,人类应该对自然之恶的起源负责。
威廉·德比斯基(William Dembski)在最近的网文中提出一种更新的说法。[50] 他相信古老地球是事实,并认为自然之恶在人类犯罪之前就存在。他称这种世界观为“我们的理性环境”,[51] 也就是说,他认为科学已经确凿地证明,地球和宇宙已经存在了数十亿年以上。但他也接受圣经关于人类的堕落招致上帝咒诅整个受造界的教导。在有力地推翻了其它古老地球神义论之后,他提出,由于上帝预知亚当的犯罪,他提前诅咒了人类以外的其它受造物。德比斯基注意到:
“这就要求上帝在他前边的行动所诱发的新事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提前行动。但此处的先后顺序并不是就时间或因果关系[chronos]而言的,而是按照上帝创造的目的和语义逻辑[kairos]。”[52]
也就是说,德比斯基认为,(基于新约中的两个希腊文词汇“chronos”和“kairos”),“时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们所经历的按次序展开的时间; 第二种是时机,与上帝的计划相关。德比斯基清楚地说,创世记第一章中的“日”不是时间顺序意义。“因此,创世记第一章不应该被解释为普通的连续的时间(chronos),而应被解释为与上帝旨意相关的时机(kairos)。”[53] 他将这种时间观比作基督是“在创世之前被杀的羔羊”(启示录13:8)。[54] 德比斯基的理论对许多神义论进行了改进,似乎回答了许多问题。
但是有三个问题,使得这一提议不能成为一个内在一致的基督教神义论。首先,他用启示录中“在创世之前”这一词语作为类比。如果这一词语确实修饰“被杀”(英文NAS,HCSB,和ESV译本中这一词语在文法上修饰“记在生命册上”),基督在创世之前只是在神的旨意和目的中被杀,而不是在实际的历史时空中。基督实际上是在亚当犯罪后很久才死的,而他的死亡所带来的益处是在他被钉死和复活后才开始的。[55] 假如按照德比斯基的类比理论,基督受死的益处从亚当和夏娃的时代就开始了。更重要的是,圣经中没有任何例子表明,上帝在一个人或一群人实际犯下罪行之前就对他们进行审判。如果这样做,就会与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公义律法相矛盾;认为上帝会这样做,会在大多数人心中带来反感,因为这是最不公正的,与圣经中揭示的上帝的本质相违背。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创世记第一章希伯来文的叙事文体。从创世记第一章一直到历代志下,其写作文体一直是历史叙事体裁,并没有明显的文体变化。[56] 假如创世记第一章的时机史观有别于连续时间史观,我们就应该能在文本中看得出来。在叙事体转为诗歌体的时候就是这样。例如申命记32章是诗歌体,但这种转变在文本中一目了然。如果我们接受了德比斯基的观点,那就意味着上帝在赐给我们经文时有一定程度上的欺骗。尽管德比斯基试图将自己的理论与“文学框架假说”区别开来,但这两种观点惊人地相似。[57]
最后一个问题在于对理性环境的完整理解和对圣经的时机论解释。在当前的理性环境下,人们认为死人复活的说法很愚蠢,因为人类的经验反复证明死人不能复活。所以对 圣经作者们都作证的耶稣的身体复活一事,也必须用时机论的方式来理解,而不是作为历史时空中的事件。对耶稣复活的这种看法与德比斯基在神义论上的说法非常一致,却违背了德比斯基所信仰的耶稣在身体上的复活,也摧毁了本于圣经的基督教。如果我们不相信按照字意理解的基督的身体复活,那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看来德比斯基只希望在神学的某些领域中将他对圣经的想法与当代的理性环境相融合,而在其它领域则不然。问题是他必须在其他领域做出某些个别诉求,才能保持自己体系的一致性。
还有最后一种神义论,让我们在解释上帝的话语或上帝的世界时,不应该纠缠于其运作的细节,而应该单纯地专注于上帝的爱。卡尔·克里恩克(Karl Krienke)如是说:
“上帝为什么允许进化这样一种想法?上帝在其创造的目的里允许罪恶和苦难,是为了成就真正的爱。由于这种选择,上帝最终承担了全人类的苦难!同理,为了赋予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爱,上帝也容许诸如进化之类的机制存在。进化的机制是一种自由,不需要上帝的介入。这对维护创造的目的,即自由选择和真爱,是必要的。因此,让我们专注于上帝的大爱,他的大爱是透过耶稣忍受的痛苦向我们展示的。让我们专注于欣赏科学、启示以及我们与他的和好与相交所揭示的上帝的伟大。”[58]
克里恩克的提议,似乎要使我们忽略周遭残酷的现实,转而注目上帝大爱的“温馨”。尽管对信徒而言,专注于上帝的爱是一项有益的功课,但是为了保持神学体系的一致性而忽视现实的资料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新时代运动呼唤所有人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现实”,而保罗的教导则与此相反:“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帖撒罗尼迦前书5:21)。
持上述各种神义论的人,都认为死亡和自然选择是上帝原始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认为自然选择(即淘汰弱者,适者生存)从创世之初就在受造界运行。然而,正如潘柏滔(Pattle Pun)所指出的,自然选择包含某些“邪恶”成份:
“正如创世记所述,动物和人类必须进食,这表明死亡发生在被食用的生物上。虽然在人类犯罪之前并没有提到食肉性,但这并不能排除动物死亡的可能性。化石记录显示,上帝用自然选择使最适合生存的物种繁衍,从而保障受造界的资源不致于耗尽,受造物的数量也得到控制。上帝允许自然选择在生态平衡中做细微的调整。”[59]
潘柏滔指出,自然选择涉及死亡、痛苦和流血。此外,对于生态系统中可能稀缺的资源也存在竞争。潘柏滔认为,这些事情可能是我们不情愿接受的,但是它们与人类堕落之前上帝“甚好”的原始创造似乎并不矛盾。潘柏滔的结论必须基于两个假设。第一,他必须相信植物的“死亡”跟人类的“死亡”含义相同。这一点,前面已经证明,是一个错误的假设。第二,他指出动物一定彼此相食。对此观点,潘柏滔没有明确的圣经支持,这也与创世记1:29-30中上帝对人和动物的食物所作的说明相违背。
有人可能认为世俗社会欢迎自然之恶/自然选择与基督教神学的整合,但实际上世俗主义者敌视这种做法。基督教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我们在“地球年龄的问题”上妥协,以便为科学护教者在世俗社会中赢得更好的传讲信息的立足点。但世俗社会对这种整合的企图心知肚明,根本不买账,而只想彻底歼灭任何基督教的残余思想。[60] 比如,琳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在贝内特(Bennett)的文章中流露出如下情绪:
“其后果是险恶的,正宗的科学和教学原则被恶意操纵。因为作者的最终目的,是诱使我们相信美国科学联盟(ASA)的创造神话。”[61]
虽然ASA的文字提倡一种神导进化论,但很明显,关于起源的问题,马古利斯和文章中的其他作者不希望看到任何有神的暗示。
世俗主义者之所以持敌对态度,其原因似乎是,当人们试图将自然之恶/自然选择与基督教神学相整合时,他们看到上帝品格上的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古老地球创造论与进化论保持距离,但该理论把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看作受造界的标准运作方式,而这二者正是苦难的主要根源。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指出了这一点:
“自然选择以最盲目、最残酷的方式,进化出新品种和越来越复杂精巧的有机体……生存竞争及淘汰弱者是一个恐怖的过程,与整个现代伦理学相悖。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一个非选择性的社会,是一个保护弱者的社会;这恰恰与所谓的自然法则相反。我很惊讶,一个基督徒会捍卫这样的观点,会相信上帝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这一过程,以达到进化的目的。”[62]
莫诺认为,圣经基督教不能既与自然选择整合,又不损及上帝慈爱良善的属性。尽管莫诺说的是 “进化论”,但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任何古老地球创造论。因为这些理论都接受同样的进化史观:即亿万年间有亿万动物患病、死亡、灭绝。莫诺指出,如果上帝是用这种方法创造的,那么现代社会比上帝更有德性。已故的哈佛大学地质学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也有同感,他写道:
“此外,用不恰当的人类术语来说,自然选择是一个非常低效、甚至残酷的过程。自然选择通过淘汰大量不适应的生命来塑造适应性,以大屠杀为代价来筑建有限的进化。自然选择是外因主导的“试错”理论——生物体尝试各种变异,而环境则否决几乎所有的尝试——而不是高效的、富有人性的、‘以目标为导向的内因主导论’(内因主导的过程是快速和仁爱的,但自然界没有这种智慧)。”[63]
世俗人文主义学者亚瑟·福克(Arthur Falk)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自然选择对那些只看到幸存产物的人来说似乎很好,但作为一个被设计的过程,它是愚蠢的。这个过程的残酷令人反感。”[64]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经常以科学数据的“真理”对有神论口诛笔伐。试看他的观点:
“自然界每年所遭受的苦难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在我写这句话的时刻,成千上万的动物被活活吞吃,更多的动物在恐惧中哀哼着逃命,另外一些动物被体内汹涌的寄生虫慢慢地吞噬,还有成千上万的各种动物死于饥渴和疾病。这是必要的过程。如果有资源富裕的时候,那就必然导致群体数量的增加,直到重新回到饥饿和痛苦的自然状态。”[65]
道金斯指出,自然选择或自然之恶(古老地球创造论者认为从创世记第一章就存在)是受造界的天然状态。如果这种观念得到彻底贯彻,必会产生可怕的伦理后果。人们可以认为 “强权即真理”或 “强者生存”的理念是建立在自然选择概念上的伦理体系的座右铭。如果我们把自然选择和/或自然之恶放在创世记第1章中,这种观念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伦理体系以及我们对上帝品格的看法。因此,护道者一旦接受了上帝创造了死亡和自然选择的观点并将之与基督教的神学相混合,那么在面对那些认为自然之恶与基督教的上帝不相容的非信徒时,他就不能给出一致的答案。
认为上帝创造了死亡和自然选择的伦理意义是很糟糕的,但更糟糕的是该观点对个人信仰的影响。哲学家戴维·赫尔(David Hull)观察到,这种通过自然选择的运作方式创造世界的神明,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信徒的拥护:
“无论进化论和自然历史数据所暗示的上帝是什么样子,他都不是新教的那位既不浪费也不匮乏的上帝。他也不是一个关心自己所造之物的慈爱上帝。他甚至不是约伯记中所描绘的那位可畏的上帝。加拉帕戈斯群岛(译者注:达尔文于1835年曾到这里考察地雀,是进化论发祥地)的神是冷酷、浪费、漠然甚至残忍的,肯定不会有人愿意向这样的上帝祈祷。”[66]
如果自然之恶是受造界的一部分,那么堕落与诅咒的观念也会受到质疑。福尔摩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注意到:
“生物学家相信物种有起源,但当他们开始阅读创世记时,开篇的故事就令他们感到不可思议。通常人们认为大部分的争议在于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有关六日创造的内容,但实际上第三章的问题更大,即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堕落,使整个地球受到诅咒。生物学家明白,前科学世代的人常用寓言和故事来表达思想。地球是借上帝之命从空虚混沌中产生的,目的是长出各样的生物种群。生物先从海里形成,走上大陆,进而繁殖而遍满全地,最后出现人类,人虽然是用尘土所造,但与其他生物有着明显的分别——这一切都与进化论的物种起源相吻合。真正的问题是大堕落:因着对人类犯罪的惩罚,自然界从乐园般的境界变得严酷恶劣。这完全不符合任何生物学范式。艰苦环境中的磨难并非发生于犯罪之后,也不是因罪而来的。无论罪人的出现带来了的多大的问题,生存竞争远在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67]
古老地球创造论的观点似乎放弃了基督教护教学的核心信息——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救赎失丧的人类和堕落的受造世界。
在基督教内部,当人们全面审查自然之恶的时候,甚至考核自然选择的良性作用时,他们的观点会明显地转变。约翰·费因伯格(John Feinberg)在专门考察苦难问题的一本书中指出:
“人类犯罪堕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上帝明言,在堕落的世界里,人类都会死亡。死亡都有原因,其中之一是疾病。有的疾病可能会出现在生命的早期,有的可能晚一些发生;有些疾病可能缓慢致死,有些则迅速致命;有些疾病是基于遗传,有些则是细菌感染。另外的死因可能是火灾、洪水、地震或饥荒。我认为根据圣经的教导,如果罪没有进入世界,自然过程就不会导致死亡。这意味着,造成所有这些看似不相关的自然之恶的最终原因,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68]
费因伯格是从整体上考察自然之恶的概念,而理查德·杨(Ric-hard Young)则重点关注食物链(暗含着自然选择的概念)。杨指出:
“大多数生态学家都会争辩,没有死亡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的所有生命形式,都依赖于其它生命的死亡。最值得关注的,是由死亡和腐烂所维持的复杂的动植物食物链。但是,在有神论的宇宙中,该定律也不一定是绝对的。圣经教导说,所有生命最终都来自赐生命的上帝,生命也靠他得以维系。死亡是生命的仇敌,而不是朋友。众所周知,生命部分地是靠其它生命的死亡来维系,但这当然不代表理想状态。犯罪后的人对创世记所记载的犯罪前的[69]和谐生态一无所知,科学界也无从知晓,但这并不能排除它曾经存在的真实性。”[70]
奈杰尔·卡梅隆(Nigel Cameron)阐述了调和主义的神义论如何破坏基督教神学的内在统一,他写道:
“为了解决问题,必须更改它的立论(就是如何将进化论纳入神学)。一方面,可以承认亚当从一开始——在他定意犯罪之前和之后——就受到圣经所称的诅咒的影响,但这推翻了罪与死的因果关系,也拆毁了救赎的基础…… 但是……上帝为人类居住而创造的世界是‘甚好’的。人是上帝创造中的桂冠,世界是专门为之预备的。整个环境的构建,是为亚当和夏娃预备理想的试用阶段。世界不是为堕落的前景而造的,更不是一开始就处于诅咒的影响之下。”[71]
创造的“完美性”似乎是完整的基督教神学或神义论的根基。[72] 以上三段引文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认为任何自然之恶或者自然选择的理论,都不能与堕落之前原始创造的“甚好”相吻和。
对于严谨的圣经学生来说,将自然之恶和自然选择的起源归因于人类犯罪和由此招致的诅咒,这才是维持神学一致性的唯一途径。那些将痛苦的起源放在创世记3:17-19中的人(例如费因伯格、杨和卡梅隆),就不会遇到前面的冲突。他们能够将自然之恶的概念与圣经的整全教导相调和。
结论
本章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研究了死亡的问题。我们研究了什么是死亡,结论是死亡就是肉体与灵魂的分离。另外,在圣经中有三处经文似乎提示植物的生死与动物和人类一样,但仔细研究后发现并非如此。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植物与动物和人截然不同。所以,尽管植物可以“枯萎”和“凋零”,但那不是圣经意义上的死亡。圣经清楚地表明,在上帝“甚好”的受造界里,动物和人类不会死亡。
我们还注意到,亚当被造时是永恆不死的。从创造的第一周开始,熵定律就开始运行,例如,在消化植物食物或呼吸空气的过程中,会有熵变。但熵变的危害却不存在于创世记第一章中。
最后,我们研究了动物和人类死亡以及自然之恶的起源时间。贯穿圣经的观点 “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罗马书8:19-21),始于创世记第三章,而不是第一章。多种古老地球神义论企图将亿万年纳入圣经,却都无法与我们看到的经文达成一致。只有相信上帝创造了一个没有死亡、痛苦和灾难的世界,我们才能建构出前后一致的神义论,才能有忠实于圣经的信息传给世人。
本文始于探讨过去:死亡从何而来?然而,过去却与未来息息相关,这关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彼得在彼得前书3:15中提到这种真实的盼望。如果基督教护教者接受圣经中关于罪恶、死亡、诅咒和救赎的教导,针对死亡的由来,他们就可以给出充分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接受所谓的“科学事实”,认为亚当受造之前动物界有亿万年的疾病、暴力、死亡和灭绝,我们就不能给出一个充分、连贯的答案,也不可能忠于圣经的教导。真正立足于圣经的内在一致的神义论要求我们摒弃广为接受的亿万年史观,以及与之相关的动物和人类的死亡、痛苦和灾难。
[1] 神义论就邪恶的起源问题向人们解释上帝之道。邪恶可以分为道德之恶和自然之恶。“二者虽然不同,但并非不相关,因为自然之恶是道德之恶的后果。”见John S. Feinberg,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1, 2nd ed.), 词条”Theodicy”。
[2] Hugh Ross, Creation and Time (Colorado Springs, CO: NavPress, 1994), p. 69. See a similar statement in John C. Munday, “Creature Mortality: From Creation or the Fall” JETS 35 (March 1992): p. 51–68.
[3] Webster’s New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Collins Word, 1976, 2nd unabridged edition), edited by Jean L. McKechnie, 词条“Death”。
[4] 例如创2:7, 6:15, 7:15。若单看“气息”一词,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如王上17:17, 传3:19, 3:21等。
[5] 详细讨论参见Jim Stambaugh,“‘Life’ According to the Bible and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Creation Ex Nihilio Technical Journal 6 (1992): p. 98–121, available at www.answersingenesis.org/tj/v6/i2/life.asp. 将植物归于“活物”的开端似乎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为有生命的物体定义时,主张寻求最小公约数。他发现:“所以,一切植物都被认为是活物,因为它们看来有能力遵循第一规则,表现出生长和衰败这两个方向相反的活动,而不是只生长或只萎缩,而是呈现两个方向上各向相当的活动,而且只要它们能够吸收食物,它们就得到营养而持续存活。” Aristotle, On The Soul, translated by W.S. Hett,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75.
[6] 其同义词描述人的死亡更形象,常常指肉体毁灭,却委婉地说“睡了。”
[7] Ludwig Kohler and Walter Baumgartner, The Hebrew and Aramaic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Leiden: E. J. Brill, 2001), p. 562.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HALOT.
[8] (1)动植物自然死亡;(2)暴力死亡,死刑;(神祗)变成必死的形象;(3)在描述将死的短语中,病危;(4)分词:将死的,死的;死人,将死的人,必死的人,死胎;献给死人的供物。旧约中唯一指植物死亡的在约伯记14:8。
[9] (1)单数:死亡,死;(2)庄严性复数:死亡;(3)最高级:极度;(4)危重病,流行,瘟疫;(5)拟人化:死亡;(6)死人的领域。
[10] 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edited by R. Laird Harris (Chicago, IL: Moody Press, 1980), 词条“מּות” by Elmer B. Smick. 下文中简称TWOT.
[11]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edited by G. Johannes Botterweck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词条 “מּות” by H. Ringgren. 下文中简称TDOT.
[12] Frederick W. Danker, A Greek-English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3rd edi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词条“θάνατoς”。该词在新约中出现约120次。下文中简称BDAG。
[13] BDAG, 词条 “νɛκρός”. 至于比喻用法,雅各用该词表示没有相应行为的信心毫无用处。该词在新约中出现约130次。
[14] Walter Elwell, ed.,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 demic, 2001, 2nd ed.), 词条 “Death,” by P.H. Davids.
[15] 参John E. Hartley, The Book of Job, NICO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8), p. 233–235; Samuel R. Driver,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Job Together With a New Translation, ICC (Edinburgh: T & T Clark, 1964), p. 127–128; 及 Robert L. Alden, Job, Th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TN: Broadman & Holman, 1993), p. 166–169.
[16] David J.A. Clines, Job 1–20,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TX: Word Books, 1989), p. 329.
[17] George R. Beasley-Murray, John,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Waco, TX : Word Books, 1987), p. 210; Raymond E. Brow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1–12, Anchor Bible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p. 472; Gerald L. Brochert, John 12–21,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TN: Broadman Publishing, 2002), p. 50; 及 Andreas J. Kostenberger, John, 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2004), p. 378.
[18] Kostenberger, Brochert, Brown, 与 Beasley-Murray 看到了这一点。又见 D.A. Cars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Pillar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1), p. 438; Leon Morris,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NICNT, rev. e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5), p. 527; 及 William Hendriksen, The Gospel of John,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1953), p. 196.
[19] 犹大将这两个词放在这节经文的末尾,显示他要读者严密注视这些假教师将面临的终极审判。
[20] Joseph B. Mayor, The Epistle of St. Jude and the Second Epistle of St. Peter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65), p. 43. 他的讲法说服力不大:“然而这不能解释这两个字首先指的是树木。这些不仅是不结果子的苗子,而且被连根拔出,这样活树也要死了。树木常用来比喻善恶人生的后果。”可见Mayor认为“死而又死”既指树也指人。然而,更好的理解是,“死而又死”指的是人的今生和来世,这一节里树木的功用只是作为一幅图画(连根拔出,丢在火里),而不是关于树木生死的命题陈述。
[21] Richard J. Bauckham, Jude and 2 Peter, WBC (Waco, TX: Word Books, 1984), p. 88. 又见Thomas R. Schreiner, 1,2 Peter, Jud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TN: Broadman & Holman, 2003), p. 466; Douglas J. Moo, 2 Peter and Jude,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96), p. 260; E.M. Sidebottom, James Jude, 2 Peter, The New Century Bible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2), p. 89–90; Charles Bigg,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s of St. Peter and Jude, ICC (Edinburgh: T & T Clark, 1978), p. 335.
[22] 参见 Henri Blocher, In The Beginning: The Opening Chapters of Genesis (Downers Grove, IL: IVP, 1984), pP. 124, 及 John C. Munday, “Creature Mortality: From Creation or the Fall” JETS 35 (March 1992): pP. 51–68.
[23] 参见See Norman Geisler, Systematic Theology: Sin-Salvation (Minneapolis, MN: Bethany House, 2004), p. P. 123; Wayne Grudem, Systematic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94), p. 516; J. Rodman Williams, Renew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96), 1:216; Millard J. Erickson, Christian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85), p. 613; 及 Gordon Lewis and Bruce Demarest Integrative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96), 2:195.
[24] Augustus Hopkins Strong, Systematic Theology (Philadelphia, PA: Judson Press, 1907), p. 527.
[25] Ibid., p. 527. 他的理由是:“科学表明肉体的生命包括衰败和失丧。”他也相信人的进化,因为这据说也是科学证明了的。
[26] 见Ross, Creation and Time, p. 69; Munday, “Creature Mortality,” p. 57; 或 Strong, Systematic Theology, p. 527.
[27] Munday, “Creature Mortality,” p. 57.
[28] Henry M. Morris, The Biblical Basis for Modern Science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86), p. 195.
[29] 参考Caleb E. Finch, Longevity, Senescence, and the Genom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的卷首语(p. x. ):“该项目其实始于我的博士论文里的文献综述。在论文中,我考虑了当时还属于异类的观点,即衰老可能不会普遍发生于全身的细胞中。哺乳动物衰老过程中的许多细胞变化是由激素或其他调节因子的变化而驱动的,而不是由于体细胞基因组的随机衰变或大分子生物合成而被随机搅扰,而且物种之间在衰老机制上可能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30] 见Jim Stambaugh, “Cre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meeting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PA., November 1995). 文章在线发表于www.answersingenesis.org/tj/ v10/i3/suffering.asp. 网络版省略了关于圣经模型与科学模型之关联的一节。
[31] 萨德以乐于虐待女人而闻名。虐待狂(sadism)一词就是萨德主义的意思。
[32] Douglas Moo,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6), p. 513– 514; John Murray,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68), p. 301–302; Thomas Schreiner, Romans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8), p. 435–438.
[33] William Hendriksen, An Exposition of Paul’s Epistle to the Romans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81), p. 268.
[34] John G. Gibbs, Creation & Redemption: A Study in Pauline Theology, (Supplements to Novum Testamentum v.26, (Leiden: E. J. Brill, 1971), p. 41. 又见Harry Alan Hahne, The Corruption and Redemption of Creation: Nature in Romans 8:19–22 and Jewish Apocalyptic Literature, Library of New Testament Studies, v. 336 (London : T & T Clark, 2006), p. 196. Hahne 说,“堕落之后,既然死亡成为自然循环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当今世界的生命模式就是虚空。受造界现今为腐败所奴役,而将来在信徒得荣耀之后,受造界将共享自由。”
[35] 有许多古老的故事讲述肉食动物将来会吃素,见Claus Westermann, Genesis 1–11 (Minneapolis, MN: Augsburg Publishing, 1987), p. 163.
[36] E.J. Young, The Book of Isaiah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1), 1:390. 又见Alec Motyer, The Prophecy of Isaiah (Leicester, UK: IVPress, 1993), p. 124–125; Otto Kaiser, Isaiah 1–12, Old Testament Library (Philadelphia, PA: Westminster Press, 1972), p. 160–162; John N. Oswalt, The Book of Isaiah Chapters 1–39, NICO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6), p. 283. 无论对千禧年持何种观点,这一点是大家都认可的 。这一段预言除了字面理解就无法理解。
[37] “道德之恶”的概念(由于人类的选择而产生的邪恶,例如谋杀、强奸、堕胎、抢劫)很容易被人类堕落所解释。然而,许多试图调和“自然之恶”问题的人却似乎喜欢采用个别诉求,其中许多说法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背道而驰。John Hick在他的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rev.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中就是这样做的。他辩称,我们的灵魂通过我们对道德之恶和自然之恶的体验而得以建造,使我们更加符合上帝对他的受造界的要求 。他认为自然之恶和道德之恶是这个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上帝让我们成长的计划的一部分。
[38] L. Stafford Betty, “Making Sense of Animal Pain: An Environmental Theodicy” Faith & Philosophy 9 (1992): p. 71.
[39] 同上,第73页。
[40] Yew-Kwang Ng, “Towards Welfare Biology,” Biology and Philosophy 10 (1995): p. 280–282.
[41] 支持这种说法的一种观点认为伊甸园只是局部的乐园,外面的世界与我们今天的世界类似,有死亡、痛苦、灾难。代表作有Arthur H. Lewis,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Garden of Eden” BETS 11 (1968): p. 169–175.
[42] 无目的论(dysteleology)是认为事物的存在并没有终极目的的哲学观点。
[43] Bernard Ramm, The Christian View of Science and Scripture (Grand Rapids, MI: Ee- rdmans, 1954), p. 93–94. 这种观点与John Hick的“灵魂建造”说法类似,也让人不免要问关于动物最初吃什么的问题。更多讨论见Jim Stambaugh, “Creation’s Original Diet and the Changes at the Fall,” Creation Ex Nihilo Technical Journal 5 (1991): p. 130–138, www.answersingenesis.org/tj/v5/i2/diet.asp.
[44] John W. Wenham, The Goodness of God (Downers Grove, IL: IV Press, 1974), p. 205. 文翰明白地说,伊甸园外面的世界与我们今天所见的世界是一样的。注意他在169-167页的说法:“当人类脱离了造物主,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时,这就带来了损害。当人类与造物主连接,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就享受到神圣的庇护,正如耶稣可以在风暴中安眠。地球是人类优裕而宏伟的家园,但是自己走出伊甸园就太危险。”又参见Theodore Wood关于自然界“表面”残酷的解释:“对于动物来说,(世界)是无休无止的大战场,一场庞大的、没有终结的血雨腥风。为了一只动物的生存,千万只动物走向死亡,而赢的总是强者。被强加于动物身上的各式各样的死亡,其恐怖和痛苦似乎足以为自然界的残酷定罪。”(Theodore Wood, “The Apparent Cruelty of Nature,” Journal of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Victoria Institute 25 (1891–92): p. 254).
[45] 见Stambaugh, “Cre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p. 17–36.
[46] Stanley Rice, “On the Problem of Apparent Evil in the Natural World”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39 (1987): p. 156. 这样的提议带来更多的问题,因为经文明讲自然界是上帝荣耀的图画,所以反映了他的属性。
[47] Rice, “Apparent Evil,” p. 156–157.
[48] Stanley Rice, “Bringing Blessings Out of Adversity: God’s Activity in the World of Nature”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41 (1989): p. 3. 赖斯在第6页上讲这一模型在除了年轻地球创造论以外的各种神学系统中都适用。
[49] Gary Emberger, “Theological and Scientific Explanations for the Origin and Purpose of Evil”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46 (September 1994): p. 157.
[50] William A. Dembski, “Christian Theodicy in Light of Genesis and Modern Science” Version 2.3 March 17, 2007, 38. www.designinference.com/documents/2006.05.christian_theodicy.pdf, accessed July 29, 2008.
[51] Dembski, “Christian Theodicy,” p. 1–2.
[52] 同上,第37页。
[53] 同上,第39页。
[54] 同上,第46页。
[55] 这并不是提议旧约信徒不能得救。他们得救与我们一样,靠着相信上帝的应许。
[56] 某些经卷的部分段落转为诗歌体(如申32),但是整体上讲,历史书是按照希伯来历史叙述写的。
[57] Meredith Kline在其著作中屡次提示“框架”观的优势在于它强调神学意义而非历史意义,这正是德比斯基所提议的。
[58] Karl Krienke, “Theodicy and Evolution”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44 (December 1992): p. 257.
[59] Pun, “Progressive Creationism,” p. 17. 潘似乎以生物学对生命的定义为准则,但是圣经的定义不包括植物和单细胞生物。见Jim Stambaugh, “ ‘Life’ According to the Bible and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Creation Ex Nihlio Technical Journal 6 (1992): p. 98–121, www. answersingenesis.org/tj/v6/i2/life.asp. 此外,某些种类看起来像肉食动物,但不一定是。见Stambaugh, “Creation’s Original Diet,” p. 133–136, 及 David Catchpoole, “Skeptics Challenge: A ‘God of Love’ Created a Killer Jellyfish?” Creation 25:4 (Sept. 2003), p. 34–35, https://creation.com/skeptics-challenge-a-god-of-love-created-a-killer-jellyfish.
[60] 一个例子是对美国科学联盟(American Scientific Affiliation)《在争议中讲授科学》(Teaching Science in a Climate of Controversy)小册子的反应。见William Bennett, ed., “Scientists Decry a Slick New Packaging of Creationism,” Science Teacher 54 (May 1987): p. 36–43.
[61] Bennett, “Scientists Decry,” p. 40.
[62] Jacques Monod, “The Secret of Life,” an interview with Laurie John,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 June 10, 1976, 被引用于 Henry Morris, That Their Words May Be Used Against Them (San Diego, CA :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7), p. 417.
[63] Stephen Jay Gould, “The Power of This View of Life,” Natural History 103 (June 1994): p. 6.
[64] Arthur Falk, “Reflections on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Humanist 55 (Nov/Dec1995): p. 24.
[65] Richard Dawkins, “God’s Utility Func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273 (November 1995): p. 85.
[66] David L. Hull, “The God of the Galapagos” Nature 352 (August 8, 1991): p. 486.
[67] Holmes Rolston, “Does Nature Need to be Redeemed?” Zygon 29 (June 1994): p. 205.
[68] John S. Feinberg, The Many Faces of Evil: Theological Systems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 1994), p. 147–148. 同样的认知也见于D.A. Carson, How Long, O Lord?: Reflections on Suffering and Evil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0), p. 51–68.
[69] 英文prelapsarian(犯罪前)和postlapsarian(犯罪后)。
[70] Richard A Young, Healing the Earth: A Theocentric Perspective o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ir Solutions (Nashville, TN: Broadman & Holman, 1994), p. 144–145.
[71] Nigel M. de S. Cameron, Evolution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e (Exeter: Paternoster Press, 1983), p. 66, 括号内的短语是本文作者加上去的。虽然卡梅隆的主题是进化论,但该论证同样适用于任何古老地球模式。
[72] 关于受造界的完美性,见Norman L. Geisler and Ronald M. Brooks, When Skeptics Ask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0), p. 61–62. Norman L. Geisler, Systematic Theology: Sin Salvation (Minneapolis, MN: Bethany House, 2004), p. 17–26. 讽刺的是,Geisler倾向于接受地球的古久历史。他似乎不认为化石记录中亿万年的死亡与他的完美创造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