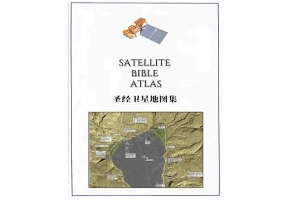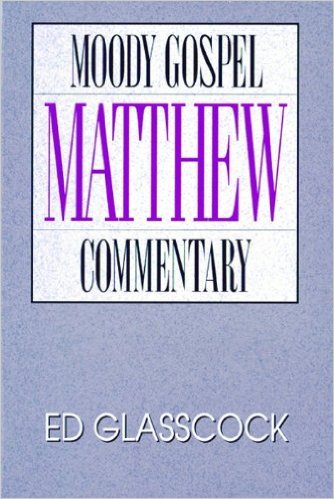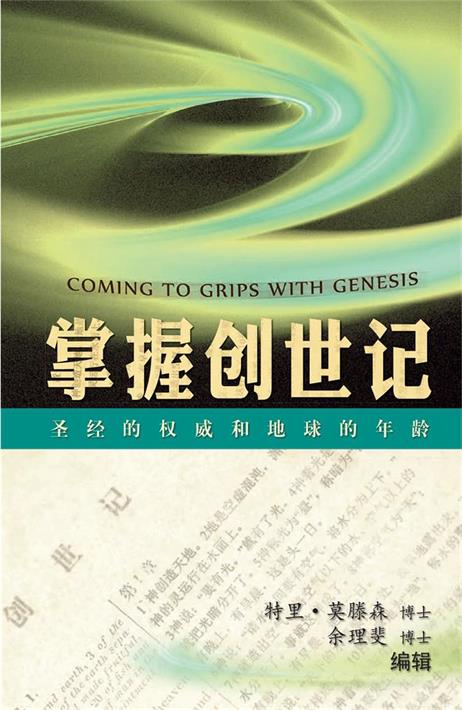
第十章:创世记第5和第11章的家谱有空缺吗?
特拉维斯·弗里曼(Travis R. Freeman)[1]
自19世纪以来,旧约学者普遍表示,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的家谱包含世代和时间上的空缺,因此不能像詹姆斯·乌雪(James Ussher)那样用家谱来制定年代表。这些学者中大多数相信族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动,也就是说,名字经常会被增减或改变形式。他们说,由于地球比乌雪所认定的要古老,因此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一定有一些名字在圣经的传承过程中被省略掉了。因此,在他们看来,这些家谱与学界普遍接受的古老地球、古老人类并不矛盾。圣经家谱当然不能用来确定创世或洪水的日期。
然而,这种观点令一些保守派圣经学者深感不安,他们坚持认为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清楚地记述了从亚当到亚伯拉罕的连续的、无间断的家谱和年代。他们认为,这些文本的措词就是为了排除遗漏和空缺。在他们看来,提出这样的空缺违反了对这些段落直截了当的阅读和圣经无误的观点。因此,他们说,乌雪根据家谱确定创世是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值得现代学者效仿。
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呢? 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里的家谱在传承的过程中是否有流动性? 是否有的名字被省略了,以致于现在这些家谱在世代和时间上有空缺呢?
本章中使用的“流动性”一词是指从家谱中省略或添加名字的做法,或者指名字的拼写被更改。名字被省略时,流动性导致压缩,就是名单被缩短了。有时,名字的省略会形成对称性,就是说,在分段家谱的每个部分中,名字的数量相等。我用术语“年代家谱”(chronogenealogy)和“非年代家谱”(non-chorono-genealogy))来描述本文讨论的各种家谱的体裁。
非年代家谱观
历史批判学者
许多现代的历史批判学者认为创世记第5章的家谱不是准确的历史记录。他们认为这是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传奇英雄名单(国王名单、智者名单、英雄名单,或部落祖先名单),在代代相传的漫长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流动性,以至于其大部分或全部的历史和年代价值(如果原先有的话)已经遗失了。他们对创世记第11章的家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创世记早期的家谱(如果曾经是家谱的话)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它们包含世代的遗漏或空缺。
克劳斯·韦斯特曼(Claus Westermann)认为,创世记第5章中列出的十个名字来自于某个古代部落关于其原始祖先的口传历史。[2] 这段口传历史在其早期被划分为不同的节段,并且每个节段是独立传承的。韦斯特曼在创世记4:25-26(亚当、塞特、以挪士)中找到一个节段(或其中一部分),又在4:17-18(该隐、以诺、以拿、米户雅利、玛土撒利、拉麦)中找到另一个节段,认为这些节段被耶和华派(J)使用了。他认为创世记5章的祭司派(P)也使用了这两个节段,因此创世记4章和5章里的名字最初是相同的。他认为这两个节段在传递过程中的流动性解释了创世记第4章和5章在名字拼写(该隐/该南、米户雅利/玛勒列、以拿/雅列、玛土撒利/玛土撒拉)之间的差异以及名字顺序(该隐、以诺、以拿、米户雅利与该南、玛勒列、雅列、以诺)。韦斯特曼还争辩说,P把传说中的人名压缩成十个,是因为这个数字在古近东“家谱中是典型和正常的”。[3]
犹太神学家那鸿·撒珥纳(Nahum M. Sarna)也认为创世记第5章中的十个名字是压缩的结果。[4] 他指出古文献记录中还有其他的十人序列(Berossus的大洪水前的国王名单,路得记4:18-22和历代志上 2:5,9-15中法勒斯至大卫的家谱,以及创世记11:10-26中闪至亚伯拉罕的家谱),借以说明在圣经时代的世界中,十代家谱是人为的和标准的。在此基础上,他说:“结论是无庸置疑的:这里(创世记第5章)就是对历史的刻意的、对称的格式化。”[5]
格哈德·冯·拉德(Gerhard von Rad)说,创世记第4章和第5章中的两个家谱“显然[来自]同一个名单。”[6] 他的证据就是名字的相似性。流动性解释了名字拼写和顺序的不同。他认为,圣经家谱的人物来源可能是从巴比伦传说中大洪水前的十个神话性质的国王流传下来的,尽管希伯来文版本将这些人扮为先祖。因此,当冯·拉德(von Rad)提请人们注意“ 【第5章】对安排人类和世界的年龄作出的努力”[7] 时,他的意思并不是这些经文揭示了他们的实际年龄。经文的神话起源和传承的流动性排除了这种字面解释。他的意思仅仅是说创世记作者提出了一种虚构的线性历史观,来挑战许多古代异教所倡导的循环历史观。[8]
以法莲·斯派瑟(E. A. Speiser)看到创世记第4章与第5章的名单之间的相似之处,就推测这两个名单是来自一个共同的美索不达米亚源头。他指出苏美尔人传说中大洪水前的十个国王是可能的来源,并提议该传说在传承过程中被大幅度“修改”,以至于原来的名字完全被新名字所取代了。[9]
约翰·吉布森(John C. Gibson)同样指出古代传说是创世记第4章和第5章家谱的共同来源。他认为创世记第5章中的名字数目可能反映了苏美尔传说中大洪水前的国王数目。[10] 关于创世记第4章和第5章中的名字,吉布森指出:
“希伯来传说中的古代英雄们被聚集在一起,呈现为亲属关系,并加了些小说明,使之成为更完整的故事。希伯来文名单可能是以色列的讲故事者或“故事歌手”用来帮助记忆的。人名的背后是一个古老的希伯来史诗循环,反映了早期希伯来人对世界之初和文明兴起的看法。”[11]
按照吉布森的说法,创世记第5章的人可能并不是直系亲属。随着希伯来史诗循环的发展,他们的名字只是被添加到讲故事者的名单中而已。
杰克·萨松(Jack Sasson)也假定创世记第4章该隐的族谱和创世记第5章塞特的族谱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名单。萨森进一步认为希伯来人经常将重要人物移至族谱的第五和/或第七个位置以强调他的重要性。例如,他指出,在创世记的家谱中,以诺是亚当的第七世孙,希伯是以诺的第七世孙,亚伯拉罕是希伯的第七世孙。对于萨森来说,这样的例子证明了流动性,因此,他排除了从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得出准确年代的可能性。[12]
罗伯特·戴维森(Robert Davidson)写道,创世记第5章中的十人名单让人想起美索不达米亚国王的名单,这暗示了前者对后者的名字和十人形式的依赖。[13] 他进一步指出,在巴比伦传说中,西帕尔的国王恩梅杜拉纳(Enmeduranna)是第七位国王,而以诺(Enoch)名字的开头与他相似,也是排在亚当之后的第七位。七被认为是神圣的数字。沙玛什(Shamash)对恩梅杜拉纳有特别的恩宠,并通过向他揭示天地的奥秘来祝福他,就像希伯来的神对以诺也特别地爱,并以把他带到天堂来祝福他。以诺可能在活了365年后离世,这个数字可能与太阳神有关。[14] 戴维森的观点很清楚:首先,以诺的故事依赖恩梅杜拉纳的故事;其次,古代家谱中的第七位是为杰出人物保留的,通常会将他的名字从其实际位置或本不在家谱中的位置移至第七位。因此,流动性在创世记第5章的形成中起主要作用。为达到标准的十人名单形式,人们做出了省略,并且出于神学目的改变其顺序。
福音派学者
另一组当今的神学家(主要由福音派人士组成)认为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族谱是准确的历史记录,但名单中省略了一定数量的名字。因此,他们在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历史性上不同于刚刚讨论过的神学家们,但他们同意家谱有流动性,而且因为流动性而导致了空缺。这一派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19世纪晚期威廉·格林(William H. Green)在这一观点上的论证。[15]
车理深(Gleason Archer)认为,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都记录了恰好十个世代,这表明有名字被省略以达到一个预定的对称性。他指出马太福音第1章是另一个家谱的例子,在那里为了对称起见省略了一些名字,可能是为了好记。阿彻在承认创世记家谱中存在遗漏的同时,坚持认为被遗漏的名字必须少于被列出的名字。为了支持这一论点,他指出,圣经中其它的长家谱名单中删除的名字从来没有比使用的名字更多。例如,马太在耶稣的祖先名单中列出的至少是省略的八倍。基于同样的根据,阿彻认为,人类不可能像一些福音派人士所建议的那样,有近20万年的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意味着从创世记家谱中删除了大量亚当的祖先,这是不可接受的。[16]
肯尼斯·基勤(K.A. Kitchen)怀疑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家谱的连续性,并给出了三个理由。[17] 首先,考古证据表明埃及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出现得更早。[18] 这些年期与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连续”读法相冲突。其次,“生”一词可以指后代而不是儿子。其三,两个名单都有十个名字,这种对称性表明其格式化。
戈登·文翰(Gordon Wenham)否认塞特家谱依赖于该隐家谱或苏美尔君王名单,却接受创世记第5章有世代和历史空缺的想法。[19] 不过他强调说,“……希伯来原文没有暗示在这个家谱中父子之间有很大的间隔”。他这样做是被迫于“考古学的发现”和“历史学的问题”,因此他把亚当置于“非常遥远的时代”。[20]
德里克·基德纳(Derek Kidner)提议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的人名是挑选出来的历史标志,而不是连续的链条。他在马太福音第1章和现代阿拉伯部落的家谱记录中找到了这种做法的例子。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作者都没有给出世代总数,也没有让人觉得先祖们的生活年代有很大的重叠,这使基德纳怀疑家谱可能不是连续的。他并没有明确承认考古学发现强化了他的怀疑,但他认为考古学“证明了”人类文明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
约翰·戴维斯(John J. Davis)认为创世记第4章和第5章的家谱之间的差异远大于相似之处,因此创世记第5章的名单是真实的人,而不是根据创世记第4章的名单捏造出来的。[21] 但他相信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只提到了大洪水前的关键人物,而不是每一代,这有几个理由:首先,两个名单的末尾都没有给出世代总数;其次,圣经里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提到这两个家谱所跨越的年数;其三,家谱里面包含了一些与年代无关的数字;其四,路加福音3:36列出了一个名叫该南的人是亚法撒的儿子,但创世记第11章却省略了他;其五,如果字面阅读创世记第11章的经文,闪比亚伯拉罕更晚离世;其六,根据地层考古学、陶器类型学和碳14鉴定进行的考古计算表明,大洪水后的人类文化出现在公元前12,000年左右,这就把大洪水发生定在公元前18,000年左右;其七,名单带有格式化安排的痕迹。因此,戴维斯怀疑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有“相当大”的空缺,但他认为这些空缺没有大到足以容纳进化论地质学家对人类和地球年龄的“过度高估”。[22]
维克多·汉密尔顿(Victor P. Hamilton)争辩说,该隐的后代名字与塞特的后代名字在顺序和拼写上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显然与后一个名单的写作无关;也就是说,他们有不同的来源。塞特的后代与任何苏美尔人的洪水前国王名单也无关,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体裁。塞特的后代构成了一个家谱,而苏美尔的序列构成的是一个君王榜。因此,汉密尔顿认为没有理由怀疑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所记载的是实际的历史人物,是实际的塞特后裔和闪族后裔。[23] 然而,他怀疑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并未记录每一代人。以下引文表达了许多福音派人士的想法:
“【最近的研究表明】创世记中的这些早期家谱源于旧巴比伦时期西闪族部落的原型家谱,他们的每一个谱系通常包括十代。根据这一观察来理解创5,就使得我们相信,创5中的名单不必理解为连续的序列。因此,不能将这些数字加在一起来推算人类的年龄。这些经文应当理解为,我们这里得到的是对称的家谱:洪水前十代(创5),洪水后十代(创11)。因此,当创5说“ X生了Y”时,这可能意味着“ X的后代最终传到了Y”。[24]
肯尼斯·马修斯(Kenneth A. Mathews)认为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的人分别是塞特和闪的真实后裔,但他也认为家谱在传承过程中发生了流动性,导致了两个压缩的、对称的家谱。[25] 马修斯指出,传统的理解是这些家谱包括了从亚当到亚伯拉罕的每一代人,并且“经文中没有明确表示有其他的可能性。”[26] 然而,他不相信没有省略,因为“这会留给我们很短的时间跨度来容纳我们所了解的人类历史。”[27] 以诺在创世记第5章中排第七位,与波阿斯在路得记第4章中所提到的大卫的家谱中的位置相似,这也向马修斯表明,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是经过格式化的,因为七这个数字代表了上帝的特别祝福。尽管马修斯完全接受这些创世记的家谱中有空缺的想法,但他坚持认为,这些空缺不可能容纳下进化古生物学所需的长久年代,因为如此巨大的空缺无视圣经的惯例,这惯例就是列出的世代比省略的要多。因此,在马修斯看来,人类仅比乌雪(Ussher)计算的要早几千年。
罗纳德·杨布洛德(Ronald F. Youngblood)提供了在创世记第5章中出现流动性的另一种可能的方式。他提议其中的名字可能是洪水前著名的朝代名称,而不是个人,其它不太重要的朝代想必被省略了。在这种解释中,那些数字与统治者在位的时间有关。杨布洛德没有说出他所指的是哪一组数字,或者其它数字组合可能的含义。他只是简单地得出结论说,这种解释暗示创世记第5章中的记录中有巨大的空缺。[28]
非年代家谱观总结
总之,认为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家谱中因流动性而存在空缺的最常见论证如下:(1)创世记第4章和第5章中的家谱太相似,它们肯定是从共同的源头演变而来的。(2)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的家谱呈对称的十代形式,而且重点人物放在第七位,这表明它们是经过格式化的,跟随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国王、圣人和祖先名单的传统。(3)对经文的无空缺解读会导致先祖们的生活年代有太多的重叠。(4)经常重复使用的公式“X生了Y”应解释为Y是X的后人。(5)按照圣经以外的证据,人类起源的时间比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无空缺解读要早得多。
年代家谱观
一些现代学者认为,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不仅包含实际的历史人物的名字,而且这些名字构成了从亚当到亚伯拉罕的连续(没有遗漏任何世代的)线性家谱。尽管他们爽快地承认流动性造成的世代空缺是古代家谱中相当普遍的现象,但他们认为,虽然某些家谱中由于流动性而出现空缺,但这并不能证明所有的家谱都有由于流动性引起的空缺。他们将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家谱视为古代家谱中省略世代的普遍模式的许多例外中的两个。
体裁的重要性
在对早期圣经家谱的分析中,已故的撒母耳·库灵(Samuel Kulling)一开始就承认许多圣经家谱,例如以斯拉记第7章和马太福音第1章中的家谱,都存在空缺。但是,在他看来,圣经家谱具有不止一种体裁。一种类型的家谱(例如,以斯拉记第7章)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某人对某项职务、职位或遗产的权利,因而不必包括每一代。而另一种类型加入了足够的详细信息,尤其是数字资料,表明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年代表,尽管可能也有其他的目的。库灵在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中找到了许多这种类型的例子,那些简短的段落说到以色列或犹大的国王在他的儿子(或篡位者)继位之前统治了若干年。当这些段落组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以色列和犹大的20代年代,并且经常被神学家用来确定重要事件的日期。创世记中的一些经文段落给出了以撒出生时亚伯拉罕的年龄和雅各出生时以撒的年龄,也是这种体裁的例子。这些关于先祖时期的经文也通常被用来确定年代。[29]
然后库灵设问:创世记5章和11章的家谱属于哪一类? 他回答说其中的许多数字,尤其是父亲的生育年龄,肯定将这些家谱定为第二类,即年代家谱。因此至少就圣经本身的证据而言,它们应被理解为没有遗漏。[30]
布瑞法德·查尔兹(Brevard S. Childs)也认为体裁是理解创世记家谱本质的重要因素。[31] 他在创世记中发现两种家谱:垂直(线性)和水平(分段)。他在11个“后代记、来历”(Toledoth,历史记录)的背景下分析了这两种类型的性质和功能,他说这些“后代记”形成整卷书的结构并将其统一为一部连续的历史(与韦斯特曼的观点相反)。在这部历史中,水平家谱的功能,例如,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家谱,以实玛利后代的家谱和以扫后裔的家谱(分别是在创10、25和36章),显示了人类在特别拣选的家族之外的普遍繁衍。另一方面,垂直家谱(主要是创5和11)则关乎被选择的蒙祝福的家族,并“追溯从亚当到雅各的不间断的一系列后裔,同时也为对先祖的传统叙述提供了一个框架。[32] 查尔兹没有说他是否相信这些垂直家谱中包含的数字是准确的,是否适合确立亚伯拉罕之前的年代,但他的这句话表明他相信创世记的作者的意图是列出一个连续的、没有空缺的家谱,而且圣经经文本身中并没有任何需要别样解释的依据。
另一位强调家谱体裁识别在解释过程中的作用的学者是大卫·罗斯韦尔(David T. Rosevear)。[33] 与库灵一样,罗斯韦尔描述了圣经中线性家谱的两种主要类型。首先,有不完整的家谱,其中省略了几代人,古代作家在不必要包括每一代人就可以达到目的时就会采用。相反,有完整的没有省略一代的家谱,圣经作者有时用来建立他们叙事的时间顺序框架。根据罗斯韦尔的说法,塞特和闪的家谱名单带有后一种家谱的标记,尤其明显的是它们一致地记载了每两代出生之间的年限。再次,与库灵一样,罗斯韦尔引用与以色列和犹大的君王有关的经书,作为这类家谱的其他例子。
詹姆斯·乔丹(James Jordan)同意库灵、查尔兹和罗斯韦尔的观点,即在确定家谱中是否存在因流动性而造成的空缺时,体裁识别很重要,但他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他认为,实际上不仅有两种类型,而是有许多不同的家谱形式。[34] 例如,他识别出连续和不连续的家谱、年代家谱和非年代家谱、只省略了几代的家谱和几乎省略了所有代的家谱,仅仅是一个名单的家谱和带有历史和传记记录的家谱、2代和20代的家谱、线性和分段家谱、等等,每种都有自己的功能和特点。乔丹分析说,创世记的作者有如此众多的形式可以使用,至少可以说,除非他相信自己的名单是完整的、没有空缺的,否则他不太可能选择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形式,仔细地叙述每一代之间的年数。乔丹进一步分析说,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包含详细的年代信息这一事实就证明这些经文属于与世代空缺的观念直接对立的体裁。他认为,说这些经文中有空缺是完全忽略了它们的体裁。[35]
大多数否认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家谱因流动性而造成空缺的神学家都意识到,尽管他们的“体裁论证”听起来合理,但是只有在他们能够为那些支持空缺的证据提供自己的合理解释时,体裁论才会为人相信。他们如何回答因流动性而产生空缺的五个主要论证呢?
论证1:创世记第4章和第5章名单的相似之处
第一个论证说,创世记第4章和第5章家谱的名字和顺序是如此地相似,以至于它们一定是从同一个原始家谱演变而来的。它们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流动性,从而产生了两个不同但相似的名单。反对这种说法的神学家们回答说,这两个名单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此外,他们说,任何相似之处都可能是由于古代世界中大家庭都倾向于重复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名字。
文翰指出,该隐的家谱涵盖了七个世代,但只有六个名字与塞特家谱中的名字有相似之处。在这六个中,四个需要更改或添加至少一个辅音才能变得相同。仅有的两个完全一样的以诺和拉麦,也可以根据对他们的生平记载区分开来。创世记第4章的拉麦谋杀了一个年轻人并以此为荣,而创世记第5章的拉麦则在他儿子的命名中承认上帝。经文对第一个以诺并没有说什么,但是第二个以诺与神同行了至少三百年,然后被神超自然地带进了天堂。流动性无法解释如此巨大的特性差异。因此,两个以诺和两个拉麦是不同的人,实际上根本不匹配。文翰进一步指出了这两段经文的不同风格。该隐段落是一个简单的家谱,而塞特段落是一个年代家谱。他认为,这些不同的风格指向两个截然不同的原始名单。[36]
马修斯同意文翰的观点,但提出了更多的他认为不能归因于流动性的差异。[37] 创世记第4章似乎对洪水一无所知,不像创世记第5章。创世记第4章在拉麦之后有一个分段式家谱,并提到了他的女儿拿玛,也与创世记第5章不同。创世记第5章遵循一致的公式给出先祖的生育和死亡年龄,但创世记第4章的语言公式化程度低得多,并且完全没有年龄。塞特的家谱与创世密切相关,但该隐家谱的背景是被逐出乐园和家庭。[38] 因此,马修斯得出结论,这两章反映了不同的源头;即不同的原始名单。
汉密尔顿解释了名字的相似性。建议说古代两个人在同一时间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名字并不少见,尤其是在同一个大家庭中。历世历代,包括今天在内,父母都经常以叔伯、堂兄弟等人的名字给孩子取名。[39] 汉密尔顿似乎承认威尔逊理论的有效性,即在古代家谱的运用中,形式取决于功能。也就是说,家谱经常被修改以更好地发挥其作为社会或政治工具的目的。汉密尔顿也同意威尔逊的观点,认为创世记第4章的作用是展示罪的传播,而创世记第5章则强调了神的形像的传递。不过汉密尔顿指出,威尔逊未能展示改变世代数、更改姓名及其顺序如何使这两处的家谱更好地发挥其功能。[40] 没有这类信息,汉密尔顿认为就没有理由假设它们出自同一原始名单或因为流动性而导致世代空缺。
在结论为创世记第4章和第5章的名字来自不同原始名单的研究中,大卫·布莱恩(David T. Bryan)的研究最为详尽。[41] 布莱恩认为创世记家谱在名字的拼写方面存在流动性,但与本节提到的其他学者一样,他深入而有力地论证:创世记第4章和第5章名单的相似性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共同的原始名单。以下是他的意见的总结。
布莱恩看到了流传到现在的这两段经文中的名字之间惊人的相似性。他指出,大多数学者对这种相似性的解释都是说这两段经文是基于同一个原始名单,而这个原始名单可能是苏美尔国王或重要祖先的名单。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有几位学者为相似性提出了另外的解释。例如,威廉·格林在1895年提议,这两个家谱中的名字在从原来的语言翻译成希伯来语时可能发生了部分混淆或同化。[42] 布莱恩指出,最近芬寇斯坦(J.J. Finkelstein)[43] 和威廉·哈罗(William W. Hallo)[44] 提出了类似的理论。以苏美尔国王名单和发音类似的洪水前圣贤名单(apkallu)为例,他们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截然不同但密切相关的名单逐渐趋于相似,他们因此提议该隐和塞特的家谱也是如此。
布莱恩认为有一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该隐和塞特家谱的名字之间相似性太明显,不可能是巧合,因此流动性一定发生了。流动性要么使一个名单发展为两个,要么使两个名单变得更像一个。布莱恩选择后一种理论。他指出,在已知的两个名单发生混淆的例子中,通常两个名单不相似的地方比相似的地方更多。在一个名单演变为两个名单的情况下,通常两个名单相似的地方比不相似的地方更多。有人可能会想,只要简单地列出相似点和不同点,看哪个更多,这样就显示出原始形式是什么。但是,布莱恩表示,这种方法行不通,因为家谱的某些特征比其他特征更容易发生流动性。例如,一个人名的拼写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远比关于他的生命述评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大。因此,某些差异(例如名称的差异)在确定原始形式时的权重要比其它差异(例如描述的差异)的权重低。我们必须考虑每个相似点或差异的权重。[45]
根据这一原理,布莱恩发现创世记第4章和第5章的经文之间的两个主要相似之处:有相似的名字和相似的名字顺序,两者都极易变动,因此权重较少。他还发现了十个不同之处。其中五个因容易改变而权重小。这五个是:(1)在创世记第5章与洪水相关联,第4章中没有;(2)创世记第5章记录了十代,但创世记第4章只记录了七代,如果包括亚当,则记录了八代;(3)创世记第4章拉麦之后的节段看起来是那段经文的一部分,但创世记第5章挪亚之后的节段看起来则是被添加到那段经文之后的;(4)表达父子关系的格式不同;(5)功能不同,因为创世记第4章指向罪的蔓延和后果,而创世记第5章则指向蒙拣选的家庭的传承。
另五个不同之处倾向于抵抗流动性。[46] 一个是在创世记第4章中没有挪亚。布莱恩暗示即使功能或目的的改变也不会导致这一重要人物的遗漏。第二个是在创世记第4章中的拉麦之后,包括了三男一女的分段世代,这在创世记第5章中是完全不存在的。第三个抗流动性的差异是在创世记第4章中强调了某些文化方面的开端,这是创世记第5章所完全缺少的。第四个是贯穿创世记第5章的数值资料,在创世记第4章中找不到。布莱恩评论道:
“这很难用流动性来解释,因为即使在[苏美尔国王]名单中不同的七到十个国王都有[数字]。数字甚至出现在只有残片的文本中。”[47]
布莱恩列出的最后一个抗流动性差异是两个以诺和两个拉麦在生平信息上的差异。该隐的后裔以诺与城市建设有关,但塞特的后裔以诺与上帝同行。该隐的后裔拉麦杀了人还自吹自擂,但与他对应的人却生下义人挪亚而且说出关于他的预言。[48]
布莱恩的论点是,两个名单中的相似特征指向一个共同的原始名单,而相异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不容易受流动性影响的特征,则指向不同的原始名单。就创世记第4章和第5章而言,布莱恩仅发现两个相似的特征,却发现十个不同的特征,其中五个是抗流动性的,不容易随时间而变化。因此,布莱恩得出结论,这两个家谱并不是从一个原始家谱衍生出来的。
论证2: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对称的十代形式
那些否认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家谱因流动性而改变的神学家们,他们如何回答支持流动性的第二个主要论证呢? 该论证说,这些经文对称的十代形式和突出第七位的形式表明它们是按照标准的古代近东模式被格式化的结果。对这种论证的回应遵循以下几种思路。
乔丹简单地说:“没有理由认为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不能反映出真实的历史事态;实际上,将儿子出生时父亲的年龄包括在内是不容许任何空缺的……而是支持历史准确性。” [49] 不过,乔丹并没有忽视古代近东地区的十代文学传统。根据魏斯曼(P.J. Wiseman)的理论,创世记是围绕着多个“后代记”(Toledoth)文件编写而成的,这些“后代记”文件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记录下来的,然后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50] 乔丹提议创世记第5章所保留的记录比其它古代近东的名单更早,甚至可能是其它名单所依循的惯例的来源。[51]
|
亚当的“后代记”(创5:1-32) |
闪的“后代记”(创11:10-26) |
|
1. 亚当 |
1. 闪 |
|
2. 塞特 |
2. 亚法撒 |
|
3. 以挪士 |
3. 沙拉 |
|
4. 该南 |
4. 希伯 |
|
5. 玛勒列 |
5. 法勒 |
|
6. 雅列 |
6. 拉吴 |
|
7. 以诺 |
7. 西鹿 |
|
8. 玛土撒拉 |
8. 拿鹤 |
|
9. 拉麦 |
9. 他拉 (三子) |
|
10. 挪亚 (三子) |
|
理查德·尼森(Richard Niessen)分析说,仅仅因为某些十代名单是经过格式化的,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的名单都经过了格式化。在他看来,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分别记录了十代,因为洪水之前和从洪水到亚伯拉罕实际上有十代。他指出,文字本身没有表示有其它的意思,其中的数字也表示没有省略。尼森承认马太福音第1章中的家谱是被格式化的,但是由于马太福音列出了三组的14代,这肯定证明古代文士并没有被锁定在十代的形式上。尼森还指出,仅仅因为马太福音第1章被格式化就相信了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也被格式化了,这忽略了它们是不同类型的家谱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创世记的经文中有数字,但马太福音第1章则没有。因此,将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与马太福音第1章进行比较就像将苹果与橙子进行比较一样,这是一个基本的解经错误。[52]
库灵强调了一个大多数学者似乎都忽略了的重要观点。也就是说,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家谱并不是真正的对称。亚当的“来历”包含十个名字(亚当到挪亚),第十个有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闪的“来历”只记录了九个名字(从闪到他拉),第九个育有三个儿子(亚伯拉罕、拿鹤和哈兰)。把亚伯拉罕(亚伯兰)在创世记第11章中算作第十代,并不帮助形成对称,因为要前后一致就要在创世记第5章中算上闪(比较11:26与5:32)。所谓的对称性实际上并不存在。[53]
在这些论点之上,必须再加上几位著名且广受尊敬的学者的发现,他们不一定支持创世记5和11章无空缺的观点,但他们坚持认为这些圣经家谱与苏美尔国王名单无关,或者得出结论说,古代君王、圣人或部落祖先的名单中实际上不存在十代的模式。仅举几例就足够了。
格哈德·F·哈塞尔(Gerhard F. Hasel)在一篇经过精心推理、翔实记录的文章中分析了所有相关的古代文献,并得出结论说,创世记第5章与苏美尔国王名单(SKL)之间在事实上或形式上都不存在关联。[54] 他提出了十个理由 。
1. SKL里的名字在语言上不同于创世记。
2. 由于功能不同,SKL给出的是统治年限而非寿命。
3. SKL将国王与城市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将父与子联系在一起。
4. SKL使用的数字要大得多
5. SKL记录苏美尔和阿卡德在一位国王的统治下继续保持了政治统一,但创世记第5章与政治无关。
6. SKL列出的是国王,而不是祖先。
7. SKL与创世记第5章相比在地域上是局部的,而不是普遍的。
8. SKL以王权的开启开始而不是以第一个人开始。
9. SKL以一位名叫苏鲁巴克(Suruppak)的国王结束,而不是像挪亚这样的洪水英雄。
10. SKL并不总是一致地以十代形式存在。
关于最后一个原因,哈塞尔指出,近至1965年,一项重大研究得出结论,说希伯来人在创世记第5章里的十代模式是从SKL借来的。[55] 然而哈塞尔写道:
“苏美尔国王名单的主要修订版(WB 444)仅包含八位国王,而不是十位国王。有一个文本只包含七位国王(W),另一个(UCBC 9-1819)则是七位或八位国王,而亚述巴尼帕(Ashurbanipal)图书馆的双语片段只有九位国王。只有贝罗索(Berossos)和仅有的一个古老碑文(WB 62)这两个文本(其中只有一个是楔形文字)记载了十个洪水前的国王。根据楔形文字资料,我们不能再说苏美尔国王名单最初包含十个洪水前的国王,并在后来成了圣经家谱的原型。[56]
哈塞尔做出了另外两项令人震惊的观察。首先,他说:“创世记第5章中不间断的传承与苏美尔国王名单中同时或同代的王朝形成了鲜明对比。” [57] 然后,他提醒读者,SKL列出了39个洪水后的人物,大约是创世记第11章所列出的四倍。[58]
文翰曾两次提及各种美索不达米亚SKL版本中洪水前国王的数目不一致,显示出他对十代格式的怀疑。[59] 他确实看到,尤其是在雅各布森(T. Jacobsen)恢复的苏美尔版本中,[60] 苏美尔洪水故事与创世记第5-9、11章之间在事件顺序上的对应。在他看来,这并不表示彼此依赖,而是表示他们对世界、人类、文明的起源及大洪水等等,有共同的早期传承。他暗示,两个版本的家谱的差异与它们的目的有关。一名苏美尔故事作家可能出于政治动机而篡改了许多早期国王的名字,以证明他的城市拥有美索不达米亚的领导权。而其它城市也可能加入不同数目的不同名字的国王,以支持他们的领导权。同时代的希伯来人也是在相同的历史框架下,但并未加入一个国王名单,因为他们没有政治目的。他们乃是出于宗教或历史的原因,使用自己祖先的名字并一直追溯到第一个人。关键点是创世记第5章的希伯来人祖先名单看起来并不依赖于任何苏美尔国王名单的名字或十代形式。[61]
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R. Wilson)坚决主张,标准的古代近东十代家谱形式根本不存在,或者至少尚未得到证明。在认为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家谱有省略世代以符合标准的十代形式的学者中,亚伯拉罕·马拉玛特(Abraham Malamat)的著作颇具影响力。[62] 前面已经提到过,韦斯特曼把十代用法普遍存在于古代家谱中的证明归功于他。许多其他人在这方面也都依赖马拉玛特的研究。然而,在对马拉玛特的研究进行彻底分析后,威尔逊得出结论说,尽管马拉玛特对古代家谱的学术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关于十代模式的结论却是极不合理的。[63]
马拉玛特试图证明旧约家谱与古代近东家谱之间的相似之处。[64] 他有时用对现代部落家谱的研究来支持其标准格式的主张。他用以比较的基础是亚述国王名单(AKL)和汉穆拉比王朝家谱(GHD)。马拉玛特说,他发现这些古亚摩利人文献有四个部分,并且通常在圣经家谱中也可以找到相同的四部分。[65]
第一部分,他称之为“家谱库”,在对人名做了一些调整之后,他发现AKL和GHD分别包含12个和11个名字,由编造的人名(有时是部落名称)随意链接在一起而成。他还引用了9到11代的现代部落家谱,并得出结论说,这是创世记中使用的标准的10代形式的证据,因为所有这些名单都接近10代。[66]
第二部分是“决定性的一线”,被用来将家谱库与名单中余下的人联系起来。AKL中的决定性人名总共为五个,GHD中有两个。在圣经中,决定性一线起于亚伯拉罕,止于犹大,仅有四代。[67]
第三部分是“祖先表”,将决定性一线与最后一个部分联系起来。在AKL中,该部分有清楚的标题,即“十个做王的祖先”,记录着著名国王闪姆西-阿达德(Samsi-Adad)的家谱。在GHD中,该部分没有明确的标题,但马拉玛特认为它原本包含十个名字,但流动性已经使其不再清楚。他再次引用了长度在十代左右的一些现代部落家谱。路得记第四章中大卫的十个祖先提供了一个圣经的例子。他还提议圣经原本要保留十个扫罗的祖先,但他只能找到七个。[68]
最后一部分,即“历史的一线”,由国王或重要人物的直系祖先组成,因为执政者需要通过建立与其前任的血缘关系来确认其王权。在AKL和GHD中,这部分相当长。他没有在圣经中找到例子,但觉得曾经存在的可能性很大。[69]
马拉玛特根据这一分析得出结论说,在亚摩利人文化中,祖先表的理想形式是十代,就像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的一样。不久后,哈特曼(T. C. Hartman)撰文支持马拉玛特的结论。[70] 哈特曼认为斯派瑟将创世记第5章与SKL联系起来是错误的,因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基本差异。他还指责斯派瑟把10代形式的源头归于SKL也是错误的,因为大多数SKL版本的名字都少于10个。根据马拉玛特所做的工作,哈特曼得出结论说,创世记第5章的十代形式可能来自于亚摩利人对十代家谱的偏爱。
威尔逊发现马拉玛特和哈特曼的论证和结论都存在重大缺陷。首先,威尔逊指出,他们声称在AKL和GHD中发现的四部分家谱模式在旧约中根本不存在。例如,圣经中被马拉玛特归于第二部分的名字,即亚伯拉罕至犹大,从未在旧约的线性家谱中同时出现。此外,马拉玛特本人也无法从圣经中举出一个符合他的第四部分的例子。[71]
其次,威尔逊根据自己对现代阿拉伯和非洲部落社会使用的家谱的广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线性家谱的长度通常在5到19代之间变化。因此部落社会并不偏好某一特定的长度。他暗示马拉玛特只选择了那些支持他的十代理论的部落家谱作为例子,而忽略了许多不同长度的家谱。即使这样,他的示例还是从9代到11代不等,必须经过调整才完全符合十代形式。[72]
第三,威尔逊指出,马拉玛特所说组成AKL和GHD的八个部分(各有四个),在现存的版本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包含10个名称。AKL的四个部分分别包含12、5、10和77个名称。GHD的第一部分包含11个名称,第二部分包含两个名称,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没有明确的标记。马拉玛特靠着任意调整和划分,给人留下家谱有标准长度的大概印象,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标准长度,无论是10代或其它代数。[73] 威尔逊非常轻描淡写地总结说,“【马拉玛特】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支持他关于那些家谱具有刻板的十代长度或四部分结构的主张。”[74]
第四,威尔逊指出,AKL和GHD属于君王榜一类。它们都不强调亲属关系,并且列出的名字经常没有任何家族或生平信息。另一方面,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有明显的家族谱系特征。因此,威尔逊声称,将AKL和GHD与创世记的记录进行比较在方法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是不同类型的文献。[75]
威尔逊同意马拉玛特和哈特曼关于古代和现代家谱中相当普遍地存在流动性的观点。但他提醒读者,某些家谱发生了变动并不意味着所有家谱都存在流动性。每份家谱都有其不同的功能和背景,因此必须分别进行检查。“一概而论是不可能的。”[76]
布莱恩挑战了萨森等人提出的说法,即创世记早期家谱中对第七位的强调表明它们被格式化了。萨森自己也承认,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家谱和君王名单中并没有这种做法。[77] 他还承认,甚至在希伯来人中也没有一致地这样做。[78] 布莱恩除了指出萨森理论中的这些基本弱点之外,还指出了其方法论上的弱点,他写道:
“[萨森]的方法前后不一。当他说希伯排在以诺之后第七位时,他从以诺之后一代开始统计。然后,当他断言亚伯拉罕排在希伯之后第七位时,他却从希伯开始计数。如果他是前后一致的话,亚伯拉罕就会成为希伯之后的第六位。”[79]
布莱恩指出他认为的另一个方法错误。萨森假设该隐和塞特的家谱是从同一个原始家谱衍生而来的,原始家谱的第七位是拉麦。一旦采用这种假设就不可避免地得出以诺是后来被加入名单的结论。根据布莱恩的说法,这种推理等同于对流动性的循环论证,因为未经证实的假设是得出结论的主要根据。[80]
论证3: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众先祖的生活重叠
关于流动性存在的第三个主要论证是,无空缺解读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会使先祖们的生活重叠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例如,在洪水之前,亚当一直活到拉麦(挪亚的父亲)出生之后,从亚当到玛土撒拉的所有先祖在一段短时期内都活着。洪水过后,闪几乎活过了亚伯拉罕,而希伯活过了亚伯拉罕几年。年代家谱倡导者如何解释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呢?
乔丹的解释很典型。他声称没有客观理由否定这些先祖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重叠的说法。乔丹说,这样的说法对于现代学者来说似乎很奇怪,这只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地认为从亚当的时代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之间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前辈学者并不觉得先祖们的生命重叠不可思议。[81] 例如,马丁·路德写道:
“但是挪亚看到了他的后代直到第十代。他在亚伯拉罕大约58岁时去世。闪与以撒同活了约110年,与以扫和雅各同活约五十年。那一定是一个非常蒙福的教会,由这么多虔诚的先祖共同领导了这么长时间,并且一起生活了很多年。”[82]
乔丹承认圣经没有记载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的人们之间的接触。他针对这种信息的匮乏提供了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此类信息对于作者的目的而言是不必要的。其次,许多人似乎已经迁移到不同的地域,导致彼此接触困难而且罕见。[83]
根据乔丹的说法,大多数神学家认为从洪水到亚伯拉罕的被召之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几千年),人们已经失去了对上帝的认识,因此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恢复这一认识。针对这种说法,乔丹指出,麦基洗德和他的城市看起来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拥有对上帝的全面认识,约伯和他的文化也如此,尽管约伯的朋友们误用了他们的知识。[84] 亚伯拉罕之后,巴兰尽管显然没有与亚伯拉罕的后代接触,但是他知道耶和华的名并且以耶和华的名发预言。大概还有其他的先知也这样。对于乔丹而言,如此广泛的关于上帝的知识和洪水与亚伯拉罕之间过了很长时间的观念相冲突,反而支持先祖们的寿命有很大的重叠。[85]
论证4: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的固定重复模式
支持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家谱因流动性而导致空缺的第四个主要论证是,固定重复的模式“当X活了Y年时,他成为Z的父亲”,应解释为X活了Y年,生下一个儿子,而这一支后代最后传到了Z。这种解释为X和Z之间任何数目的世代都留下了空间。在支持流动性的所有论证中,否认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存在空缺的人对这一条的回应最激烈。他们似乎真地感到震惊,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违反基本的解经学原理且与经文直白的意思背道而驰的解释竟然得到了许多神学家的真诚拥护,包括一些保守的福音派主要人物。乔丹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年老地球预设,以及由此而来的想使经文包容他们的古老地球时间尺度的压力,知识渊博的神学家万不会想到这样的解释,更不用说提倡了。[86]
根据年代家谱的倡导者的推理,一条最为广泛接受的解经原则就是,作者的意图是经文的正确含义;尤其是那些采用语法历史解经法的人,更是认同这一点。[87] 人们怎么知道作者的意思呢?他的意思通常是他的陈述中最明显的意思,而这是由他的目标读者认定并在上下文中读出来的。[88] 在整个犹太史和教会史上,直到19世纪莱尔和达尔文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信徒,也就是目标读者,都将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理解为连续的家谱,记录了亚当到亚伯拉罕每一代人的名字以及每两代之间的年数。[89] 将模式的措词从“当X活了Y年时,他成为Z的父亲”改为“当X活了Y岁时,他生下一个最终传到Z的人”,这改变了作者的原意,严重违反了这条完善的解经学原理。[90]
原著的目标读者是否误解了作者的意图(达到数千年之大),忽略了X生Y可能意味着X是Y的祖先这一事实呢? 无空缺论的倡导者说,当然没有,因为“生”这个词的模糊性一直是众所周知的。对于创世记5章和11章来说,读者否定了这样的解释,因为作者费了很大力气在经文中列出了从每个人出生到其继承人出生之间的年数。如果作者的意图不是将这些名字联成一个连续的世代序列,这些数字就是多余的,而且完全没有意义。[91]
连续家谱的倡导者们认为,目标读者理解的正确性至少从四个方面得到了证实。首先,对于数字的存在从没有人提出过其他的合理解释。其次,古代文献中没有提供任何例子表示“ X活了Y年,生了Z”代表着X和Z之间还隔了几代。第三,创世记经文本身的细节表明:亚当和塞特(5:3)、塞特和以挪士(4:26)、拉麦和挪亚(5:28)、挪亚和闪(6:10,7:13,8:15,9:18,10:1,11:10)、希伯和法勒(10:25)、他拉和亚伯拉罕(11:27-32)之间都没有隔代,因此在其他人之间有隔代的可能性很小。第四,在新约圣经中,写犹大书的犹大显然是早期教会的领袖,也是耶稣的同母异父兄弟,他说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犹大书14),表明他相信从亚当到以诺没有空缺,甚至可能表示他相信亚当的家谱和闪的家谱都没有空缺。[92]
论证5:经外证据和人类的古久
关于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家谱中因流动性而导致空缺的第五个论证是,根据圣经以外的证据(例如科学证据),人类起源的时间比无空缺解读这两个家谱所得出的时间要早。人类进化的观念和定年法导致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人类之古久远远超过圣经的时间尺度,针对这一观念和方法的科学异议超出了本章和本书所讨论的范围。鼓励有兴趣的读者参考一下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杰出创造论学者马文·卢布瑙(Marvin Lubenow)的著作。[93] 关于放射测年法的不可靠性,有很多专门为非专业人士撰写的文章(附有充分的文献记录,以供专业人士参考)。[94]
年代家谱观总结
总而言之,持年代家谱观的人坚持认为,决定流动性问题的第一步是体裁的识别。不同形式的古代家谱发挥不同的作用。有些形式容许流动性,另一些则不容许。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记录了每个先祖在所提到的儿子出生时的年龄,这就是年代家谱的标记,这种体裁排除了导致世代空缺的流动性。
对于年代家谱的倡导者而言,决定流动性问题的第二步是揭露流动性论证的弱点。首先,他们指出,该隐和塞特家谱的相异之处比相似之处更多(并且更重要),表明它们很可能不是从被提议的同一个原始家谱演变而来的。相似性的最好解释是大家庭倾向于重复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名字。第二,他们坚持认为,古代家谱的标准十代形式根本不存在(尤其是威尔逊对马拉玛特的批评),强调第七位也不是标准的做法。第三,他们指出,虽然先祖们寿命的重叠在现代人看来似乎令人怀疑,但没有人说明为什么这些古人不能同时活着,而这是前辈的神学家们并不怀疑的。第四,年代家谱的倡导者们认为,将“ X活Y年生Z”解释为“ X活Y年后生子传到Z”的做法没有文献上的先例。他们进一步认为,后一种解释违反了基本的解经学原理,并使在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重复了18次的模式中给出的所有“ Y”数字变得毫无意义。
两种观点的评估
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家谱在传播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导致世代空缺的流动性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学术尝试是围绕着五个议题进行的。
第一个议题涉及在解经过程中体裁识别的重要性。前面的讨论揭示,空缺倡导者倾向于将所有家谱一视同仁。尽管他们经常谈论不同的家谱形式和功能,但在实践中,他们经常通过将一个家谱与另一个不同类型的家谱进行比较而得出结论。他们将马太福音第1章(没有提到年数)与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20代都含有数字)进行比较,并接着认定既然马太福音第1章有空缺,那么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也必定有空缺。这是他们完全无视家谱类型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解经学上是无法成立的。圣经和古代近东世界中存在的多种家谱形式,不仅应为学者提供关于不同功能的线索,而且还应提供不同的解释规则。由于无空缺倡导者强调要认真注意并严格遵守这些规则,他们在这方面的问题上就占据了制高点。
但是,仅仅要求识别体裁并遵守适当的解经规则并不能确保可以准确地识别出体裁。无空缺倡导者将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识别为年代家谱,主要是因为它们给出了每个先祖在“生”名单上下一个人时的年龄。这样的生育年龄真的为家谱标上了年代意义吗?无空缺的支持者只能举出几个家谱资料的例子,这些家谱资料用儿子出生时父亲的年龄来达到确定时间的目的。这些例子几乎完全来自创世记第12-50章的先祖时期。另一方面,支持空缺的人却提不出任何证据,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圣经里的还是经外的,显示儿子出生时“父亲”的年龄清楚地不是用来传达时间信息。因此,不存在以非时间表的方式理解生育年龄的先例。相比之下,把这些年龄理解为年代家谱的标志更合适。
为了确定流动性问题,学者们辩论的第二个议题涉及该隐家谱(创4)和塞特家谱(创5)的相似性。是否有一个原始名单通过流动性演变成两个相似的名单呢? 一些学者肯定这一说法,并认为名字的相似性只能这样解释。其他学者则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两个名单确实存在很大差异,并且任何相似之处都可能是由于大家庭偏好重复使用相同或相似名字所致。事实是,名字和相伴特征的相异性远比相似性多得多,其中有些通常不会出现在由同一原始名单演变出来的两个名单中,这表明该隐和塞特的家谱一直是分开的,并不是一个原始家谱演变成两个的结果。
关于流动性的学术辩论的第三个议题是关于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里的族谱可能的格式化,为符合标准的十代形式,并着重于第七个位置。马拉玛特在这个问题上的著作几乎使所有学者都相信这种形式在古代近东地区是标准的,并且创世记的作者从他的家谱来源中删除了名字以符合公认的模式。然而,威尔逊后来的工作指出了马拉玛特在方法和结论上的重大缺陷,并表明古代近东国王榜和现代部落谱系在世代数目上差异很大,而且事实上没有对任何特定家谱长度的明显偏好。哈塞尔已经证明,苏美尔国王名单SKL不能再用作标准10代形式的范例,因为几乎所有版本的SKL都在7到9代之间。因此,如果十代模式曾经存在,那就还没有得到证明。学者们不再具有假设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被格式化的事实基础。
关于流动性问题辩论的第四个议题涉及先祖们在世时间上的重叠。空缺倡导者们觉得重叠太大而难以置信,而无空缺倡导者们则看不到任何客观的理由去质疑。由于空缺倡导者没有给出其它理由,他们的怀疑似乎是因为他们已经笃信洪水发生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而且人类是在公元前10,000年之前被造的。因此,他们的论点不是建立在圣经的证据上,而是建立在关于人类年代的历史和科学的论据上,而这些论据近年来受到了强烈的挑战,因而在许多学者看来是错误的。就圣经文献而言,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的许多人同时活着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妨碍,正如路德和过去的其他杰出学者所信的。
在关于流动性问题的辩论中经常讨论的第五个议题关系到是否应将公式“ X生了Z”解释为X生了传到Z的血缘线。在这一问题上最有说明性的证据是,直到公元1800年之前,这种解释在犹太人或基督徒中几乎没人听说过。如果创世记的作者的意图是要让他的目标读者知道名单中省略了一些名字,那么他就彻底失败了。促成这种新解释的毫无疑问是19世纪初期和后期得到广泛接受的莱尔地质学和达尔文生物学,而不是健全的释经学原理。新解释的最具影响力的来源是格林(Green)和沃菲尔德(Warfield),他们承认其目的是为了在据说已经被证实了深时间的科学证据面前挽救旧约的信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忽视了两千多年的解经历史。其它的圣经证据也揭示了许多。如果父子之间有隔着几代的话,那么给出父亲生育儿子时的年龄显然是多余的,甚至会误导。我们绞尽脑汁也无法想象创世记的作者为什么会记下这些年龄,除非他的意图就是要将这些世代联成一个连续的序列。既然没人能在所有古代文献中指出一个例子,证明在Z出生时给出X年龄的家谱中存在空缺,那么以这种方式解释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依据是什么呢?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依据被提出来,更不用说被确立了。
结论
关于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家谱中存在因流动性而造成的空缺的主要论证都缺乏根据。尽管各方都承认某些古代家谱具有流动性,但尚无一方提出在塞特和闪的家谱中存在流动性的可靠证据。就圣经的证据而言,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的家谱没有经过省略或添加,里面没有空缺。这一结论对相信圣经的人有两个明显而重要的启示。首先,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提供的数字可以并且应该用于确定年代的目的。其次,人类只有大约6000年的历史。而且由于亚当和夏娃是在字面意义上的第六日里被创造出来的(如本书其它地方所证),整个宇宙也只有大约6000年的历史。
关于第二个该南的补录
与流动性问题相关的另一个议题也值得关注。路加福音第3章提到了两个名叫该南(Καίναν)的人,第一个是以挪士的儿子(参见创5),第二个是亚法撒的儿子(参见创11)。路加的第二个该南没有出现在创世记第11章的马索拉文本中,因此亚伯拉罕在创世记的马索拉文本中是亚当的第20代孙,而在路加福音中是第21代孙。因此,要么路加福音文本列出了一个不存在的人,要么创世记的马索拉文本忽略了一个确实存在的人。前一种选择令人怀疑路加的准确性,而后者则承认创世记第5章中有世代的空缺。
非年代家谱观
非年代家谱的倡导者觉得在路加的准确性和马索拉的遗漏之间不难选择。约翰·戴维斯下面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人:
“应该注意的是,现在的希伯来文创世记第11章中并没有列出洪水后所有的先祖。在路加福音的马利亚家谱中,该南这个名字出现在沙拉和亚法撒之间(3:36),这一遗漏使得我们无法确定大洪水的发生日期。……因此,创世记第11章必定有相当大的空缺,并且创世记第5章的家谱也很可能不是完整的。因此,不可能确定创世或洪水的确切日期。”[95]
蒙塔古·米尔斯(Montague S. Mills)指出,七十士译本在创世记第11章中包含了第二个该南,而且许多学者认为路加使用了七十士译本而不是希伯来文本作为他的家谱来源。然而,路加的信息来源对米尔斯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他对神默示的预设使他相信路加记载的准确性,无论其来源如何。在此基础上,米尔斯分析认为路加确认了七十士译本的准确性,并证明是马索拉文本省略了第二个该南。[96]
许多新约圣经文本评论家指出,第二个该南出现在路加福音的几个重要的早期大写字母手稿中,例如A、B、L、Δ、Λ、Π和א。这些手稿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有力地证明路加将该南列入了他的原始名单。这一证据使得许多福音派人士因为热心保护路加福音的准确性而坚持认为确实存在第二个该南,而马索拉文本却遗漏了他。
年代家谱的观点[97]
年代家谱支持者显然否定了说马索拉文本略去了名字的这个选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信路加使用了错误的信息来源(七十士译本),或者错误地列出了一个不存在的人。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方案,认为马索拉文本是正确的,第二个该南从来就不存在,并且与大写版本的证据相反,路加在原文中並沒有包括他。
理查德·尼森支持这种看法,他的两个主要论证可以总结如下:首先,七十士译本是对较早的希伯来语文本的不准确修订。[98] 在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其不准确之处尤为明显。涉及的不仅仅是添加一个名字,七十士译本中的每个名字都配有一组完全不同的数字,并且每个生育年龄都增加了50至150年。结果,七十士译本在创世和洪水之间增加了586年,在洪水和亚伯拉罕之间又增加了880年。这些数字膨胀的原因并不难发现。在亚历山大城负责七十士译本翻译项目的曼奈托(Manetho)刚刚在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非拉铁非”(Ptolemy II Philadelphus)的主持下,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埃及国王名单和年代。七十士译本的译者都是住在王宫里的犹太人,每天都要依靠他供应饮食。毫无疑问,他们有压力使圣经的年代与曼奈托夸大了的历史日期更加接近。有迹象提示,译者加入第二个该南作为“红色警示”,表示他们或多或少被迫增加了希伯来年代的时间。
“希伯来语中的‘该南’是‘该隐’这个名字的延伸。希伯来语中的‘该隐’含有‘获得’的意思,七十士译本的译者以此表示该特定名称在该特定位置是‘获得’的或多余的。这也是对希腊文词汇的巧妙的双关用法。七十士译本用的词是Καίναν,令人联想到καίνος,意思是‘未知,陌生,闻所未闻’,或κενος,意思是‘空’。”[99]
此外,七十士译本分配给第二个该南的三个数字与他的儿子沙拉的数字完全相同,真的这样碰巧的可能太小了,可能是为了表明他不是真实的。[100]
尼森的第二个主要论证是,尽管路加福音的许多大写版本包括第二个该南,但也有许多没有。例如,被认为是五、六个最重要的新约文本证据之一的贝扎古卷(Codex Beza)就没有。同样,许多早期教父在他们对路加福音的注释中都省略了该南。斐洛(Philo)、安提阿的约翰(John of Antioch)和尤西比乌(Eusebius)也省略了。俄利根(Origen)保留了它,但在他的一卷七十士译本中用方尖碑做了一个标记,这是他标记非权威读法的方式。因此,也许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路加在他的原文名单中并未包括第二个该南。[101]
尼森提出了一个建议,是关于第二个该南如何进到路加的某些早期抄本,后来成为其公认的文本的一部分的。
“路加福音的原文被誊抄了好几次,最终有人注意到路加福音3:36似乎‘缺了’一个名字。他参考了七十士译本,由于早期的基督徒只说希腊语而不说希伯来语,因此早期基督徒非常尊重七十士译本。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些抄写员不小心‘忽略’了这个名字,于是亲自对它进行了‘更正’。他的手稿一遍又一遍地被誊抄,含这个错误的更正的手稿也增多了。”[102]
撒母耳·库灵和尼森一样,认为第二个该南是被错误地加进七十士译本和路加福音的。除了尼森提出的原因之外,库灵还指出,第二个该南并未出现在马索拉文本中重复创世记第11章先祖名单的任何段落里。他既没有出现在七十士译本的历代志上1:18中,也没有出现在某些七十士译本抄本的历代志上1:24中,这表明七十士译本内在的不一致。第二个该南也没有列在约拿单的塔格姆译本(Targum of Johnathan)、昂科洛斯的塔格姆译本(Targum of Onkelos)、旧叙利亚文本、拉丁文译本以及所有其它包括撒玛利亚五经在内的古代版本中。库灵说,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七十士译本和路加福音的抄写者可能会添加一个名字,但是想不出一个原因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和其他早期作家会只省略一个名字而留下其余的名字。因此,第二个该南必定是错加的。[103]
罗伯特·菲特(C. Robert Fetter)也得出结论,说该南根本就不存在、路加的原文中也没有他。[104] 在对所有涉及第二个该南问题的古本、手稿、历史、年代学和经文注释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并且考虑了许多神学家对此问题的看法之后,菲特总结了存在第二个该南的证据如下:
1. 在路加福音的大部分最佳手稿中都可以找到他。
2. 在七十士译本的大多数记载中都可以找到他。
3. 他在禧年书中被列出。
4. 他可能被列入异教作家德米特里(Demetrius)的年代表中。[105]
菲特总结了反对第二个该南存在的证据如下:
1. 路加福音的某些手稿省略了该名字,包括最古老的手稿之一。
2. 七十士译本内部在这一点上不一致。
3. 禧年书的性质和年代都不能使人信服它在这一点上的权威。
4. 除了七十士译本之外,没有任何古老版本包含该名字。
5. 除了德米特里之外,没有古代历史学家认可该南。
6. 希伯来圣经中没有任何其它地方提到他。
7. 早期教父所拒绝接受他的名字。
8. 有理由相信,较短的希伯来文年代要优于七十士译本的年代。
9. 撒玛利亚五经和约瑟夫的年代都忽略了他的名字。
10. 可以找出两个可信的将他加入名单的动机,即千禧年构想和传奇理论,都是基于历史事实(见下一段)。
11. 他的名字和年龄可能都是基于家谱中其他成员,而不是事实。[106]
根据这些证据,菲特得出的结论是,该南几乎可以肯定从来不曾存在过。
为什么七十士译本将第二个该南加入呢?菲特提供了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基于基督教的编年史家提阿非罗(Theophilus)的著作,他是公元176–186年间安提阿的主教,并且涉及一个千禧年构想。那时许多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包括提阿非罗在内,都是千禧年论者,他们相信历史只会有六千年的历史,每千年的终结都有一些标志性的重大事件。由于法勒的名字(创世记10:25; 11:18)表示“分裂”,因此他们认为历史会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即法勒(Peleg)的儿子拉吴(Reu)出生之前和之后的三千年。不幸的是,从他们的理论来看,七十士译本从亚当的受造到拉吴出生仅记录了2,791年。他们毫不气馁,将209年的差异归咎于抄写的错误,并着手予以纠正。他们开始时将塞特出生时亚当的年龄增加了一百岁,但他们注意到玛土撒拉的生育年龄与洪水前其他先祖的生育年龄相冲突,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减去20岁来缓解这种矛盾。这些修正将亚当和拉吴的出生之间的时间变成了2871年。他们仍然需要129年才能达到所需的三千年,因此他们在亚法撒和沙拉之间插入了新的该南,这个名字是从创世记第5章中类似的位置借来的,并说沙拉出生时该南的年龄是130岁。通过将法勒生拉吴的年份分配到历史的第二个大纪元,他们就得到第一个纪元正好是三千年。[107]
年代学家马丁·安思泰(Martin Anstey)指出,在七十士译本的某些抄本中拉麦出生时玛土撒拉的年龄是187岁,而其他抄本中则是167岁。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菲特的千禧年构想解释。[108]
菲特写道,将该南加入七十士译本的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这样的:
“……因为禧年书里有他(毫无疑问在当时的其它文献中也有他),所以尽管希伯来文记载中没有,他还是被认为是亚法撒之子和沙拉之父,因此只要有机会就把他包括在家谱里面。”[109]
然后他补充说:“可能是由于这两个原因,为了符合传统,他的名字先被加进去,然后根据千禧年构想的需要,将他的年龄做了调整。”[110]
为什么第二个该南被加入路加福音中呢?菲特指出,在许多早期基督教作家所使用的七十士译本中没有第二个该南,因此他否定了路加简单地无分辨地从希腊文创世记第11章中复制了家谱的想法。不过费特认为,一旦第二个该南进入七十士译本并成为其公认的一部分后,抄写经文的人就承受着将他也纳入路加福音抄本的压力,并且最终他们在这种压力下屈服了。[111]
评估
在大部分重要的大写手稿中,路加的基督家谱都有第二个该南,但这些手稿的历史只能追溯到公元四世纪之后。公元四世纪之前,几乎所有的文献都没有他,包括世俗历史学家约瑟夫、基督教神学家、除了七十士译本以外的古代版本、以及相当重要的撒玛利亚五经。甚至一些七十士译本的抄本在创世记第11章中也没有列出他,而且七十士译本的所有抄本都未能在旧约重复出现闪的家谱时一致地列出他。所以,几乎可以肯定第二个该南根本就不存在。他的名字可能是刚好在公元四世纪之前添加到路加的记载中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确定添加的原因,但是尼森和菲特提供的场景似乎是合理的。总之,路加福音里的第二个该南不应该被视为马索拉文本的创世记第11章有遗漏的可靠证据。
[1] 本章包括了我的论文 的一大部分,“A New Look at the Genesis 5 and 11 Fluidity Problem,” Andrews University Seminary Studies 42 (2004): p. 259–286; 和 “The Genesis 5 and 11 Fluidity Question,” TJ 19(2) [2004]: p. 83–90. 这里的使用得到了出版者的和善的许可。
[2] Claus Westermann, Genesis 1–15: A Commentary, trans. John J. Scullion (Minneapo- lis, MN: Augsburg, 1984), p. 348-354. 韦斯特曼认为创世记第5章的先祖名单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没有任何联系。
[3] 同上,第352页。为证明古代家谱中经常使用十代模式,韦斯特曼援引以下文献:Abraham Malamat, “King Lists of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 and Biblical Genealog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8 (1968): p. 163–173.
[4] Nahum M. Sarna, Genesis, JPS Torah Commentary (New York: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89), p. 40–41.
[5] 同上,第40页。
[6]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A Commentary, trans. John H. Marks, Old Testament Library (Philadelphia, PA: Westminster, 1961), p. 69.
[7] 同上,第66页。
[8] 同上,第66-69页。
[9] E.A. Speiser, Genesis, AB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4), p. 41–42.
[10] John C. Gibson, Genesis, Daily Study Bible (Philadelphia, PA: Westminster, 1981), 1:155–156.
[11] 同上,第156页。
[12] Jack Sasson, “A Genealogical Convention in Biblical Chronography?” Zeitschrift fu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90 (1978): p. 171–177.
[13] Robert Davidson, Genesis 1–11, The Cambridge Bible Commenta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61.
[14] 同上,第61-62页。
[15] William H. Green, “Primeval Chronology,” Bibliotheca Sacra 47 (1890): p. 285– 303.
[16] Gleason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Chicago, IL: Moody, 1994, revised ed.), p. 209–212.
[17] K.A. Kitchen, Ancient Orient and Old Testament (Chicago, IL: InterVarsity, 1966), p. 35–39.
[18] 同上,第37页。基勤承认考古学家们非常依赖碳14定年法来确定这些日期。放射性定年法最近受到很多科学研究的强烈挑战。参下面网页的许多文章:www. answersingenesis.org/home/area/faq/dating.asp.
[19]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1–15, WBC (Waco, TX: Word, 1987), p. 123–134.
[20] 同上,第133-134页。
[21] John J. Davis, Paradise to Prison: Studies in Genesis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75), p. 102,151.
[22] 同上,第 28-32、104、151页。在第30页上,戴维斯承认他对格林的依赖。
[23] Victor P. 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 1–17, NICO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0), p. 249–254.
[24] 同上,第254页。哈密尔顿引用的重要研究 Abraham Malamat, “Tribal Societies: Biblical Genealogies and African Lineage Systems,” Archives europeenes de sociolgie 14 (1973): p. 126–136.
[25] Kenneth A. Mathews, Genesis 1–11:26, NAC (Nashville, TN: Broadman & Holman, 1996), p. 295–305. 在第302页,马修斯承认他的观点的经典陈述可以在格林著作的285-303页找到。在第305页,他也指出他依赖于Benjamin B. Warfield, “On the Antiquity and the Unity of the Human Race,” Princeton Theology Review 9 (1911): p. 1–25.
[26] 同上,第302页。
[27] 同上。
[28] Ronald F. Youngblood, The Book of Genesis: An Introductory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1), p. 75.
[29] Samuel R. Kulling, Are the Genealogies in Genesis 5 and 11 Historical and Complete: That Is, Without Gaps? (Reihen, Switzerland: Immanuel-Verlag, 1996), p. 30–31. 关于以色列王,实际上有四个或更多的家谱,因为至少有四个朝代。无论如何,它们的年代学数值是明显的。
[30] 同上。
[31] Brevard S. Childs,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Philadelphia, PA: Fortress, 1979), p. 145–146.
[32] 同上,第146页。
[33] David T. Rosevear, “The Genealogies of Genesis,” in Concepts in Creationism, ed. E.H. Andrews, Werner Gitt, and W.J. Ouweneel (Welwyn, England: Evangelical Press, 1986), p. 68–77.
[34] James B. Jordan, “The Biblical Chronology Question,” Creation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Quarterly 2 (1979): p. 1–6.
[35] 同上,第6页。
[36] Wenham, Genesis 1–15, p. 123–124.
[37] Mathews, Genesis 1–11:26, p. 281–282.
[38] 马修斯既没有解释,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些差异不能归因于功能带来的流动性。
[39] 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 1–17, p. 250–251.
[40] 同上,第250页。本文后面对罗伯特·威尔逊的工作有更全面的论述( “The Old Testament Genealogies in Recent Research,” JBL 94 [1975]: p. 169–189);威尔逊也对古代和现代家谱的形式和功能做出了深入分析 (Genealogy and History in the Biblical Worl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1–205)。
[41] David T. Bryan, “A Reevaluation of Genesis 4 and 5 in Light of Recent Studies in Genealogical Fluidity,” Zeitschrift f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99 (1987): p. 180–188.
[42] William H. Green, The Unity of the Book of Genesis (1895), p. 46–47. 显然格林并不认为名字的混淆是与圣经的无误性冲突的,因为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会有在字母和拼写上的改变。
[43] J.J. Finkelstein, “The Antediluvian Kings: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ablet,”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17 (1963): p. 50.
[44] William W. Hallo, “Antediluvian Cities,”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23 (1970): p. 63–64.
[45] Bryan, “A Reevaluation of Genesis 4 and 5 in Light of Recent Studies in Genealogical Fluidity,” p. 180–182.
[46] 同上,第183-187页。
[47] 同上,第187页。
[48] 同上,第187-188页。
[49] Jordan, “The Biblical Chronology Question,” p. 9.
[50] P.J. Wiseman, New Discoveries in Babylonia about Genesis (London: Marshall, Morgan and Scott, 1958), p. 45–89. 也参见Duane Garrett, Rethinking Genesis: The Sources and Authorship of the First Book of the Pentateuch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1), p. 91–125;和R.K. 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69), p. 63–64, 542–553. 在552页,Harrison断言,“创世记中看到的原始资料毫无疑问是非常古老的。”
[51] Jordan, “The Biblical Chronology Question,” p. 9.
[52] Richard Niessen, “A Biblical Approach to Dating the Earth: A Case for the Use of Genesis 5 and 11 as an Exact Chronology,”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Quarterly 19 (June 1982): p. 63.
[53] Kulling, Are the Genealogies in Genesis 5 and 11 Historical and Complete, p. 33–34. W.H. Gispen, Genesis, vol. 1, Commentaar op het Oude Testament (Kampen, The Netherlands: Kok, 1974), 第385–386页也承认对称性不存在。七十士译本在创世记第11章多列了一位先祖(称为第二个该南),但有很强的证据显示这是抄写错误。这个问题在本章后面有更细节的阐述(参标题为“关于第二个该南的附录”一节)。
[54] Gerhard F. Hasel, “The Genealogies of Genesis 5 and 11 and Their Alleged Babylonian Background,” Andrews University Seminary Studies 16 (1978): p. 361–374. 也参见K. Luke, “The Genealogies in Genesis 5,” Indian Theological Studies 18 (September 1981): p. 223–244.
[55] 参见W.G. Lambert, “A New Look at the Babylonian Background of Genesis,”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16 (1965): p. 287–300, 尤其 292–293页。
[56] Hasel, “The Genealogies of Genesis 5 and 11 and Their Alleged Babylonian Back- ground,” p. 367.
[57] 同上。
[58] 同上。
[59] Wenham, Genesis 1–15, p. 124.
[60] T. Jacobsen, “The Eridu Genesis,”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00 (1981): p. 513– 529.
[61] Wenham, Genesis 1–15, p. xxxix–xli, p. 123–125. M.B. Rowton, “The Date of the Sumerian King List,”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19 (1960): p. 156–162, 也提出SKL背后的政治动机。
[62] Abraham Malamat, “Kings Lists of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 and Biblical Genealogies,” in Essays in Memory of E.A. Speiser, ed. William W. Hallo, 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53 (New Haven, CT: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68), p. 163–173;作者同前, Mari and the Bible: Some Patterns of Tribal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s,” JAOS 82 (1962): p. 143–150; idem, “Tribal Societies,” p. 126–136.
[63] Robert R. Wilson, “The Old Testament Genealogies in Recent Research,” JBL 94 (1975): p. 169–189;威尔逊对古代和现代家谱的形式和功能也有深入分析,见Genealogy and History in the Biblical Worl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1–205.
[64] Malamat, “King Lists,” p. 163–173.
[65] 同上,第164页。
[66] 同上,第165-168页。
[67] 同上,第168-169页。
[68] 同上,第169-171页。
[69] 同上,第164页。
[70] T.C. Hartman, “Some Thoughts on the Sumerian King List and Genesis 5 and 11B,”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91 (1972): p. 25–32.
[71] Wilson, “Old Testament Genealogies,” p. 178.
[72] 同上,第 175-179页。关于现代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家谱的透彻讨论请参Wilson, Genealogy, p. 18–55.
[73] Wilson, “Old Testament Genealogies,” p. 182–88.
[74] 同上,第188页。马拉玛特自己在语言上的模棱两可支持威尔逊的结论,就是马拉玛特没有证明其观点的结论。例如,在他讨论古代家谱所谓的十代形式时,马拉玛特(“国王名单”,165–166页)在8个句子的段落里就用了八个不肯定的词或短语——(1)可能,(2)可能地,(3)可能曾是,(4)我们也可以假定,(5)费解的,(6)我们大概可以,(7)如果我们假定,(8)倾向。这样的语言弱化了他听起来很有信心的结论,“洪水前和洪水后【亚当和闪】的家谱,对称地编排成10代的长度,毫无疑问是刻意调和并效仿这个具体的家谱模型的结果。”
[75] Wilson, “Old Testament Genealogies,” p. 187.
[76] 同上,第189页。
[77] Sasson, “A Genealogical Convention in Biblical Chronography?” p. 172.
[78] 同上。
[79] Bryan, “A Reevaluation of Genesis 4 and 5 in Light of Recent Studies in Genealogical Fluidity,” p. 181.
[80] 同上,第182页。
[81] Jordan, “The Biblical Chronology Question,” p. 4.
[82] Martin Luther, Commentary on Genesis, trans. J. Theodore Mueller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58), p. 199;被引用于Jordan, “The Biblical Chronology Question,” p. 1–2.
[83] Jordan, “The Biblical Chronology Question,” p. 4. 乔丹提议吉尔伽美什史诗有历史的依据,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先祖访问另一个先祖的例子。在这个史诗中,吉尔伽美什长途跋涉去寻找经过洪水的老人,乌他那普汀,而他立刻就告诉他有关洪水的事情。
[84] 乔丹假定约伯的时间比亚伯拉罕早,至少就约伯故事的中心而言。
[85] Jordan, “The Biblical Chronology Question,” p. 4–5. 在这个观点中,约书亚指控亚伯拉罕的先祖拜外邦的神(书24:2)应该理解为泛指,就像后来像耶利米这样的先知们指控全以色列拜偶像一样,甚至大家都理解耶稣也允许例外。
[86] 同上,第6页。
[87] E.D. Hirsch Jr.,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23, 深入地分析了这一原则,并得出结论说,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因为语言符号并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
[88] 在圣经中可以找到这个规律的明显例外。例如,耶稣有时用隐晦的语言说话,而当时不悔改的人会误解他。不过,耶稣自己也承认他故意不用直白的语言来呈现他的信息。绝大多数的时候,圣经作者们大概都是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清楚地传递他们的信息。如此,这个规律还是成立的。
[89] 参Davis A. Young, The Biblical Flood: A Case Study of the Church’s Response to Extra- biblical Evidence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5), p. 1–79.
[90] Kulling, Are the Genealogies in Genesis 5 and 11 Historical and Complete, p. 25–36; Niessen, “A Biblical Approach to Dating the Earth, p. 61–65; Rosevear, “The Gene- alogies of Genesis,” p. 73; Bert Thompson, Creation Compromises (Montgomery, AL: Apologetics Press, 1995), p. 175; 和 Jordan, “The Biblical Chronology Question,” p. 5–6.
[91] Rosevear, “The Genealogies of Genesis,” p. 72–73; Niessen, “A Biblical Approach to Dating the Earth, p. 62-63.
[92] Kulling, Are the Genealogies in Genesis 5 and 11 Historical and Complete, p. 25–36; Niessen, “A Biblical Approach to Dating the Earth, p. 61–65; Rosevear, “The Genealogies of Genesis,” p. 73; Jordan, “The Biblical Chronology Question,” p. 5–6.
[93] 参Marvin Lubenow, Bones of Contention: A Creationist Assessment of Human Fossils (Grand Rapids, MI: Baker, 2004, 2nd rev. ed. 和该书第一版中的附录(关于化石年代鉴定)。
[94] 参Donald DeYoung, Thousands, not Billions: Challenging an Icon of Evolution, Questioning the Age of the Earth (Green Forest, AR: Master Books, 2005). 这是一个国际创造科学家博士团队对放射性定年法经过八年研究所发表的结果的总结,面向非专业人士。也请考虑网站www.answersingenesis.org/home/area/faq/dating.asp里的许多文章。
[95] John J. Davis, Paradise to Prison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75), p. 30.
[96] Montague S. Mills, “A Comparison of the Genesis and Lukan Genealogies: The Case for Cainan” (Master of Theology Thesis,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1978), p. 9–11.
[97] 反对存在第二个该南的另一个论证,请参Jonathan Sarfati, Refuting Compromise (Green Forest, AR: Master Books, 2004), p. 295–297.
[98] 鉴于已有的许多研究,本研究预设马索拉文本的优先性和准确性。七十士译本在创世记第5章和第11章中的数字显然是不准确的。例如,它们使玛土撒拉活到洪水之后17年。这里的讨论不是来论证这个议题,而仅仅是给出尼森反对第二个该南的大致意思。
[99] Richard Niessen, “A Biblical Approach to Dating the Earth: A Case for the Use of Genesis 5 and 11 as an Exact Chronology”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Quarterly 19 (June 1982), p. 64.
[100] 同上。
[101] 同上。
[102] 同上,第 64-65页。
[103] Kulling, Are the Genealogies in Genesis 5 and 11 Historical and Complete, p. 33. 库灵否认一个名字被省略了好让创世记第11章与创世记第5章对称的观念,因为它们并不对称。
[104] C. Robert Fetter, “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Second Cainan’ in Luke 3:36” (Master of Divinity thesis, Grace Theological Seminary, 1956), p. 1–87. 虽然费特的深入研究已经过了40年了,但是围绕第二个该南问题的证据主要是与古代文献相关,而费特已经深入地处理了这些文献。所以,他的研究和结论还是值得考虑的。
[105] 同上,第74页。
[106] 同上。
[107] 同上,第70-72页。
[108] Martin Anstey, Chron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Kregel, 1973), p. 44.
[109] Fetter, “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Second Cainan’ in Luke 3:36,” p. 73.
[110]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