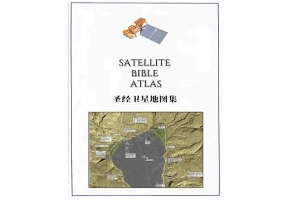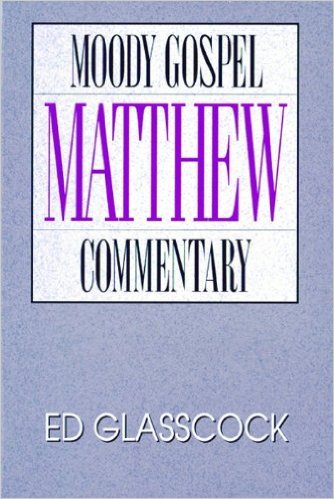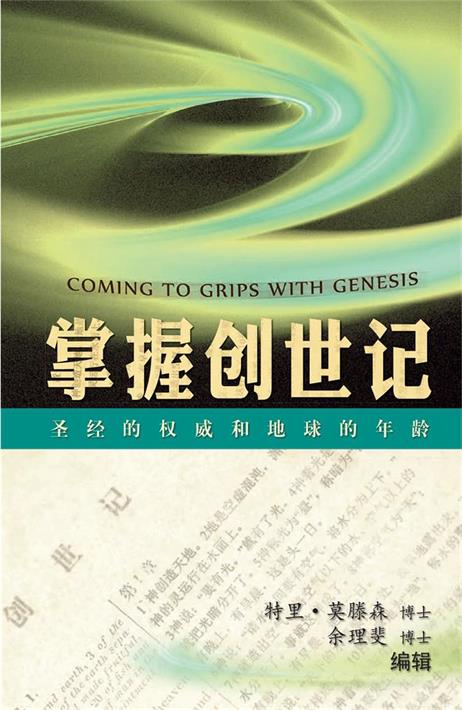
后记
编者
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和科学逐渐取代了神学和启示,成为真理和知识的仲裁者。通过科学的强大文化影响力,全世界都被告知进化和亿万年历史是可以证明的、毋庸置疑的科学事实。认可的压力很大,而那些没有认可的人则被嘲笑为愚昧无知的地平说原教旨主义者。达尔文主义和“深度时间”影响了几乎所有主要学科,并因此逐渐塑造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大多数基督徒不接受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即所有动植物都是共同祖先的后裔),首先是因为它明显地与创世记相抵触,但也可能是因为其科学证据经不起权衡,说服力不足。但是,基督教学术界的大多数人以及许多牧师和非专业人士似乎已经拥抱了亿万年的历史观。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经常公开地)信心满满地认定所有相关证据无可争议地指向一个古老的地球和更古老的宇宙。他们同样认定深度时间与圣经之间没有矛盾。但是,无论持这些观点的教师们是多么地真诚,他们都为自己的学生们打开了接受进化论的大门,其社会后果和属灵损害是严重的。
危险的想法总是带来负面的影响,就像我们在20世纪所看到的悲剧,实施达尔文思想的哲学以后收获了诸多苦果。令人不寒而栗的达尔文主义恶果莫过于纳粹主义,它有意识地采用了达尔文原则,终致亿万生灵惨遭涂炭。我们西方世界一度牢固地立足于犹太-基督教的原则,但现在已深入后基督教时代,其后果是“半分娩流产”、彻底重新定义婚姻、安乐死等。道德的衰落至今没有减缓的迹象。
微生物学家迈克尔·丹顿(Michael Denton)并不是基督徒,但他于1985年在他的影响深远的针对进化论的科学评论中指出:“今天,在二十世纪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形成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达尔文主义的自然观。”[1] 当时丹顿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精明的见识。但其实怀疑论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福音和基督教道德的普遍抗拒并不是从达尔文开始的:它早已“弥漫空中”。[2]
哈佛大学已故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是一位著名的无神进化论者,他提出了基督徒经常忽略的联系:“当人们认为地球显然很古老而不是6000年前才被创造出来的时候,[达尔文主义]革命开始了。达尔文的发现是导致了整个雪崩的那个雪球。”[3] 亿万年的观点不是科学的“发现”,而是一项植根于反圣经的历史假设的发明,我们同意,对圣经年代表的拒绝触发了整个链式反应。
上面的说法很讽刺,因为它是由哈佛学者做出的,而这所学校的早期座右铭是“ Veritas pro Christo et Ecclesia”(真理为基督及其教会)。哈佛大学是美国第一所大学,成立于1636年,在那时,所有申请者都必须具备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圣经。在它的前一百年,其一半以上的毕业生成为牧师。在西方,最可悲和得到最充分证明的事实之一是:像哈佛大学这样本来以基督为中心的机构,正在慢慢地吸收现代性的时代精神,一种反超自然的、深度时间、进化论教条感染了他们的课程并最终杀死了他们对圣经的观点和信仰声明。简短地翻阅一下我们国家最古老、最负盛名的学术机构的原始典章,就可以发现它们曾经具有坚定的基督教特色。在美国最早的108所大学中,除了两所以外,其余的都曾经是坚强的基督教大学,它们通常具有共同的目标,即以上帝的话语训练学生,以达到为基督赢得世界的明确目的。如今,他们是其创始人几乎不认识的反基督教信仰的堡垒。[4]
考虑到漫长而曲折的妥协轨迹,我们让读者来思考一下:当学校雇用支持进化和深度时间观点的教授并将这种哲学种子播种到整个课程时,它的风险是什么?您知道有几所机构漂向正道? 随着学院的偏离,各教派最终也都偏离了。今天的自由派曾经是正统派,他们曾经相信圣经的启示性和无误性,相信圣经中的奇迹、耶稣的代死和赎罪以及他的身体复活。但是历史表明,在高等批判和古老地球地质学的双拳夹击下,高等院校开始吸收反圣经的自然主义(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的哲学假设,并从此一路下滑。
本书的作者们坚信,没有任何正确解释的科学事实最终将与直接解读的创世记相矛盾。我们已经表明:圣经(上帝的“特殊启示”)教导,受造物向我们揭示了上帝的存在以及至少他的某些属性。这种“普遍启示”是关于上帝的。并非所有科学家“发现”的有关上帝之创造的一切理论都是普遍启示。同样并不是大多数科学家所相信的一切都符合“普遍启示”这个标签。圣经没有教导说,仅通过研究普遍启示,而无需参考特殊启示,我们就可以敲定创造的时间框架或上帝创造的方式。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教义为解释对受造界的观察提供了保护性参数,而不是相反。
我们强烈赞成巴刻(J. I. Packer)的主张:无误论者必须“首先承诺,对于我们查阅圣经时实际发现的所有教导,都当作从神而来的真理接受。”[5] 我们必须将经文与经文进行对比,根据上下文仔细地解经,寻求作者的意图,并事先承诺顺从其教义。只要对文本进行正确的解释,其结果就可以作为判断其他一切事物的依据,包括我们自己的神学浅见。否则我们怎能确定时空中发生了任何奇迹?同样的,创世记是一副眼镜,它可以正确观测、过滤和解释上帝的创造。
任何对宇宙历史的重建,如果与圣经真理相悖,都必须被认为是错误的。但当我们在圣经的框架内研究受造界的生物、岩石和恒星时,我们所看到的就合乎情理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生物学中观察到,上帝确实创造了动植物,它们各从其类地繁殖,而不是变成不同的类。我们的思想会认识到科学证据与全球性的大洪水相吻合。使用从圣经得出的假设,我们还可检测到设计的标记,而且实际证据指向近期的创造。通过坚持一致的圣经预设,我们发现上帝的诅咒在整个受造界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当年宗教改革的先驱们所言,世界原非今天的样子。
我们已经证明,教会的历史性正统教义是年轻地球创造论。在1800年间,基督徒几乎普遍的信念是,上帝在大约6000年前的六日内创造了世界,并且在挪亚时代,他用全球性的洪水摧毁了世界。但是在19世纪早期,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的地质学家们和天文学家们,应用反圣经的假设,开始推行其古老地球和古老宇宙的理论。当然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当潘多拉魔盒在教会中打开时,信徒们开始拥抱间隔论、长日论、局部洪水论、框架假说、以及其他一些在自然地阅读创世记第1-11章时不能立即看出的教义。谁能计算这些理论对基督教世界造成的损害?
在圣经中插入亿万年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首先,我们被要求忽略创世记和圣经其他地方的经文中的许多细节,正如本书所讨论的。第二,我们还必须拒绝、无视或以其他方式压制耶稣和使徒的明白教导。第三,通过将“深度时间”纳入我们的思维,我们削弱了圣经关于死亡起源的教导。第四,我们玷污了上帝的品质。采纳了漫长时间的观点,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目前观察到的自然恶是由造物主设计的,而且他认为这样的世界“甚好”。第五,我们还有许多其他棘手的难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全能的创造者完成的工作不是没有死亡的(甚至视死亡为“好”),那么我们凭什么保证在新天新地里没有死亡?为什么要相信圣经关于世界末日的教导,而不信其关于世界开端的记载?无论这些人的动机是真诚还是无意,将深度时间束缚于圣经,最终都会破坏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这福音是根植于创世记字面上的历史的,并破坏对永恒状态的盼望,因为在永恒里不应有自然恶或道德恶。
我们认为,本书中的论证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圣经依据,让我们相信教会在其最初的18个世纪里是正确的。附录中的资源也为此提供了一些科学证据。我们敦促读者熟悉这些材料。
1990年,在惠顿学院关于基督教与科学的座谈会上,戴维斯·杨(Davis Young)的坦白令人瞠目。作为前长日论的拥护者(但仍然是古老地球论者),他感叹道:“长日论者发展出令人惊奇的灵活性来克服一些文字障碍。”他坦承自己为“几年前肢解圣经本文而公开忏悔”,并决定改正,以“不让自己更尴尬”。他生动地描绘了那些在圣经和古老地球进化论之间强求和谐的人,说他们 “惯用遁词”,善于“解经学艺术体操”,因而造成了“神学肌肉损伤”。他说,他并不特别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些“妥协的做法总体上是失败的”,而且“尽管这些做法都精巧,但都勉强得令人瞠目。”因为杨氏坦承对上帝话语的错误处理,人们可能会认为他现在是一位年轻地球创造论者。但遗憾的是,他离圣经更远了。他在惠顿演讲中(显然今天仍然是)得出的结论是,创世记第1-11章“可能是用非事实的方式表述了历史。”[6]
这种不合逻辑的 “非事实历史”的思想,其实是杨氏对地质“事实”接受的结果,而地质“事实”实际上是基于反圣经的、自然主义的、均变论哲学假设的解释。他在跟随世俗的进化论地质学家的学术训练中吸收了这些“事实”(或曰“ 洗脑”,如德里克·阿格(Derek Ager) 所言[7])。不幸的是,对教会而言,许多圣经学者都信任杨氏的著作,因为他有地质学资历,也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E. J.杨是受人尊敬的旧约学者。因为戴维斯·杨的著作,那些神学家们不相信神关于地球年龄的话语。我们只能希望这些学者愿意仔细考虑那些资历相当的年轻地球地质学博士的观点,他们的著作和DVD列于附录中。
近年来,智能设计运动(IDM)在教会中变得很流行。这一运动的领袖们所写的大部分书籍都是由福音派出版社发行的,并在教会中赢得了大量读者。我们非常重视IDM的论点,这些论点揭示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缺陷,其精密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自然界里的设计(与时间、机遇和自然规律所产生的截然相反)。这些论点极大地扩充了IDM兴起前后数十年来年轻地球创造论者所使用的设计论证。
我们也感激IDM对达尔文主义科学中的自然主义影响的关注。本·斯坦因(Ben Stein)于2008年拍摄的具有挑战性的电影《驱逐》(Expelled)适时曝光了学界的问题,表明“进化与创造/设计”之争实际上是世界观的冲突,而不是“科学与宗教”之争。我们认为,《驱逐》一片非常有帮助,它将使很多人重新思考这场战役的性质。因此,我们将继续热烈感谢IDM,极力使用其研究成果,并鼓励他们继续战斗。
话虽如此,我们还必须扼要地表明关于IDM对教会影响的担忧。首先,根据我们所读到的和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IDM让基督徒忽视神的话语在地球年龄问题上的教导,使他们认为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不如科学理论清晰。IDM学者的书籍可能笼统地提到圣经,但这通常看起来像是事后诸葛或断章取义,而不是认真地在地球年龄的问题上对圣经作出最佳的解释,特别是关于创世记。同样,许多IDM领袖在基督教场所演讲(教堂、基督教大学、神学院、基督教广播和电视等)也是这样。在这些场合中,他们通常会忽略创世记(甚至没有自然而然地读一遍),因为他们支持古老地球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一运动中的许多人不是福音派人士,甚至不一定是基督徒。IDM的主要智囊团“发现研究院”的领导人坦言此运动没有宗教界限。[8] 如果圣经丝毫没有触及地质学、宇宙学和受造界的年龄,那么忽略圣经文本还不是问题。但是圣经有教导。没有任何一个认真的基督信徒可以合理地无视神的话语,或者对相关主题的经文浅尝辄止。
其次,尽管IDM领导人擅长展示哲学上的自然主义在生物学中的重大影响,但他们却忽略了自然主义在地质学和天文学中同等的统治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IDM的支持者把亿万年当作已经被证实了的科学事实。但是,正如我们所展示的,自然主义在控制了地质学和天文学50多年以后才通过达尔文主义控制了生物学。实际上,前者奠定了后者的基础,而后者又成为学术界各个领域拥抱进化论的基础。因此,受造界的年龄和历史成了自然主义哲学扼制科学的核心。进化论就像一根由三股不可分割的线条拧成的绳索:生物进化(生命的起源及演化史)、地质进化(地球的起源及演化史)和天文进化(宇宙和天体的起源及演化史)。如果基督徒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去研读圣经中关于受造界年龄的教导,他们就不能真正地解决进化论或哲学自然主义的问题。
第三,由于IDM论证仅聚焦在设计上,因此他们似乎没有完全意识到自然恶起源的神学重要性,或者,他们知道问题,却不能提供一个与关于堕落的经文一致的恰当的答案。进化论者长期以来指向疾病、突变和自然灾害,他们的结论是:如果这是一个有智慧的设计师的工作,那他就是一个虐待狂。这些观点可以追溯到达尔文,他在1856年给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的信中写道:“自然界的运作是如此地笨拙、浪费、低级得让人大跌眼镜、残忍得可怕,魔鬼的祭司会就此写一本怎样的书!”[9] 一位慈爱的神怎么会造成一个满是死亡、痛苦和自然恶(如飓风、地震、海啸)的世界?这是一个最普遍的反对基督教信仰的论点。除非我们相信创世记所说的关于最初没有动物或人类死亡的完美创造,以及亚当堕落犯罪对宇宙的影响,我们便不能对此提供一个完全符合圣经的神义论的答复。
第四,IDM论点并不能真正替代古老地球进化论,因为IDM的论点没有历史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 “智能设计师”何时进行的创作?一切都是一幕完成的吗?如果是这样,多久以前? 如果不是,那么事物是按照什么顺序创造的,创造活动之间隔时多长? “他”是否仅创造了简单的活细胞,然后所有植物和动物都在有(或没有)“他的”控制或干预下进化出来? 还是“他”以成年形式制造了不同种类的动植物? 没有一些具体的叙述,IDM的论点在解释所有现实方面就比不过进化论。我们认为,只有圣经关于起源和历史的观点才是深度时间进化论的恰当替代方案。
第五,根据经文,虽然自然界确实指向一位设计师,但它远不止于此。它指向了圣经所说的上帝(罗马书1:18-20)。但是IDM的领袖们要么低估了这个事实,要么实际上否认了这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进化论者(他们没有属灵的辨识力)不断谴责IDM是年轻地球创造论的隐蔽形式。但实际上,大多数IDM领袖都强烈反对年轻地球的观点。
最后,充实上一点,IDM的论点只能使一个人相信某种定义模糊的“智能设计者”。根据IDM领袖迈克尔·贝希(Michael Behe)的观点,仅就设计论点而言,它并不能排除设计者是一群外太空生物的结论。[10] 然而圣经说,被造物明证这位真实而活着的上帝,即上帝是天地的创造者。[11] 因此,IDM忽略了许多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了上帝的圣洁、公义和愤怒,以及他的爱心、智慧和权能)。结果,IDM中出现了奇怪的伙伴:自然神论者、泛神论者和各种有神论者。
这种仅凭设计去捍卫上帝存在的方法(无论对上帝的定义如何模糊)曾于1800年代初在英格兰尝试过,参与者主要是某些基督徒和自然神论者,他们已经接受了地球年龄比圣经所教导的更古老的观点。这些智能设计论证没能使异教徒归主,也没能阻止当时的文化从圣经基督教滑向无神论。我们认为其失败的原因是神学上的模糊性,他们虽然分析了古老地球地质学和古老宇宙天文学理论的哲学假设,但这些分析是肤浅的、脱离圣经的。
因此,IDM的论点并不一定会引导人们走向基督。如果他们确实让人考虑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并最终归向基督,那么这样的人可能会难以相信创世记,因为他可能只有一个适合他的妥协的解经模型。如果他的主要导师避免“会引起分裂的创世记解读”,那么在哪里可以找到对圣经的正确解释方法?他可能会对IDM的作者及其著作产生缠绵的情感依恋,因为这些著作曾帮助他相信有一位设计者。相比之下,年轻地球创造论者的提议既包括科学思辨,也包括圣经论证,已经令许多人(包括不少科学家)被基督得着,并让基督徒重返对创世记的完全信任。[12]
我们理解IDM的策略只是在科学层面上吸引唯物主义者,因为(人们认定)唯物主义者不会接受基于圣经权威的论证。但是,年轻地球创造论者知道如何在世俗的公共场合中仅讨论科学证据,例如在大学或公立学校中的讲座或辩论。在IDM运动诞生之前很久,许多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就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即使在这些世俗的背景下,年轻地球创世论者也发现,许多不信的人即使不相信圣经是神启示的话语,但是对圣经在这个主题上的教导还是持开放态度的,并有兴趣了解。虽然我们不要求非基督徒在没有任何护教论证的情况下接受圣经的权威,但我们也不隐瞒自己基于圣经的出发点,或为此道歉。相反,我们显示,科学证据有力地证实了圣经的教导,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上帝启示了圣经,而且他完全了解创世的历史。但是,在与基督徒交流时(例如,在书籍、教会、神学院或圣经书院中,一些IDM领袖也去这些地方),我们必须帮助信徒首先考虑上帝的话语对整个起源问题的说法。
IDM的领袖们有一个异象,它以约翰逊(Philip Johnson)所说的“楔子”策略为代表。[13] 理由似乎是,如果我们先从打破生物进化论的范式开始,让生物学家接受智能设计者的概念,然后我们就可以解决创造者的身份和创造年代的问题。如果我们使得楔子深入进化论范式的原木中并打开足够大的裂缝,那么这块原木将分裂。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异象,因为圣经说凡是没有与神建立正确关系的人都以不义阻挡真理(罗1:18-20)。大多数生物学家将永远不会被赢到智能设计的立场上,因为这基本是属灵的,是世界观的冲突,而不是科学的辩论。此外,为了使大多数生物学家接受智能设计而进行的长期而无果的努力,导致了多少基督徒因为接受了深度时间的地质学和宇宙学理论,而对上帝之道失去信心,并将自然主义的预设吸收到他们的思想中?又有多少非基督徒因为认为地质学和宇宙论证明了创世记的前几章是神话而永远不相信圣经(和福音)而死在他们的罪过(永远沦丧)中?
无神论科学可能会被泛神论科学或自然神论科学所取代(尽管我们怀疑不会这样)。但是圣经的世界观和关于起源的创造模型绝不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无论我们的逻辑和科学证据多么强大,大多数人都不会被说服,原因不在于理智上,而是在于道德和灵命上。如果我们真信圣经关于上帝、人的本性和世界体系本质的教导,结论必然是,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
已故的哈佛大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教授、强烈的反创造论者史蒂芬·J·古尔德(Stephen J. Gould)总结了早期地质学及其对圣经解释的影响:
“传统上,非圣经的资讯,无论是自然的还是历史的,都通过适应圣经的单一叙述而获得了其真正的意义。现在,这种关系开始被反转:圣经叙述通过所谓专家的权威,而适应非圣经知识的框架,从而得到其真正的意义。通过这种方式,圣经知识的合理性和宗教意义只能以越来越受到非圣经因素约束的形式来维持。如果不是在美国,至少是在欧洲,那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地质学家,普遍接受了新的圣经评判,因此认为地球的年龄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无关。”[14]
这场关于地球年龄的争论,归根结底就是围绕着圣经的明晰性和权威性。圣经根本没有教导深度时间、渐进式创造或局部性洪水。它清楚地讲授了几千年前字面意义上的、超自然的六日创造,以及一场全球性的洪灾,洪水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的表面,并在此过程中摧毁了数十亿的植物、动物和人类。创世记第1-3章、罗马书8:19-23和其他相关段落也清楚地表明,神完成的创造甚好,人类和动物没有死亡。此外,圣经对上帝的良善、智慧、权能、公义、忠实和恩典的见证,叫人难以理解他如何在亿万年的过程中创造并消灭了无数物种,然后创造了人类。人类被命令统治这些生物,其中的大多数生物(根据这种观点)在亚当出现之前就已经死了。这个想法没有圣经依据,倡导它就是让上帝无能、邪恶,像虐待狂一样。
因此,我们是以经解经还是以外面的“科学”为更高的权威来解释圣经?我们是否愿意相信上帝的话语?在创造和大洪水发生时,上帝就在现场,他知道一切,他从不犯错,他总是说真话,并且使人无误地编写圣经,叫旧约犹太人、教会先贤们、宗教改革者和当今的基督徒能知道关于受造界如何形成的真相以及为什么它是今天的样子。还是我们对科学家的话语更有信心?在地球的早期历史中,这些科学家并不在场,他们不了解一切,他们不断犯错(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不断修改教科书),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背逆了创造者,试图不用神来解释这个世界,叫自己不必对神负有道德责任。
几年前,本书的一位编辑与一个大型福音事工的一位以敬虔著名的领袖有一次非公开会晤。这位领袖想听听为什么编辑认为地球的年龄至关重要。本书中的一些观点是在他们的谈话中提出的。在讨论结束时,这位领导人说:“我相信上帝可以做任何事情。我相信他可以在六秒钟、六天或六百万年内创造出来。” 这乍看似乎是信心充足的陈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不管这位基督徒是否虔诚,问题不是我们认为上帝能否做。问题是上帝说他确实做了。因此,问题是:我们相信神所说的吗?如果科学理论叫我们采用当初的希伯来文读者从未考虑过的创世记解释,那么下一步将是什么?如果我们重新诠释圣经中关于创造的天数、堕落和洪水,那么重新诠释将在哪里停止?为什么要止于创世记?耶稣基督为童贞女所生或他的复活呢?也许我们忠实于后面两点,但是我们的孩子、学生、学校和教会在我们去世后会这样做吗?
据说,马丁·路德曾经表达以下观点:
如果我以最响亮的声音和最清晰的阐述宣称上帝真理的每一部分,只是避开世界和魔鬼此刻正在攻击的那一点点,那么我不是在承认基督,无论我多么勇敢地宣扬基督教。士兵在战斗激烈处证明他的忠诚;如果他在这一点上畏缩,那么在其他所有战场上的坚定只是他的逃避和耻辱。[15]
当今受到全世界最激烈攻击的战场就是关于世界起源的神圣超自然的创造、圣经年表和洪水。我们是否要在这里为上帝的真理而争辩?我们是否从第一节经文开始相信上帝的圣言并为其真理性而争辩?
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说: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以赛亚书66:1-2)。
在过去的200年中,教会中许多人因维护深度时间的说辞而战兢。但是从历史上看,那些敬拜亚伯拉罕、雅各和以撒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父上帝的人,都因对上帝话语的战兢而表现出他们的忠诚。对您来说,眼下是一个心灵探索、谦卑而忏悔的时代吗?接受造物主话语的时候又到了。福音派人士认为,圣经是独一的、智慧的、永生的上帝的活泼的声音。所以我们都同意他曾在创世记中发声——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们能否谦卑自己,拒绝一切拦阻,战兢地相信他在创世记第1-11章无误的话语,不管世界和其他信徒怎么想?这是每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1] Michael Denton, 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London: Burnett Books, 1985), p. 358. 丹顿是新西兰医生,分子生物学博士。
[2] Milton Millhauser, Just Before Darwin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59), chapter 3.
[3] Ernst Mayr, “The Nature of the Darwinian Revolution,” Science, vol. 176 (2 June 1972): p. 988.
[4] 有关美国大学的非基督教化的全面调查,请参阅 Jonh. Roberts and James Turner,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5] J.I. Packer, “Hermeneutics and Biblical Authority,” Themelios, 1 (1975): p. 11
[6] 杨氏这些话的上下文是这样的:“一日一纪论假说至少在文本上似乎合理,即创造的日子是不确定的长期时期,尽管直接的上下文提示表示‘日’的词‘yôm’的真正含义是‘日’……一日一纪论者发展出令人惊奇的灵活性来克服一些文字障碍。”在讨论了创世记第1章和进化史之间的一系列相互矛盾的事件顺序之后,他继续说道:“但是,这种明显的冲突点并没有劝止好心的基督徒(包括早期我自己)从轻描淡写到表述不同于原文的含义。就我而言,我曾建议不同日发生的事件相互重叠。几年前我为肢解圣经文本而公开忏悔,我将改正,以不让自己更尴尬。”在审查了使创世记和古老地质学协调一致的其他不成功的技巧后,杨氏坦言:“尽管这些做法都精巧,但都勉强得令人瞠目。虽然解经学艺术体操表现出强大的灵活性,我怀疑这也带来了临时性神学肌肉损伤。把创世记第1到11章解释为历史事实,这与科学研究所揭示的关于宇宙和人类早期历史的画面不一致。扭曲圣经的文本似乎无法使它符合科学数据。圣经可能是用非事实的方式表述了历史。”见Davis Young, “The Harmonization of Scripture and Science.” 引用于Marvin Lubenow, Bones of Contention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2), p. 232–234. 莫腾森存有整篇演讲的CD录音。
[7] 参见本书前面的莫滕森关于历史发展的一章的结尾。
[8] 在电影《驱逐》中可以听到许多这方面的陈述。
[9] Frederick Burkhardt and Sydney Smith, eds.,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vol. 6, 1856–185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78.
[10] Michael Behe, “The Evolution of a Skeptic,” www.origins.org/mc/resources/ri9602/behe.html, updated February 6, 1999, accessed August 18, 2008. 他说这是对采访中的倒数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如果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声称聪明的外星人不仅播种了生命,而且实际上设计了地球上的生命,那么我就不能指着一个生化系统来反对他。我可能认为这有点牵强,但我将不得不从哲学、神学或历史的角度来反驳。” IDM的大多数主角都认为设计者是圣经中的上帝,但我们只是在强调这不是从IDM前提得出的必然结论,而是一种主观的宗教观点,源于智能设计以外的其他因素。
[11] 例如,诗篇19:1-6,罗马书1:18-21,使徒行传17:22-31。
[12] 例如 “A Testimony: ‘Joel Galvin’ — Faith Shipwrecked by Compromising ‘Christian’ Colleges; Restored by Answers in Genesis,” www.answersingenesis.org/home/area/feed- back/joel_galvin_testimony.asp.
[13] Phillip E. Johnson, The Wedge of Truth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0).
[14] 被引用于Martin, J.S. Rudwick, “The Shape and Meaning of Earth History,” in David C. Lindberg and Ronald L. Numbers, eds., God & Nature (Berk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306 and 311.
[15] 这个这著名的声明经常被引用,但是很少有人给出适当的文献记录。它能在如下一些二手资料中发现。Elizabeth Rundle Charles, Chronicles of The Schönberg-Cotta Family (London: T. Nelson and Sons, 1864),p. 276. 许多作者错误地将这一段归于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ed.J.K.F. Knaake, et al. (Weimar: H. Bohlau, 1883), Briefwechsel, vol. 3, p. 81f., 但这里只是表达了类似的感悟。参考路德的1523句评论,原始德文版Briefe, Sendschreiben und Bedenken (Berlin: G. Reimer, 1826), p. 345.